一个数学家的学徒生涯「André Weil回忆录」- 全本
安德烈·韦伊:一个数学家的学徒生涯
(André Weil The 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
 安德烈与埃夫琳·韦伊(照片由吕西安·吉莱摄于1948年5月2日)
安德烈与埃夫琳·韦伊(照片由吕西安·吉莱摄于1948年5月2日)
(André Weil The 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
詹妮弗·盖奇 (Jennifer Gage) 英译自法文
译者致谢
我感谢罗珊娜·沃伦 (Rosanna Warren) 持续的支持与鼓励。在数学术语方面,我要感谢萨纳西斯·凯哈吉亚斯 (Thanasis Kehagias)——布尔巴基真正的后裔。最后,我深深感激韦伊博士本人的耐心和慷慨帮助。
J.G. (詹妮弗·盖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成长岁月
第二章 在高等师范学校
第三章 初次旅行,初试写作
第四章 印度
第五章 斯特拉斯堡与布尔巴基
第六章 战争与我:一出六幕喜剧
序幕
芬兰赋格曲
北极间奏曲
身陷囹圄
为国效力
告别武器
第七章 美洲;尾声
人名索引
(献给挚爱的妻子的灵魂)
Pero nadie querra mirar tus ojos porque te has muerto para siempre. (但没有人会想凝视你的眼睛,因为你已永远逝去。)
——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 (FEDERICO GARCIA LORCA)
前言
我的一生,或者至少是配得上这个称谓的那部分——尽管经历了各种变迁,却异常幸福的一生——始于1906年5月6日我的出生,止于1986年5月24日我的妻子兼伴侣埃夫琳 (Eveline) 的去世。如果说在我题献给她的这几页文字中,她出现的篇幅不多,那并非因为她在我的生命和思想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几乎从我们初次相遇起,她就如此紧密地融入其中,以至于谈论我自己也就是在谈论她:她的存在与她的缺席,构成了我全部生命织锦的经线。我该说什么呢?只能说我们的婚姻是那种证伪了拉罗什富科¹ (La Rochefoucauld) 说法的婚姻吧?Fulsere vere candidi mihi soles...²
我的妹妹在这本回忆录中也着墨不多。无论如何,不久前我已向西蒙娜·佩特尔芒 (Simone Pétrement) 讲述了我对她的回忆,她将其记录在她那本出色的传记《西蒙娜·韦伊:一生》(Simone Weil: A Life)² 中;佩特尔芒的书里包含了许多关于我们童年的细节,在此赘述就显得多余了。孩提时,西蒙娜 (Simone) 和我形影不离;但我始终是哥哥,她是妹妹。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少了,交谈时多半带着幽默的口吻;认识她的人都证明,她天生聪慧、充满快乐,即使当世界给她蒙上了一层无情的悲伤时,她依然保持着幽默感。事实上,我们很少进行严肃的对话。但是,如果说我对她青春期的喜怒哀乐一无所知,如果说她后来的行为常常让我觉得(或许有充分理由)简直是违背常识,我们之间却始终足够亲近,以至于关于她的一切,除了她的死亡,对我来说都不算真正的意外。她的死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承认,我曾以为她是坚不可摧的。直到很晚我才明白,她的生命自有其运行的法则,也因此而终结。对她的轨迹,我不过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而已。
我在此试图做的,仅仅是追溯一个数学家的智识历程——一个或许已经变得过于啰嗦,以博(我希望是善意的)年轻一代一笑的数学家。对于作家或艺术家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比仔细审视其婴儿期的最初呢喃更重要了,此后,现代读者便期待着能窥探到主人公最私密的爱情生活。但我既没有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性情,也没有他的才华;而且,那也不是记述一个数学家一生的方式。
我最初计划将这本回忆录结束于1941年3月,我和妻子及她的儿子阿兰 (Alain) 抵达纽约港之时。但我的学徒岁月(我的 Lehrjahre,同时也是 Wanderjahre³)并未那么早结束。我在说什么呢?我今天仍在学习:学习生活在我的回忆之中。愿仁慈的读者带着善意陪伴我……您的陪伴于我将弥足珍贵。
注释:
¹ 指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以其《箴言录》(Maximes) 闻名,其中对人性及婚姻常持批判态度。韦伊意指他们的婚姻证明了幸福长久的婚姻是存在的。 ² 拉丁文,出自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 (Catullus) 的诗,意为“对我而言,那些日子确实阳光灿烂”。 ³ 德语,Lehrjahre 意为“学徒岁月”,Wanderjahre 意为“游学岁月”或“漫游岁月”,指德国传统手工业者学徒期满后的游历时期,也常用于比喻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学习成长与游历探索阶段。
第一章 成长岁月
(Chapter I Growing Up)
我几乎从不记得我的梦境,而我对人脸的记忆力更是差得不能再差。是否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的童年记忆寥寥无几?确实,我一直认为人类的记忆存储空间有限,记忆的艺术既在于记住,也在于遗忘。
因此,我的童年记忆是零碎而稀疏的,并且开始得很晚。再说,我们又怎能确切地区分什么是真正回忆起来的,什么是后来听别人讲述、又不自觉地转化为虚假记忆的故事呢?我脑海中似乎有一幅模糊的画面,是1910年冬天,洪水将巴黎 (Paris) 塞纳河 (Seine) 附近的街道变成了河流。确实有可能我被带去观看这番不寻常的景象;但也许这幅图像只是对我后来听到的描述,或是某个杂志上的照片或插画的转置。
至于我的家世渊源,我只有些模糊而零散的概念:追寻我的“根”("roots")——用现在的时髦话说——从未吸引过我。我的两位祖父我都不认识。其中一位,亚伯拉罕·韦尔 (Abraham Weill),在我出生前就已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去世。据说,作为阿尔萨斯 (Alsace) 犹太社区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员,他经常被请去调解他人的纠纷。按照犹太习俗,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娶了她的妹妹,并与她生了两个儿子,我的父亲,然后是我的奥斯卡叔叔 (uncle Oscar)。我出生时,我的祖母和叔叔们早已带着家人搬到了巴黎 (Paris),他们行使了作为阿尔萨斯人的权利,选择了法国国籍 (French nationality)。我的父亲,贝尔纳·韦伊 (Bernard Weil)(不知在哪一环节,姓氏里的一个l丢失了)也做了同样的选择,并于1905年结婚。
直到1912年,我家都住在斯特拉斯堡大道 (Boulevard de Strasbourg) 19号,离东站 (Gare de l'Est) 不远。有一天,父亲带我在大道上散步时告诉我,我的名字来源于意为“人”("man") 的希腊语 (Greek) 词,这也是给我取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他接着是否说了我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名字?我不记得了;但那无疑是他话语的意图,其含义也因此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父亲很早就决定学医,因此他懂希腊语:在他上学的那个年代,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在高中 (high school) 学习希腊语是无法成为医生的。这项如今看来有些古怪的要求,不仅源于传统的延续,也因为医学术语中充斥着源自希腊语的词汇。作为家中唯一完成中学学业的人,父亲是在斯特拉斯堡,不得不用德语 (German),在人文中学 (humanistisches Gymnasium) 完成的学业。他也是在斯特拉斯堡开始了他的医学学习并服了兵役,很可能是在医疗部队,之后才来到巴黎。他几乎从不谈论他过去的这部分经历;但当他在1914年被征召入伍时,他只在救护队里靠近前线待了几周,就被一条规定调到了后方,这条规定影响了所有曾在德国军队服役的阿尔萨斯人:担心他们一旦被俘会被当作逃兵处理。
 贝尔纳·韦伊医生 (Dr. Bernard Weil) 和塞尔玛·韦伊夫人 (Madame Selma Weil) 与他们的孩子安德烈 (André) 和西蒙娜 (Simone) 在马耶讷 (Mayenne) (1916年)
贝尔纳·韦伊医生 (Dr. Bernard Weil) 和塞尔玛·韦伊夫人 (Madame Selma Weil) 与他们的孩子安德烈 (André) 和西蒙娜 (Simone) 在马耶讷 (Mayenne) (1916年)
我不知道父亲除了能随口背诵《奥德赛》(Odyssey) 的第一行之外,是否还记得他古典学研究中的更多内容,但正是因为这些学识,他后来才能抄写我妹妹那些夹杂着希腊文引语的手稿。无论如何,在我印象中,只要身体允许,他总是全身心投入到他的职业实践中:直到1940年,他的阅读仅限于他忠实订阅的《医学报刊》(Presse Medicale)。他既没有时间,很可能也没有意愿去读其他任何东西。作为一名出色的全科医生,他因其诊断的可靠性而备受同事推崇。除了这项才能,他的和蔼可亲、坦率真诚,以及他无可挑剔的诚实和真正的善良,为他赢得了病人的爱戴,以及战争期间他所服务的各家医院人员的敬仰。
我的母亲于1879年出生在俄国的港口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 (Rostov-on-the-Don)。她的父母都属于奥地利犹太人 (Austrian Jews) 群体,该群体是十九世纪德国文化 (German culture) 最璀璨的花朵之一。她的父亲是阿道夫·莱因赫兹 (Adolphe Reinherz),一位富裕的谷物商人,在婚前就已在俄国 (Russia) 站稳脚跟。他也是一位学者,我的外祖母一直珍藏着那本记录他希伯来语 (Hebrew) 诗歌的红皮笔记本。她生前,我常在她书房里看到这本书,但令我懊恼的是,在她去世很久之后我再去找时,却找不到了。在1882年的反犹骚乱 (pogroms) 之后,全家离开了俄国,先是定居在比利时 (Belgium),最终——在一个心爱的儿子去世后——落脚在巴黎,我的外祖父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在巴黎去世了。从那时起,我那位有着迷人名字赫尔米娜 (Hermine) 的维也纳 (Viennese) 外祖母就一直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她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自从在俄国度过的那段时期以来,她一直对俄语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正是这份兴趣点燃了她与著名生物学家埃利·梅契尼科夫 (Elie Metchnikoff) 及其妻子奥尔加 (Olga) 的友谊。奥尔加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是欧仁·卡里埃 (Eugène Carrière) 的学生,也是她丈夫精彩传记的作者。我无法描述可爱的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1911年)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1911年)
奥尔加·梅契尼科夫,而不提及她在我们婚后被介绍给我妻子埃夫琳 (Eveline) 时惊叹“多么漂亮的蓝眼睛!”的样子。同样来自奥尔加,我至今仍保留着她为我外祖母赫尔米娜画的那幅精美肖像,画中她那悲伤而又宁静甜美的表情,在普林斯顿 (Princeton) 的家中一直伴随着我。
至于埃利·梅契尼科夫,他于1916年去世,我对他唯一的记忆就是他漂亮的胡子;我甚至不确定这记忆是真切地关于他本人,还是关于我可能看过的他的某张照片。但我的父母从他那里感染了一种对细菌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我妹妹小时候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也正是梅契尼科夫,在听说计划为包括让·佩兰 (Jean Perrin) 和保尔·朗之万 (Paul Langevin)(仅举两例)在内的一些科学家的孩子们开办一个班级时,试图说服我的父母让我加入这所“天才学校”("school for geniuses")。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这些计划最终落空了。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1911年)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1911年)
我的父母于1905年在巴黎结婚。这无疑是一桩“包办婚姻”,但不久之后就建立起了牢固的相互情愫,他们的婚姻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稳定的婚姻之一。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医生,无论多么有才华,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设立诊所和购买执业权,几乎是不可能起步的。我母亲的嫁妆就用于此目的,剩余部分则根据我母亲一位叔叔的建议进行了投资,他是巴黎证券交易所 (Paris Stock Exchange) 的经纪人,也是家庭的财务顾问。投资包括俄国和奥地利的政府债券,在当时看似是“可靠价值”("sure values");十年后,这些变成了“无价值”("non-values"),我妹妹和我就此还好好笑了一场。除了这一次,我们家里的谈话从未提及金钱。母亲去世后,我在一个壁橱后面发现了好几捆这些债券。
我的母亲或许正是我父亲需要的那种配偶。她精力充沛,即使在最微小的冲动中也充满激情,能够对家人付出无限的奉献,为家人画了一个魔法圈(幸运的是,我没过多久就得以逃脱),毫无疑问,除了在医疗实践方面,她在所有事情上都迅速取得了对丈夫的主导地位。他显然对这种安排感到相当自在,直到1940年被迫离开巴黎,使他不得不放弃执业,这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空虚,这种空虚因我妹妹1943年的去世而加剧。因此,所有关于家务、社交生活、旅行和度假的决定权都落在了我母亲身上。她在比利时 (Belgium) 接受了极好的文学和音乐教育,自然能流利地说法语 (French) 和德语 (German),英语 (English) 也不错。在巴黎,她显然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歌唱家罗丝·卡龙 (Rose Caron) 最好的学生之一,婚后多年她仍继续培养自己的声乐天赋;因此,至今我脑海里仍装着格鲁克 (Gluck)、莫扎特 (Mozart) 和舒曼 (Schumann) 的许多伟大旋律——尽管我自己从未能唱出一个音符。
我在相当早的年纪,四到五岁之间,学会了阅读,地点是在蒙鲁日-东站 (Montrouge-Gare de l'Est) 有轨电车的上层(由于未知的原因被称为“顶层”("imperial"))。这条如今38路公交车的遥远前身,从我们家通往卢森堡公园 (Jardin du Luxembourg),母亲几乎每天都带我们——我妹妹西蒙娜 (Simone) 和我——去那里散步。母亲会让我读沿途电车线路旁的店面招牌。我成了一个贪婪的读者,拿到什么就读什么。一次在海边度假时,父母很 amused 地发现我在阁楼里全神贯注地读马塞尔·普雷沃 (Marcel Prévost) 的《半处女》(Les demi-vierges)。是时候考虑给我提供更适合我年龄的教育了。
在必要的时间里,母亲密切督导我们的教育,以最明智的热忱投入这项任务。1912年,还没有计算机来给每个孩子分配特定的学校、班级和老师。经过 painstaking 的研究,母亲选择了一位杰出的小学教师,尚特勒伊小姐 (Mademoiselle Chaintreuil),她在蒙田中学¹ (Lycée Montaigne¹) 教十年级 (tenth form)。经过几个月的辅导,她认为我有能力,尽管年龄偏小一点,加入她在中学的班级。她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我母亲与她保持了长期且非常亲密的友谊——据我所知,比她与其他任何人的友谊都要亲密。我们叫她加布里埃尔阿姨 (Tante Gabrielle)。
她最喜欢的读物是阿米埃尔 (Amiel) 的《日记》(Journal)。有一天,母亲认为我在读写方面基础足够扎实,表达了对“算术”("arithmetic")(当时,对于那个年级,“数学”("mathematics") 这个词还未被使用)的担忧。尚特勒伊小姐让她放心:“关于那个科目,无论我告诉他什么,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毫无疑问,她想到的是柏拉图 (Plato) 的回忆理论。
也是“加布里埃尔阿姨”,在学年结束时,送了我一本加斯东·博尼耶 (Gaston Bonnier) 的《简明植物志》(Simplified Flora),我带着它去了瑞士 (Switzerland) 的巴莱格 (Ballaigues)。也许这本书中巧妙的分类系统带给我的乐趣,不亚于它让我得以识别的高山花卉 (Alpine flowers);无论如何,我清晰地记得我和妹妹在那里探索的草地上点缀着的番红花 (meadow-saffron)。回忆起那次度假,更清晰的画面是,当我们走近时,从高高的野草中腾起的成群蓝色小蝴蝶,我却从未好奇到去查找它们的名字。
新学年开始时,我们已从斯特拉斯堡大道 (Boulevard de Strasbourg) 搬到了圣米歇尔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就在圣路易中学 (Lycée Saint-Louis) 对面,离我们钟爱的卢森堡公园 (Jardin du Luxembourg) 和蒙田中学 (Lycée Montaigne) 都不远。在我十年级 (tenth form) 学年结束时,决定让我跳过按常规本应进入的九年级 (ninth form),因为这被认为是多余的:并非我的父母想“拔苗助长”,像现在常见的那样,而是因为当时九年级的目的是巩固前一年的所学,并不会教我任何新东西;在那个更幸福的时代,这样的时间浪费似乎并不可取。因此,我直接升入了八年级 (eighth form)。
这个年级分为三个班,其中一个班由九年级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由蒙贝格先生 (Monsieur Monbeig) 执教。我自然没有被分到这个小组。我的命运是被分给了一位和蔼的先生,他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位族长。按照惯例,每个班每周都要根据一个主题(法语、算术、历史等等,每周不同)写一篇作文 (composition);每周根据这次作文的表现对学生进行排名。这个制度并非没有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对这些排名的重视。然而,将竞争作为一种教学动力如今已失宠,而竞争精神在几乎所有领域却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激烈,这难道不奇怪吗?无论如何,我母亲得知第一次作文我排在班级第一名后,冲到校长那里,告诉他:“如果我儿子连九年级都没上,就能排第一,那一定意味着他所在的班级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我要求你把他转到另一个班;否则,他最终会无所事事。”惊讶的校长回答说:“夫人,这是第一次有母亲向我抱怨她儿子的班级排名太高了。”但我母亲不是那种能容忍别人反对她意愿的人,所以,违反所有规定,我发现自己被置于蒙贝格先生(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格 (geographer Pierre Monbeig) 的父亲,他后来在1945年至1947年间成为我在巴西 (Brazil) 的朋友和同事)慈父般的管教之下。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充满了非传统的想法。为了进行语法分析,他发明了一套个人的代数符号系统,也许仅仅是为了节省他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我回想起来,这种早期对非平凡符号系统的实践一定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尤其对一个未来的数学家而言。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在印度,帕尼尼 (Panini) 发明语法先于十进制记数法 (decimal notation) 和负数 (negative numbers) 的发明,而后来,语法和代数都达到了阿拉伯语世界中世纪文明所著称的无与伦比的高度?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应该通过强迫幼儿谈论集合 (sets)、双射 (bijections)、基数 (cardinal numbers) 和空集 (empty set) 来为他们学习数学做准备。或许,在蒙贝格先生手下学习语法分析——包括词法分析和当时所谓的“逻辑”("logical")(即命题)分析——对我来说,准备得同样充分。无论如何,我必须说,后来我在乔姆斯基 (Chomsky) 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遇到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似乎都不陌生。
然而,不要以为蒙贝格先生的教学水平远超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不认为他的教学中有任何过于抽象的东西。而且在周六下午——因为在那个幸福的时代,家庭和老师都不会被如今困扰人们的周末焦虑所纠缠(当时,周四不上学)——蒙贝格先生会给我们读冒险故事。那一年读的是《科科兰船长》(Le Capitaine Corcoran),母老虎路易松 (Louison) 的英勇事迹让我们紧张得坐立不安。有一次,黑板上出现了一个“脏话”("dirty word")。蒙贝格先生宣布,除非肇事者自首(惩罚肯定很轻微,大概不过是温和的责骂),否则下周六就没有路易松的故事了。我听到身后一个富家子弟的儿子承诺,如果他的邻居愿意挺身而出做替罪羊以挽救局面,就给他二十五生丁的报酬。也许这笔交易并未达成,但我对我们滑稽地称之为“正义”的制度的信心却从此彻底动摇了。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在马耶讷 (Mayenne) (1916年)
安德烈 (André) 与西蒙娜 (Simone) 在马耶讷 (Mayenne) (1916年)
1914年,一切都变了:战争闯入了我们在诺曼底 (Normandy) 海岸的假期。七月的某一天,父亲穿着预备役军官制服出现了,还佩着剑。外祖母觉得他疯了,但不久之后他就奔赴前线了。我写了一首四行诗,无疑是家庭谈话的回声:
医生 wartime 真幸运; 照顾伤病尽职责。 救护车门后面隐, 车门坚固厚实呢。
毫无疑问,在那些悲惨的几周里,母亲和外祖母在这样的想法中寻求慰藉。很快,第一批伤员开始出现。他们被安置在一栋改建成医院的别墅里,我会去那里和一些伤势较轻的人下跳棋。我弄到了一本教科书,是埃米尔·博雷尔 (Emile Borel) 的几何学课本,是我一个年长的表兄留给我的(无疑是心甘情愿的)。
当时,法国中学教育使用的教科书都非常好,是1905年“新大纲”("new programs") 的产物。我们往往忘记了那个时期的改革同样深刻,而且远比我们这个时代改革者所宣扬的(据称受布尔巴基 (Bourbaki) 启发的)福音更有成果。这一切始于阿达玛 (Hadamard) 的《初等几何学》(Elementary Geometry) 和 J. 塔纳里 (J. Tannery) 的《算术》(Arithmetic),但这些杰出的著作,理论上是为中学最后一年“初等数学班”(math. élem.) 课程设计的,实际上只适合教师和最优秀的学生:阿达玛的书尤其如此。相比之下,埃米尔·博雷尔 (Emile Borel) 的教科书,以及后来的卡洛·布尔莱 (Carlo Bourlet) 的教科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学数学课程。我已经不记得1914年夏天落入我手中的是哪一本了,但我还保留着一本布尔莱为三年级、二年级和一年级编写的代数课本,是1915年春天在芒通 (Menton) 得到的。现在翻阅它,我发现它并非没有缺点;但必须说,我对数学的兴趣正是源于此书。
至于我的父亲,从前线被召回后,他在一系列军队医院里度过了战争岁月,除了1915年在芒通 (Menton) 的一段康复期,以及1916年在阿尔及利亚 (Algeria)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以南的一支军队纵队里待了三个月。除了非洲那次,母亲都想跟着他到所有这些岗位,拖着我们——我妹妹和我——一起;通常我的外祖母赫尔米娜 (Hermine) 也陪着我们。这些旅行几乎不利于规律的学习计划,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益处远大于传统的学校生涯。在第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存在保密:父亲被派往讷沙托 (Neufchâteau),一个军事禁区,官方禁止军人家属进入。我们在外面散步时,能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那时伤寒 (typhoid) 疫苗尚未研制出来,医院里到处是伤寒病例。当时的治疗方法是冷水浴,这似乎让病人像苍蝇一样死去。没过多久, overworked 且无疑深感沮丧的父亲自己也病倒了;他被送到芒通接受治疗和康复。这段时期对全家来说是一段愉快的假期。西蒙娜和我成了热衷于收集名为“咖啡豆”的漂亮小贝壳的收藏家。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想在父亲生日那天(4月7日)给他一个惊喜:让妹妹给他读报纸。恐怕我让她经受了一段高强度的学习。就连我们散步时也在练习问答:“M-A-I-S 怎么发音?”“B-E-A-U 怎么发音?”但她最终还是按计划给“比里”("Biri")(我们对他的昵称)读了报纸。
从1914年到1916年,我只上函授课程,老师是本该在中学教我七年级的老师。我跟他开始学习拉丁语 (Latin)。至于数学 (mathematics),我暂时不需要任何人:我对此 passionately addicted。有一次我摔得很疼,妹妹西蒙娜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跑去拿我的代数书来安慰我。为了弥补正规教学的缺乏,我很幸运地从1915年秋天开始订阅了维贝尔 (Vuibert) 出版的《初等数学杂志》(Journal de Mathématiques Elémentaires)。这份极其有用的期刊主要刊登各种问题,尤其是考试题目,涵盖了从三年级(相当于初一)往上的所有中学教育阶段。同时刊登的还有编辑部收到的最佳解答,以及提交了正确解答者的姓名。不久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我竟然也能解答。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被印出来时,我是多么自豪啊!很快,我的名字就经常出现了,然后在一个光荣的日子,我的解答被发表了。虽然《高等数学评论》(Revue de Mathématiques Spéciales) 现在仍然(或者说再次)存在,但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类似《初等数学杂志》的刊物了,真是可惜。
1916年10月新学年开始时,父亲要么在非洲,要么即将启程去那里。我们暂时回到了圣米歇尔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 的家,我被蒙田中学 (Lycée Montaigne) 的五年级 (fifth form) 录取。
我常说,一个有天赋的学生最好每两三年遇到一位优秀的老师来给予他所需的动力,其余时间由更普通的老师来填补。这大概就是一个学生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在法国中学里所能期望的。无论如何,在1916年秋天,我再次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非凡的老师,安德罗先生 (Monsieur Andraud)。他不仅通过了大学教师资格考试 (Agrégation examination),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让鲁瓦 (Jeanroy) 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关于普罗旺斯诗歌 (Provencal poetry) 的论文。安德罗先生说,他是最后一批必须用拉丁语写补充论文 (complementary thesis in Latin)² 的学生之一。让鲁瓦甚至要求他将论文中引用的所有普罗旺斯文本都翻译成拉丁文;正如
安德罗先生所说,那是“一项艰巨的拉丁文练习”。至于他论文的主体部分,他是在用拉丁语思考,这对他来说毫无问题。我所知道的拉丁语几乎都是从安德罗先生那里学到的。后来,再次回到巴黎后,我和妹妹都跟他学习了希腊语。他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但他始终更喜欢他在蒙田中学那个波澜不惊的五年级班级。
在中学度过了富有成效的秋季学期后,我在沙特尔 (Chartres) 度过了该学年的剩余时间,父亲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就被派到了那里。那里的班级水平太差,以至于我几乎完全被免除了上学,借口是在家接受辅导。我们再次在海边度过了一部分暑假。1917年10月学校重新开学时,我们家在拉瓦勒 (Laval)。我已经自学了足够的希腊语 (Greek),并且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学 (mathematics),得以进入三年级 (third form) 的古典文学班。我已经不记得是在那里读了《伊利亚特》(Iliad) 的第一卷,还是我自己为了乐趣而读的;无论如何,我就是这样发现了诗歌,并认识到它是不可翻译的;因为我不认为这一发现可以追溯到几年前我对埃德蒙·罗斯丹 (Edmond Rostand) 的早熟热情,那份热情我也曾传递给了妹妹。那时我们已经会比赛着朗诵高乃依 (Corneille) 或更好的是拉辛 (Racine) 的宏大演说。在三年级的一次背诵作文课上,轮到我背诵拉辛 (Racine) 的《伊菲革涅亚》(Iphigénie) 中克吕泰墨斯特拉对阿伽门农的长篇控诉:这是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我吟诵着诗句,浑然不顾同学们因为我的表演而笑得前仰后合。结束后,老师认真但不失幽默地宣布,“韦伊的朗诵是最好的”,我被评为第一名。
那时我有一本安南代尔 (Annandale) 的英语词典,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包含了对印欧语言学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和格林定律 (Grimm's Law) 的介绍,以及相当详细的、可追溯到梵语 (Sanskrit) 的词源信息。我梦想有一天能够用原文阅读所有这些语言写成的史诗。我对这些史诗的浪漫想法后来促使我去寻求西尔万·莱维 (Sylvain Lévi) 的建议。
1918年我本应进入二年级 (second form),我的文学老师本该是埃米尔·西努瓦 (Emile Sinoir),一位高师毕业生 (Normalien),曾是雅典法国学院 (École d'Athènes) 的成员。但战争接近尾声,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肆虐,我们家正准备返回巴黎 (Paris)。秋天我没有回中学上学,而是接受了西努瓦先生的私人辅导。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教过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与他保持通信。我跟他读柏拉图 (Plato),他会布置一些作文让我写。有一次我得模仿拉布吕耶尔 (La Bruyère) 的风格写一个人物;另一项作业是写“一封给火车站站长的信,询问丢失物品的事宜”。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教学并不像现在人们认为的那样狭隘地局限于书本知识。
回到巴黎圣米歇尔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 的公寓后,我被托付给安德罗先生 (Mr. Andraud) 上希腊语课。课程在我们的餐厅进行,那里还有一个装着两只金丝雀的笼子,是我妹妹的心爱之物。安德罗先生温暖的南方口音几乎总能引得雄金丝雀模仿,只要一听到他的图卢兹口音 (Toulouse accent),它就会开始没完没了地啭鸣。
按计划,十月份我将进入圣路易中学 (Lycée Saint-Louis) 一年级 (first form) 的“C”方向(拉丁语与科学)("C" track (Latin and Sciences))。我的父母非常正确地认为,我的数学知识仍然存在严重缺陷。他们联系了科兰先生 (Mr. Collin),他将是我一年级的老师,结果第二年,在末学年班 (classe terminale),我又成了他的学生。因此,是他为我进入一年级做了准备。
我不能不稍微展开谈谈这位杰出教师的美德。我对他个人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单身汉,住在植物园 (Botanical Garden) 附近的一间小公寓里,他最喜欢的暑期活动是在奥弗涅 (Auvergne) 骑自行车。我从未留意过他的知识视野是否超出了他所负责教授的数学水平;或许他过于内向,不愿显露。像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中学教师一样,科兰先生在如今人们所说的粗俗意义上的“纪律”("discipline") 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当我不再是他的学生时,他告诉我,他被分配到的第一个班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圣西尔军校 (Saint-Cyr) 的预备班)是出了名的捣蛋鬼集中营。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学生们计划要考验他。他坐在教室前面,一言不发地盯着学生们看了一整节课。此后,他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我认为没有哪位老师能比科兰先生更擅长培养学生的严谨思维和创造性想象力了。他会叫一个学生到黑板前,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是几何题,他会确保图形画得正确。常常十分钟在完全的寂静中度过。不仅是黑板前的学生,所有坐在座位上的学生都会热切地尝试寻找解法:在科兰先生的课堂上,即使是那些“职业”差生——那些以此为荣的学生——也急于证明自己并不比我们其他人笨。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后,科兰先生会问:“谁解出来了?”;几只手会举起来。当足够多的手举起来后,全班一起合作解出题目。如果所有人都卡住了,科兰先生会说:“我来提几点看法”,他的提示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定义必须背诵,科兰先生对解题或证明中的任何漏洞都毫不留情。在他那里,数学真正是一门学科 (discipline),在这个美好词语最完整的意义上。
当然,口头提问和问题只是对他教学核心——正式讲座——不可或缺的补充。除了定义,科兰先生并不给我们口述课文。大家默认,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学习智能记笔记的艺术;事实上,我相信没有比这更好的思维训练了。每个人都做笔记,有疑问时就和同学的笔记比较。尽管存在一些非常好的教科书,但没有哪个称职的老师——无论是数学还是其他科目——会满足于仅仅使用这些书。
批评一年级和“初等数学班” (math. élem.) 的数学课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即使是这些课程中最具争议、最受质疑的方面也有其优点。三角形几何和圆锥曲线的焦点理论适合用来出一些能磨砺几何想象力的问题;关于几何轨迹的问题,甚至是所谓的“二次三项式炎”("trinomitis"),都让我们习惯了笛卡尔方法 (Cartesian method) 意义上的“完全枚举”。事实上,这种如今备受诟病的教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
但是我扯远了。关于科兰先生在进入一年级之前的课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一劳永逸地向我展示了数学是通过严格定义的概念来运作的。我从未想过一个函数可以用代数公式以外的方式表达;在我接触到的书中,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可以动摇我这种天真想法的东西。我不记得科兰先生是用什么措辞教我“函数”("function") 这个词的定义的。他不可能使用当时还不存在的布尔巴基 (Bourbaki) 语言,甚至也不可能使用他可能仅略知皮毛的集合论 (set theory) 语言。重要的是,一旦给出了定义,他就不容忍任何人将“函数”这个词用于任何不符合该定义的事物。如果一个函数在一个区间由某个公式给出,在其他地方由另一个不同的公式给出,它仍然是一个函数,因为定义就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除了唯一的例外阿达玛 (Hadamard) 之外,没有人比科兰先生教给我的数学更多。在他成为我的学生之前,我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他把我培养成了一个数学家,而他做到这一点,最主要是通过他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的不妥协之所以如此有效,还因为为了给每周的练习(我觉得有点太容易了)增加点趣味,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两页纸的限制,所有内容都必须写在里面。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走捷径的诱惑,说“显而易见……”("it is obvious that...");科兰先生教我永远不要用这个词。“如果显而易见,”他说,“你就不会觉得有必要这么说;如果你这么说了,那就意味着它并不显而易见。”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写数学。
尽管圣路易中学声称自己是法国最好的理科中学(并非没有道理),但绝不能认为那里的人文学科被忽视了。我已经懂足够的英语 (English),并且对诗歌有足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从一位聪明但也许过于说教的英语老师那里学不到太多东西。另一方面,历史 (history) 老师成功地向我传达了这门学科在智力上是多么 stimulating。他留着胡子,肩膀宽阔,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随心所欲地用一些挑衅性的言论让课堂一片哗然,又能瞬间让它安静下来。他鼓励我们超越教科书。这并非我第一次涉猎历史:早在1916年,我就曾是富斯特尔·德·库朗热 (Fustel de Coulanges) 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 的热心读者;在拉瓦勒 (Laval),我还读过奥古斯丁·蒂埃里 (Augustin Thierry) 的墨洛温王朝编年史 (Merovingian chronicles) 和一部(佩蒂·德·儒勒维尔 (Petit de Julleville) 著的)希腊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基本上是修昔底德 (Thucydides) 著作的改编本。我一年级的老师建议我去圣热内维耶芙图书馆 (Sainte-Geneviève library)——离学校和家都很近——阅读马蒂耶 (Mathiez) 关于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的著作。
在法国文学和拉丁语方面,我们的教授是才华横溢的夏尔-布伦 (Charles-Brun),一位激进的南方地方主义者 (meridional regionalist) 和一个有点放荡不羁的文人 (bohemian man of letters),他第一个拿自己不修边幅的外表开玩笑。
“喜欢我的人,”他会说,“称我的头发是‘他那随风飘拂、不屑梳理的秀发’;其余的人则说‘他那肮脏邋遢的癞毛’。”我会去他位于德朗布尔街 (Rue Delambre) 的家读希腊语,因为希腊语并未包含在中学理科方向的一年级课程中。我们读了柏拉图 (Plato) 的《克里同篇》(Crito);他的教学使我能够在暑假期间阅读《斐多篇》(Phaedo) 和《为科罗纳辩护》(Pro Corona)。夏尔-布伦不太循规蹈矩。尽管如此,当时人们认为最好先学会遵守规则,然后再允许自己打破规则;每篇作文都必须有计划、逻辑发展和结论。有一天的话题是勒南 (Renan) 的一段话,列举了构成一个民族的品质;我们要将这个列表应用于法国。在1920年,这当然是一个可能出现在学士学位会考 (baccalaureate examination) 上的题目。我煞费苦心地逐点论证法国不具备任何必要的品质,并得出结论:“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夏尔-布伦的主持下,地方主义持续取得进展。” 作业发还给我时,得了12分(满分20分)³,评语是:“这相当有趣,虽然太长了……而且你会通不过学士学位会考的。”
事实上,我考试失败的风险不大——尽管我的成功因其他原因而受到威胁。我的年龄远低于参加考试所需的最低年龄;我的特殊考虑请求被拒绝了。由于没有这个初级文凭我就无法开始“初等数学班” (math. élém.) 的学习,大家讨论了替代方案。一年来,我每周四都在康邦街 (Rue Cambon) 的一所小学上木工课,而且颇为喜欢。无论是对我的家人、我的老师,甚至对我自己来说,我注定要从事数学事业这一点当时还并不明显。如果环境后来迫使我转向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s) 或工程学 (engineering),一点实践经验可能会派上用场;有人建议我在职业学校或类似学校花一年时间学习金属加工、应用力学或电学。尽管我对在中学接受的那些完全平淡无奇的物理 (physics) 和化学 (chemistry) 教学并不感冒,但我对这个必要的插曲并无反感。无论如何,机缘巧合之下,我得以幸免。学校督学在第三学期进行了年度视察。科兰先生把我叫到黑板前,乐于让我大放异彩,然后向在教育部有影响力的督学解释了情况;我再次提出的豁免请求获得了批准。暑假期间,科兰先生被调到了一个“初等数学班” (math. élém.),1920年秋天我发现他就在那里。
当时,好学生被鼓励同时参加“初等数学班” (math. élém.) 和“哲学” ("philosophy") 两门学士学位会考:双学士学位对申请进入高等理工学校⁴ (École Polytechnique⁴) 的人有优势。我遵循了这个计划。就我的学业记录而言,这是成功的;但尽管一位可敬的老师努力了,哲学从未能让我“入门”:这门学科似乎与我的思维方式不相容。考试时,我被问到一个与康德 (Kant) 和涂尔干 (Durkheim) 相关的问题。我对所使用的教科书足够熟悉,可以写出一篇尚可接受的文章,但实际上我从未读过这两位作者写的任何一句话,而我得到的分数远高于我认为自己应得的,这让我感到震惊。当哲学考官问及我下一年的计划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将准备高等师范学校 (École Normale) 的入学考试。”“当然是哲学方向?”“哦不,先生;是数学方向。”在我看来,一个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能取得如此好成绩的科目,几乎不值得尊重。年轻是无情的。
确实,在此期间,我已经认识了格雷维 (Grévy),然后是阿达玛 (Hadamard),我未来的计划正在成形。在圣路易中学有四个“预科班” (taupe)⁵ 部分:这是通常给予为高等理工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理科部入学考试做准备的课程的名称。还有一个中间班级,称为“准预科班” (hypotaupe):这里的课程与预科班相同,只是年底不需要参加考试。在四位预科班教授中,格雷维和米歇尔 (Michel) 被认为是最好的。科兰先生把我介绍给了格雷维,后者完全信任科兰的判断;他们俩都认为我有能力加入格雷维的班级,并目标在下个学年就参加高等师范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格雷维把我介绍给了阿达玛,阿达玛曾是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
所有认识阿达玛的人都知道,直到他漫长生命的尽头,他都保持着非凡的思维和性格的清新:在许多方面,他的反应仍然像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的善良无边无际。1921年阿达玛接待我时的热情消除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距离。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同辈,知识渊博得多,但几乎不显老;他毫不费力就能让我接近他。很快,他有机会帮了我一个对我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忙。每年,圣路易中学都会将一项捐赠奖授予“初等数学班” (math. élém.) 最好的学生。奖品是相当于该捐赠基金年利息的书籍。我可以自己挑选这些书,并在选择时寻求了阿达玛的建议。因此,在年度“庄严颁奖典礼”("solemn award ceremony") 上(任何当时在法国中学上过学的人都能想象出那个场景),我收到了若尔当 (Jordan) 的三卷本《分析教程》(Cours d'Analyse) 和汤姆孙 (Thomson) 与泰特 (Tait) 的两卷本《自然哲学论》(Treatise of Natural Philosophy)。多亏了阿达玛,我从若尔当那里学习了分析(比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从古尔萨 (Goursat) 那里学要好得多),并通过汤姆孙和泰特入门了微分几何 (differential geometry)。当然,我没有立刻读完这些大部头;但我认为,我在第二年确实开始读若尔当了。
1921年,相对论 (relativity)——或者当时被称为“爱因斯坦理论”("Einstein's theory")——风靡一时。这个话题被广泛讨论,甚至在报纸上也是如此,以至于我不能不希望熟悉它。我是通过阅读爱丁顿 (Eddington) 来做到这一点的。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操作,张量演算 (tensor calculus) 对我来说似乎很容易,尽管我自然无法领会其几何方面。在黑森林 (Black Forest) 度假期间,我突发奇想,在家庭出游时以父母为实验对象,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解释。他们非常耐心地依从了。第二年,当我在格雷维的预备班时,爱因斯坦 (Einstein) 被邀请到法兰西学院⁶ (Collège de France⁶) 做一系列讲座。入场需要门票:我想我是通过阿达玛拿到票的。所有活跃在科学界、哲学界或上流社会的人都来了,人山人海,以至于不得不调动共和国卫队 (Garde Républicaine) 来控制人群。在这样的氛围下,很难期待高水平的科学交流;如果在那次场合确实有严肃的科学讨论,我相信一定有,那也必定仅限于少数精英——爱因斯坦、朗之万 (Langevin) 和其他少数几个人。保尔·潘勒韦 (Paul Painlevé) 觉得有责任参与公开讨论,他忠实地出席了,为讨论增添了些许趣味,但我仍然感到些许失望。另一方面,我在哲学家格扎维埃·莱昂 (Xavier Léon) 家中目睹了埃利·嘉当 (Elie Cartan) 和爱因斯坦之间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爱因斯坦将他的广义相对论建立在经典黎曼几何 (classical Riemannian geometry) 的基础上,用嘉当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有曲率但无挠率的几何 (geometry with curvature but without torsion);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当时完全不知道还可以设想其他类型的几何,而嘉当的视角则使得可以走得更远。在格扎维埃·莱昂家,嘉当向爱因斯坦指出,例如,也可以设想有挠率但无曲率的几何 (geometry with torsion but without curvature)(事实上,这就是爱因斯坦自己后来引入的具有绝对平行性 (absolute parallelism) 的几何类型)。自然,我不理解嘉当所说的含义,更不用说其引申意义了;尽管如此,它给我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当嘉当的思想对我来说变得熟悉时,它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在预科班 (taupe),学生当然会获得——或者至少在当时会获得——代数运算的熟练技巧,无论有些人怎么说,一个严肃的数学家都很难缺少这种能力。至于格雷维自己的课程,现在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那是一门严肃、诚实、计划周密的课程,无疑优于书店里能买到的教材;无论如何,它使那些教材变得多余了。就规定的教学大纲而言,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好了。在方法和为竞争性考试做准备方面,这种教学无疑达到了它的目标——但我并不认为它真的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一年的预科班是有益的;一个学生可以无害地,有时甚至富有成效地,忍受两年,算上一年准预科班 (hypotaupe)。但是那些考试失败——有时并非他们自己的过错——并在那里待了三年,甚至四年的老“留级生”(taupins),是相当令人恐惧的一群人:他们的命运不值得羡慕。幸运的是,我没有重蹈覆辙。
幸运的是,那年预备课程也没有占据我所有的时间。我开始学习若尔当。另外,我对梵语 (Sanskrit) 早熟而浪漫的迷恋让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产生了想法,把我介绍给印度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西尔万·莱维 (Sylvain Lévi)。那时,大学教授们都在家里,在书堆中工作和接待访客。无论是阿达玛还是西尔万·莱维,我相信他们的任何同事,在法兰西学院都没有办公室;只有在科学实验室里,有时能找到教授的一个角落。当这些学者选择不在家接待访客时,他们通常会安排在学院开会的日子,在学院的前厅与访客见面。
当西尔万·莱维在吉-德拉布罗斯街 (Rue Guy-de-la-Brosse) 的家中接待我时,他对我说:“学习梵语有三个理由,”他列举了它们:我相信是《吠陀》(Veda)、语法 (grammar) 和佛教 (Buddhism)。“你属于哪一个?”我不敢告诉他,驱动我的并非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而仅仅是我对印度史诗 (Indian epic poetry) 的天真想法。我已经学会了——不记得在哪里学的——字母表和一两种变格法,我向他请教如何继续学习。他告诉我,最好的教材是贝尔盖涅 (Bergaigne) 的,但已经绝版了;否则我应该弄一本维克多·亨利 (Victor Henry) 的教材。我立刻买了这本书,并毫不耽搁地开始使用它。
也是在我中学最后几年,我对文学,尤其是希腊诗歌的热情,因对希腊和拉丁作者古版本的喜爱而增强。其中一些当时仍然可以在塞纳河畔 (quays of the Seine) 的旧书摊上找到。阅读这些古版本让我感觉与古代作家更加亲近——并非因为他们的同时代人读过这样的书卷,而是因为我很快就情有独钟的十六世纪版本,是像埃蒂安 (Estienne)、阿尔杜斯 (Aldus) 和比代 (Budé) 这样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而且它们与手稿相距并不遥远。我知道现代版本可能拥有更可靠、更准确的文本;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此外,我逐渐发现,越是近代的版本,就越不可避免地遭受标点过多的困扰。这些拐杖虽然有时有帮助,却不符合文本的精神,有时更容易通过顺应长句的节奏来理解柏拉图或德摩斯梯尼,这可能更好地表达了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意思,而不是使用被句号和逗号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文本。此外,任何热爱精美排版的人都不能不钦佩这些在印刷术早期及其存在的第一世纪里产生的杰作。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已经极难找到那些为罗马 (Rome)、佛罗伦萨 (Florence) 和威尼斯 (Venice) 的印刷厂带来荣耀的伟大摇篮本 (incunabula);即使它们出现,价格也远超我微薄的预算。但在拉丁区 (Latin Quarter) 的书商那里,有时甚至在塞纳河畔的书箱里,仍然能以——即使是我也能负担得起的价格——找到由阿尔杜斯、埃蒂安或西蒙·德·科利纳 (Simon de Colines) 印刷的漂亮书籍。我对它们一见钟情。在皇家宫殿 (Palais-Royal) 拱廊下的一个小店里,我认识了一位博学的年迈书商,他很喜欢我。这个人,我称他为“戈万老爹”("Père Gauvain"),教我如何识别伟大印刷商的标记,如何阅读那些忠实复制自手稿、曾用于印刷希腊文本、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其美感的连字 (ligatures)。卖书对戈万老爹来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然而,正是从他那里,我买到了我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版《伊利亚特》,一本1560年的十六开本 (sextodecimo),它是我多年来形影不离的伴侣。稍后,他提醒我注意一本阿尔杜斯的柏拉图(1513年的初版 (princeps edition)),他的一位同行书商一直想卖掉它但没成功,愿意以极低的价格——相对而言——出手。这次,我的父母不得不出手相助。戈万老爹还教我如何使用布吕内 (Brunet) 令人钦佩的《书商手册》(Manuel du Libraire*)。幸运的是,这部和蔼博学的杰作刚刚在德国以珂罗版重印。利用它,我得以建立一个马尔罗 (Malraux) 式的想象中的图书馆,其中我选择的每一位希腊或拉丁作者都由几部最精美的古版本代表。剩下的就是去寻找实际的书籍了。凭着极大的耐心,我设法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收集了一套相当不错的藏书。但大约在1930年左右,许多美国图书馆想通过建立“稀有珍贵”("rare and precious") 图书收藏来装点门面;价格飞涨,很快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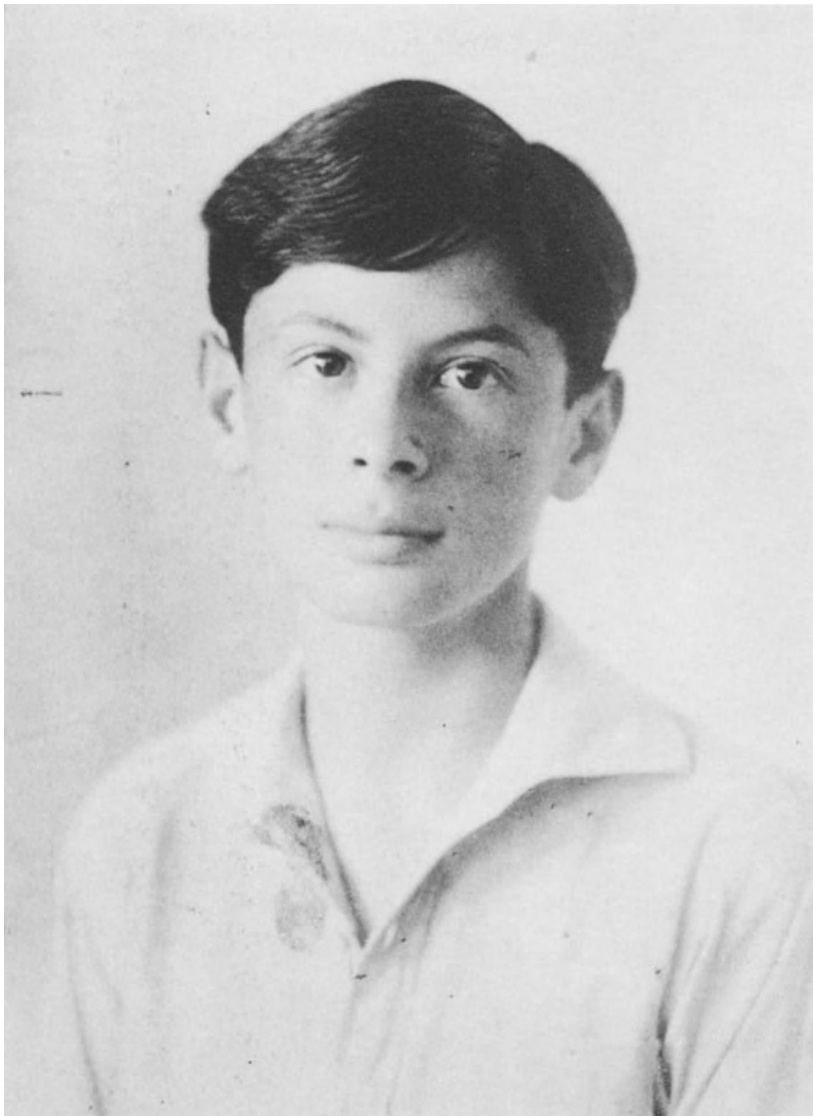 A.W. 在巴登-巴登 (Baden-Baden) 度假 (1921年)
A.W. 在巴登-巴登 (Baden-Baden) 度假 (1921年)
但在1922年,我还看不到那么远。我告别了中学,动身前往高等师范学校。
注释:
¹ Lycée Montaigne: 蒙田中学,巴黎一所著名的公立中学。 ² complementary thesis in Latin: 拉丁语补充论文,过去法国博士学位要求的一部分,除主论文外,还需提交一篇用拉丁语写成的较短论文。 ³ 12 out of 20: 法国学校评分系统通常采用20分制,10分为及格线,12分属于中等偏上的成绩。 ⁴ École Polytechnique: 高等理工学校,法国最负盛名、最难考入的工程师学校之一,常被视为培养精英人才的摇篮。 ⁵ taupe: 法语俚语,特指为考入高等理工学校 (École Polytechnique) 和高等师范学校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等“大学校”(Grandes Écoles) 的理科方向而设立的高强度预备班。 ⁶ Collège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法国历史悠久、地位崇高的学术机构,教授向公众开放其讲座,不授予学位,汇聚各领域顶尖学者。
第二章 在高等师范学校
(Chapter II At the Ecole Normale)
在“高师”("Ecole")——我们过去常这么称呼它——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共享学习宿舍。我首要关心的事,甚至在开学前,就是找到投缘的学友。我们有五个人:除了我自己,还有拉贝雷讷 (Labérenne)、德尔萨特 (Delsarte)、伊夫·罗卡尔 (Yves Rocard) 和巴尔博特 (Barbotte)(他入学考试第一,是我们的“酋长”("cacique" - 指成绩最优者,类似状元)。拉贝雷讷和我一起上过格雷维 (Grévy) 的预备班,是个思想开朗的高个子年轻人;他是个好伙伴,一点也不书呆子气。德尔萨特来自鲁昂 (Rouen),和我一样,只上了一年预科班 (taupe)。罗卡尔来自路易大帝中学 (Lycée Louis-le-Grand),他很快就在自己的储物柜里塞满了大大的黑色笔记本,上面已经用细小但清晰的字迹记录着他关于气体动理论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的想法和计算。我们四个人都不倾向于温顺。但我们的“酋长”就不能这么说了,他曾在凡尔赛 (Versailles) 上预科班:他是一位军人的儿子,尊重权威,不爱搞恶作剧;行政部门总是很看重他。这与我在凡尔赛的一些他的同学给我描绘的形象不同。他最终在我们这群人里感到相当不自在:在他眼里,我们一定显得是危险的异端。
找到学习小组后,我第二关心的就是图书馆。由著名的吕西安·埃尔 (Lucien Herr) 主管的人文图书馆,学生们极易进入。相比之下,科学图书馆——需要穿过一个几乎完全被大地懒骨架(我们称之为“巨兽”("mega"))占据的房间才能到达——每周只对学生开放一两个小时。负责的职员马塞尔·莱戈 (Marcel Légaut),后来写了许多灵修著作,以写博士论文为借口,设法把自己的职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我第一次拜访我们尊敬的科学部主任韦肖 (Vessiot) ,就是告诉他这个最低限度是不够的。他以所罗门的智慧作答,特别为我设立了图书管理员助理(当然是无薪的)的职位,让我拿到了图书馆的钥匙,作为交换,只需承担名义上的保管职责。很快,我就习惯了长时间待在图书馆里,白天如此,有时晚上也如此。
图书馆主要通过交换协议,配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期刊;其他藏书也相当不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恰好有一套完整的战争年代¹ 的《时代报》(Le Temps)。我早已放弃了童年时从阅读保罗·德鲁莱德 (Paul Déroulède) 和报纸中获得的摇旗呐喊的情绪。此外,虽然我的父亲,典型的阿尔萨斯人 (Alsatian),仍然是一位老派的爱国者,但沙文主义 (chauvinism) 在我们家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我父亲本人年轻时显然有过无政府主义 (anarchist) 的同情;他肯定支持过德雷福斯 (Dreyfus),并且仍然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是一位激进社会主义者² (radical-socialist²)。无论如何,我们家几乎从不谈论政治,除非评论最新新闻。而且,我母亲的一个妹妹嫁到了德国 (Germany),住在法兰克福 (Frankfurt)。尽管战时法律禁止与“敌人”("the enemy") 进行任何联系,我的外祖母莱因赫兹 (Reinherz) 从未停止通过瑞士 (Switzerland) 获取消息。“德国佬”("Boche" / "Kraut") 这个词不属于我们的词汇。即便如此,能拿到那套《时代报》,我还是挺高兴的,这样我就可以第一手阅读战争期间灌输给法国公众的“洗眼液”(这是在“洗脑”("brainwashing") 这个词流行之前)(即宣传)。我承认,当我发现德彪西 (Debussy) 的文章一本正经地解释为什么德国音乐不配享有其声誉,以及埃米尔·皮卡 (Emile Picard) 的文章对德国数学说着差不多同样的话时,我有点惊讶。我着手寻找那份著名的宣言,它长期以来为反对“条顿野蛮人”("Teutonic barbarians") 的宣传火上浇油。这份出现在1914年的文本,由九十三位德国知识分子签署,旨在抵消轰炸兰斯大教堂 (Reims Cathedral) 对世界舆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份文本总是被协约国引用,作为为轰炸辩护的骇人听闻的尝试。我发现它的语气是温和的;它恰当地对大教堂的损坏表示惋惜,其中只有一句话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大意是,即使是为了拯救一座大教堂,冒德国士兵生命危险也是不对的。这个想法在我看来确实是野蛮的。并非说,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不能争辩一个人的生命比一座大教堂更有价值;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点,虽然我不接受它,但可以为之辩护。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野蛮之处在于它明确指出要保护的生命是德国士兵的生命,而不是其他人的。我怎么会怀疑,同样的论点,用“我们的孩子”("our boys") 代替“德国士兵”,有一天会成为文明捍卫者的官方教条,并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类似的替换,无限增殖,催生出能想象到的最怪诞的讽刺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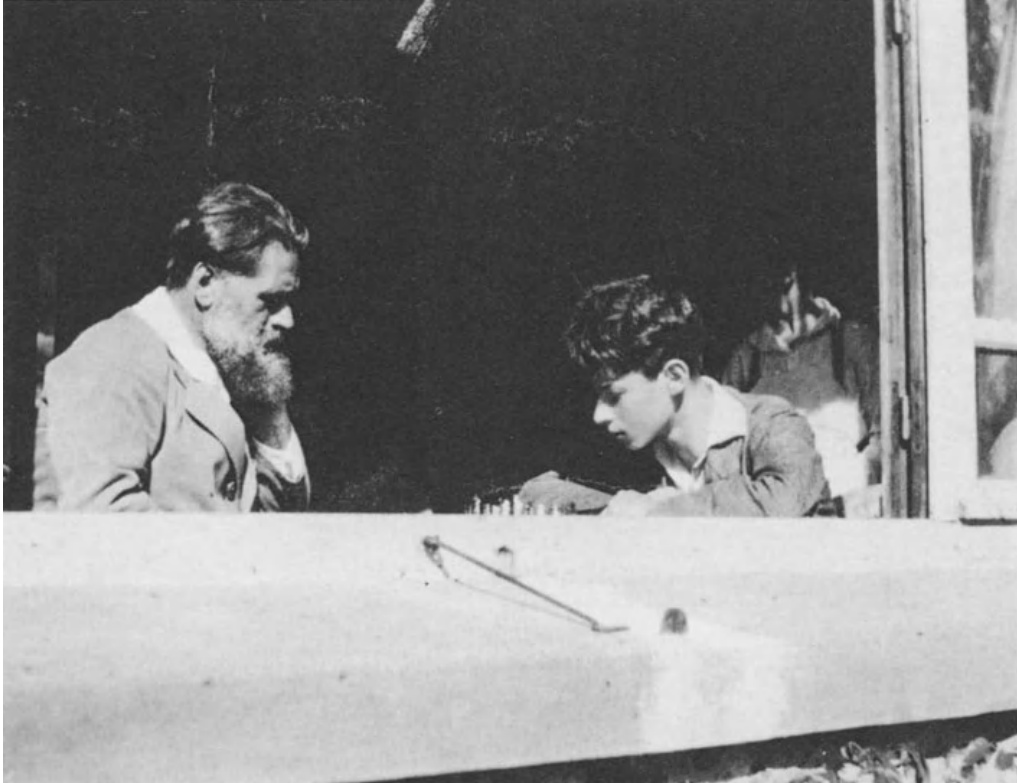 A.W. 在比利时 (Belgium) 度假期间下棋 (1922年)
A.W. 在比利时 (Belgium) 度假期间下棋 (1922年)
 A.W. 和西蒙娜 (Simone) 在松树林中阅读 (1922年夏)
A.W. 和西蒙娜 (Simone) 在松树林中阅读 (1922年夏)
关于“宣言”("manifesto") 的结论,我在此记录下我很久以后在德国了解到的情况。首先,希尔伯特 (Hilbert),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表现出极高的尊严,拒绝签名——尽管我不认为1922年时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熟悉,以至于能注意到签名者名单中没有他。其次,有人告诉我,许多签名者,包括费利克斯·克莱因 (Felix Klein),并没有看到文本;他们只是被电话要求支持一项被说成是爱国义务的事情。只有那些对请愿书、抗议书和各种声明如何在知识分子中兜售毫无概念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
那么,回到我的“图书室”("bibli" - 我们对高师图书馆的称呼):碰巧,当我进入高师时,我对德语 (German) 有相当不错的实际掌握能力。我从未学过这门语言,但我的父母都说得很流利,习惯于在我们姐妹俩不该听懂他们谈话内容时使用德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结果,我能够不太困难地使用德语书籍和期刊。此外,阅读若尔当 (Jordan) 使我比班上其他人占了优势。因此,我免修了古尔萨 (Goursat) 的课程,这门课通常被认为是新“入伍者”("conscripts" - 指新生)的必修课。我没有理由后悔这个决定。事实上,我们被给予了非常大的自由度,唯一的限制是知道如果在年底的执照考试 (Licence examinations) 中失败,就意味着失去在学校的位置,当然还有所有随之而来的特权。同年,我开始参加甚至参与阿达玛 (Hadamard) 在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今天还在举办的话,仍然如此。
“讨论班”("seminar") 这个词因过度使用而变得相当廉价:如今讨论班多如牛毛。讨论班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雅可比³ (Jacobi³)。在巴黎 (Paris),当我在高师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讨论班,那就是阿达玛的。年初,我们在他位于让-多朗街 (Rue Jean-Dolent) 家中的图书馆见面,他分发数学论文让我们作报告。这些论文大部分是他从世界各地收到的抽印本——至少是那些在他看来值得讨论的。除此之外,他还添加了各种来源的题目,以及我们其他人提出的题目,因为他对建议相当开放。这些著作大部分是最近两三年发表的,但这个条件并非硬性规定。至于涵盖的主题,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广泛地展现当代数学的全景。如果说不是详尽无遗,那至少是他的目标。对于他宣布的每个题目,他都会征求志愿者,并常常简要解释为什么这篇论文激起了他的好奇心。题目分发完毕后,就确定了向小组报告的日期,经过一番闲聊,我们就都离开了。
那时讨论班每周举行一次;后来改为每周两次。参与者中有成就卓著的数学家,也有初学者。保罗·莱维 (Paul Lévy),曾是阿达玛的学生,是忠实的参与者之一。阿达玛表现得好像这些报告主要是为了让他个人了解情况;我们是向他陈述,尤其是为他而讲。只要解释得好,他什么都懂;当总结不清晰时,他会要求澄清,或者——并非罕见地——自己进行补充。他总是保留在最后加上自己评论的选择权,有时寥寥数语,有时则更从容。他从未表现出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无论谁在作报告(我特意不用“讲座”("lecture") 这个词,因为在阿达玛面前,报告不可能变成讲座),都被视为平等对待。即使对我这个刚进高师不久就被接纳为参与者的黄毛小子也是如此——这可不是一般的青睐。我相信自己当时对多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对多变量幂级数的收敛域做了一些观察(我认为是原创的,或许确实如此),推广了阿达玛关于单变量级数的经典定理;但更重要的是,我刚在高师图书馆发现了哈托格斯 (Hartogs) 的著作。尽管它们已经问世一段时间了,但在法国鲜为人知,也从未成为阿达玛讨论班报告的主题。我提议了这个题目,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那一年及随后的几年里,“图书室”和阿达玛的讨论班,是它们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数学家。我也上了其他课程:皮卡 (Picard) 在索邦大学 (Sorbonne) 的课,勒贝格 (Lebesgue) 在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课。这两门课程,由两位截然不同类型的强大个性人物讲授,都很有启发性——但我一生中上过太多的课和讲座,认为没有必要一一描述它们。每周二下午五点,走进勒贝格的教室,我们都会钦佩地看着年迈的富卡尔 (Foucart),他刚用希腊铭文写满了黑板,正由两位忠实的学生搀扶着走出同一间教室。他是法兰西学院教授终身制时代最后一位幸存者,年纪离一百岁不远了;他的两位学生看起来也没年轻多少。冬天,在同一间教室里,还会有附近街区的醉汉进来取暖,因为讲座对公众无一例外地开放。他们毫无顾忌地打瞌睡,但对伴他们入睡的声音并非无动于衷——至少我们观察到他们在勒贝格的讲座里待不长,我们会打赌他们能坚持多久。我想没有人能坚持超过八分钟。
同年,我开始阅读黎曼 (Riemann)。在此之前一段时间,首先是在阅读希腊诗人时,我开始确信,在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而了解这些思想家的唯一途径就是直接接触他们的著作。此后我学会了相当大地修正这个判断,尽管我从未真正完全放弃它。然而,我的妹妹,她得出了类似的观点——要么是她自己,要么可能部分受我影响——一直坚持到她短暂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上哲学课的那一年,我也被庞加莱 (Poincaré) 的一句话所打动,它表达了同样极端的立场:“文明的价值只在于它们的科学和艺术。” 怀着这样的想法,一旦物质上和智力上力所能及,我别无选择,只能一头扎进过去伟大数学家的著作中。黎曼是第一个;我读了他的就职论文和他关于阿贝尔函数 (Abelian functions) 的主要著作。这样开始是我的幸运,我一直对此心存感激。这些著作并不难读,只要意识到每个词都蕴含深意:也许没有其他数学家的写作能与黎曼的密度相媲美。若尔当的第二卷是学习黎曼的良好准备。此外,“图书室”收藏了费利克斯·克莱因 (Felix Klein) 的一套很好的油印讲义,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对黎曼著作极端简洁性的一种相当散漫但富有智慧的阐释性评论。
在这一切之中,我努力不忘记梵语 (Sanskrit)。当时朱尔·布洛赫 (Jules Bloch) 在索邦大学教初级班。在那里我遇到了注定拥有辉煌事业的老学长乔治·杜梅齐尔 (Georges Dumézil)⁴。除了对语言基础知识的一丝不苟的教学,朱尔·布洛赫还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他对印度语言和文明以及许多其他主题的闪耀观察。年底,希望利用部分假期阅读梵文文本,我去向西尔万·莱维 (Sylvain Lévi) 请教。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红色天鹅绒装帧的小书。那是一本“本地”("native")(用当时流行的术语)版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读这个,”他告诉我。“首先,如果你没读过它,你就无法理解任何关于印度的事情”——他顿了一下,脸上焕发出光彩——“而且,”他补充道,“它很美。” 借助朱尔·布洛赫借给我的一本词典,以及从高师图书馆借来的《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的英译本,我在舍夫勒斯 (Chevreuse),一个叫做“拉甘盖特”("La Guinguette") 的地方,在我父母一两年前建造的小房子那片杂草丛生的大花园里,通读了《梵歌》。后来我得知,西尔万·莱维同情那些选择将这首诗视为《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后来增补的人:并非说这部庞大史诗的文本在几个世纪里没有被修改和增补;但是,西尔万·莱维想知道,怎么会有人看不出《梵歌》是这部作品的核心,而其余部分必然是围绕它构成的呢?这好比说果核是后来才加到果实里去的。
这首诗的美立刻打动了我,从第一行开始。至于启发它的思想,我觉得在其中找到了唯一能满足我心灵的宗教思想形式。我和妹妹是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或宗教仪式下长大的。除了我的祖母,一位善良的老阿尔萨斯妇女,她讲方言比法语更流利,并始终忠于传统,我们家没有任何东西能以任何方式让人回忆起我们的犹太背景 (Jewish background)。她非常疼爱我们,我小时候叫我“我的小羊羔” (mon hammele)。我记得她纯银色的头发,那么漂亮,以至于有一天一个理发师在街上拦住她,提出要买她的头发。她和我父亲的弟弟奥斯卡叔叔住在一起;我和妹妹很少见到她,也从未试图向自己解释那些在我们看来像是烹饪怪癖的东西。现在很难相信,但我确信直到十岁或十二岁,我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 (Jewish),而当我发现时,我当然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性。我所说的“犹太人”,是指根据这些词语的传统定义,具有犹太血统;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定义犹太性,巴黎大主教显然可以宣称自己是犹太人,而无需担心首席拉比是否同意。如果我小时候问过自己犹太教 (Judaism) 意味着什么,我无疑会得出结论,这个概念,连同其补充概念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与历史或人类学有关,与我无关。无论如何,我不会将它与宗教观念联系起来。事实上,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我的父母一定对此记忆犹新,但他们从未谈论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在中学里,我读了不少帕斯卡 (Pascal) 的书,先是《致外省人信札》(Provinciales),然后是《思想录》(Pensées)。我不仅钦佩他写作的美,也钦佩这位强大头脑锻造出的体系的连贯性。尽管如此,在钦佩这个信仰体系和想要信奉它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对于《梵歌》,我感觉仿佛可以全身心地进入它的世界。后来, благодаря 《梵歌》,我在印度感到宾至如归;很久以后,也 благодаря 《梵歌》,我妹妹的思想方式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我在高师的第二年只是第一年的延续,自由度甚至更大,因为我在一年内就通过了所有考试,我的时间现在完全属于自己。我一定是在第二年读了费马 (Fermat)。我们的主任当时在索邦大学开设一门关于李群 (Lie groups) 的课程。要是嘉当 (Cartan) 来教这门课该多好!但是变换理论 (transformation theory) 的教席是为韦肖设立的,而嘉当过于严谨,不愿侵占同事的领地。这门课或多或少被认为是我这个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我去了一次,无聊透顶,再也没回去过。我倒是定期参加朱尔·布洛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开设的关于《吠陀》(Veda) 的课程。每周在楼梯间我都会与韦肖擦肩而过,他正上楼去教他的课,而我刚从朱尔·布洛赫的课上出来。我总是礼貌地向他问好。这并没有改善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我还听了梅耶 (Meillet) 关于印欧语言学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的讲座和西尔万·莱维关于迦梨陀娑 (Kalidasa) 的《云使》(Meghaduta) 的讲座。这两位老师都是无与伦比的。梅耶几乎已经失明——据说是因为解读了许多来自中亚 (Central Asia) 无法解读的文本——他会即兴演讲,向听众展示一些连我这个无知者也能分辨出是惊人原创性的观察。西尔万·莱维用他略带低沉的声音,逐句逐句地阅读和解释迦梨陀娑的诗。他首先会读梵文文本:对他来说,梵语是一门活语言,印度的学者 (pandits) 长期以来都记得他能在任何场合即兴发表的无可挑剔的梵语演讲。梵文之后是藏文 (Tibetan) 译本,在场的一些人,当然包括我,一个词也听不懂。然后是莱维的评注,最后他会提供一个法文翻译,总是既优美又精确。这首诗主要由一个恋爱中的夜叉 (Yaksha) 对“信使云”(标题中的 meghaduta)发表的长篇演说构成,云将把演说转达给他远方的挚爱。西尔万·莱维擅长展现这首诗的奇妙之处;我至今仍能听到他几乎低语般念出第十节的开头:
mandam mandam nudati pavanah...
法文是:
doucement doucement te pousse le vent (轻轻地 轻轻地 风儿吹拂着你)。
在高师的第三年通常用于准备教师资格考试 (Agrégation examination)。我的工作受到了这种要求的影响——并非说我花了大量精力准备年底必须参加的考试;而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让我感到内疚。因此我培养了对音乐的兴趣,并经常去听音乐会。有五六年的时间,家里让我学小提琴。我的外祖母莱因赫兹,对音乐充满热情,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很久以前,住在比利时时,她失去了她深爱的儿子,他既是出色的法律系学生,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是他小提琴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遗赠给他一把瓜达尼尼 (Guadagnini) 小提琴,我相信,在行家眼中,这琴堪比斯特拉迪瓦里 (Stradivarius)。外祖母虔诚地保存着这把琴,珍藏着希望,希望有一天她的某个外孙能证明自己配得上它。偶尔这把琴会被托付给我。它的音色美妙绝伦,但唉,我知道自己无法胜任这个挑战。一个人可以仅仅为了乐趣而弹钢琴,即使没有天赋,但小提琴至少需要一些天赋,而这正是我残酷地缺乏的。我尝试拉琴的努力让我既认识到音乐的美,也认识到自己无法重现这种美的绝望。我只好仅仅满足于聆听,并订阅了每周出版的《音乐周刊》(La Semaine Musicale)(现已停刊),上面不仅列出了巴黎音乐会的节目单,还附有对演奏作品简短而实质性的分析,以及
巴黎周日教堂礼拜的管风琴音乐节目单。我就是这样在圣雅克-迪奥帕教堂 (Saint-Jacques du Haut Pas) 第一次听到巴赫 (Bach) 的帕萨卡利亚 (Passacaglia)。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教师资格考试包括四场解题考试和两场在评审团面前进行的讲课,主题选自中学课程。准备解题部分意味着复习往年的题目,其中大部分相当古怪。我做了适量这样的工作,并没有理由后悔。另一方面,课堂讲课环节是非常有用的练习,尤其是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点评之后。这项练习教会人如何规划一个报告;人也从中学会——至少,应该学会——如何在黑板前举止得体:对着听众讲话而不是对着黑板,并强调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作为高师的学生,以及后来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自己主持此类练习时,我都觉得它们非常有益。美国学生没有类似的要求,这常常让我感到困扰。1925年,我的口试部分是公开的,在圣路易中学 (Lycée Saint-Louis) 进行,我的一位同学来听我的讲课,看到一位评审团成员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后来把纸留在了桌子上。我的朋友抓起那张纸读到:“他将成为内阁部长。” 幸运的是,这个预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诅咒,没有成真。
第三章 初次旅行,初试写作
(Chapter III First Journeys, First Writings)
像几乎所有家在巴黎的学生,以及少数已婚学生一样,我不是高师的寄宿生。然而,大多数学生是寄宿生,他们生活在斯巴达式的条件下,今天的师范生 (Normaliens) 会对此望而却步。他们睡在大型宿舍里,床位之间仅用薄薄的屏风隔开,提供最起码的隐私:大多数马在马厩里的条件都比这好。寄宿生获得食宿以及一点零花钱,勉强够从“男爵夫人”("the Baroness")那里买咖啡——这是我们对克洛德-贝尔纳街 (Rue Claude-Bernard) 常去的那家酒吧老板娘的昵称,在那里我们经常穿着“邦武”("bonvoust") 服装——也就是发给我们的用于军事训练的工装裤(当时我们词汇里还没有“蓝色牛仔裤”("blue-jeans") 这个词)。(“邦武”这个词来自一位曾一度负责这些训练的邦武上尉 (Captain Bonvoust) 的名字。)那些希望补充微薄收入的学生通过辅导“貘”("tapirs" - 我们对寻求家教的中学生的俚语称呼)来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貘”的供应很充足。据说,自那时以来,一些师范生已经通过不那么传统的方式赚钱了。
相比之下,走读生有权获得一笔 modest 的奖学金,理论上相当于寄宿生的食宿费用。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从未需要求助于辅导“貘”。我的父母虽然不富裕,但生活得相当舒适,对于一个受病人喜爱的医生来说,这很正常;但不向他们要钱是我的荣誉所在。
1925年,教师资格考试 (Agrégation examination) 之后,几乎我所有的同学都去当少尉服兵役了。我们班是最后一届无需通过任何考试就能获得这个军衔的。我还太年轻,不能这样做。当时存在许多奖学金;它们发放得很吝啬——而且我在高师行政部门并不太受待见。其中一项由索邦大学 (Sorbonne) 授予的奖学金相当微薄,引不起什么嫉妒:这个奖学金给了我。它本是为住在巴黎的学生准备的,但我设法安排在罗马 (Rome) 度过一个学年,不太担心这笔钱是否足够。我开始觉得巴黎的视野有些束缚我了。
我已经拥有了贝伦森 (Berenson) 关于意大利艺术 (Italian art) 的四卷书,他在书中编目了伟大画家的作品,我用这些书来参观卢浮宫 (Louvre)。暑假期间,高师允许我借阅文图里 (Venturi) 的多卷本意大利艺术史,理论上这本书是不准带出图书馆的。这些阅读为我提供了一些艺术和语言背景。离开前,我和家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 (French Alps) 的上莫里耶讷 (Haute Maurienne) 地区的朗斯勒维拉尔 (Lanslevillard) 待了两周,在那里我第一次体验了高山。我在那里进行了许多长途步行。在海拔7000英尺或更高的地方,空气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 stimulating 效果。有时全家会进行更长的远足,一直走到冰川开始的地方。在那些日子里,要再往前走,据说需要专业向导的服务;这个机会从未出现过。
我妹妹后来写到,凝视山景曾一劳永逸地将纯洁的观念印刻在她的灵魂中,她想到的就是这次假期。当然,这样的想法没有进入我的脑海:我留下的是完全不同的印象。看到日落时分阳光在远方交错,给了我同时在多个平面上构思的想法。我当时想,写作应该这样,让读者的思绪被引向当前主题之后,朝向它背后的一个平面,然后再到其他更遥远的视角。这个想法并无原创性;我很可能是在别处学到的——例如,在我正准备不久后去看的某些意大利绘画中。但它是在那里,在山中,来到我这里的,而在我妹妹身上,同样的风景激发了截然不同的反思。
在我散步的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打开一本关于丢番图方程 (Diophantine equations) 的计算笔记。费马方程 (Fermat's equation) 的神秘吸引了我,但我对它已有足够的了解,意识到取得进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阅读黎曼 (Riemann) 和克莱因 (Klein) 使我确信,必须将双有理不变性 (birational invariance) 的概念推到前台。我的计算向我表明,费马的方法,以及他的继承者们的方法,都基于一个几乎显而易见的评论,即:如果 和 是代数上互质的、具有整数系数的齐次多项式,并且如果 是互质的整数,那么 和 “几乎”互质,也就是说,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G.C.D.) 只可能取有限个值;那么,如果给定 ,其中 是 和 的次数之和,那么 和 “几乎”是精确的 次幂。我试图将这个评论翻译成双有理不变的语言,并且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里已经有了我未来论文的雏形。
十月,是时候动身去意大利 (Italy) 了。我悠闲地取道米兰 (Milan)、贝加莫 (Bergamo)、维罗纳 (Verona)、维琴察 (Vicenza)、帕多瓦 (Padua)、威尼斯 (Venice) 和佛罗伦萨 (Florence)。游客这个职业有其自身的方法论,需要学习。碰巧我对这个职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这门艺术,表现出了天生的才能。这种才能,加上一定的语言便利,对我此生的幸福贡献不小。我意识到在意大利,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成意大利人:这正是秘诀所在。因为我微薄的津贴迫使我仔细节省开支,我很快学会了侦察街区、旅馆、餐馆或奶酪店,以便能以最优惠的价格找到富裕旅行者常常完全错过的东西。在米兰,我的外国学生身份使我能够获得免费进入意大利所有博物馆的通行证 (tessera),从而使我免于担心一项否则会严重占用我预算的项目。
经过一个月的旅行抵达罗马 (Rome),我已经能说一口过得去的意大利语 (Italian),在那里感到相当自在,更因为著名的维托·沃尔泰拉 (Vito Volterra) 向我伸出了慈父般的欢迎。他可能不如阿达玛那样是位全能的数学家,但在各方面都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人。国王任命他为终身参议员;他和克罗齐 (Croce) 是两位直到最后关头,无论如何都投票反对法西斯分子 (Fascists) 的参议员。1925年,贾科莫·马泰奥蒂 (Giacomo Matteotti) 刚刚被暗杀。在他去世的台伯河 (Tiber) 岸边,每晚都会堆满鲜花,但每天早上都会被警察巡逻队清扫掉。政治生活似乎笼罩着一层不真实的气氛。也许一次有力的推动就能推翻这个政权,但这从未发生。我对这一切始终是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尝试了几次之后,我最终寄宿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离圣母大殿 (Santa Maria Maggiore) 不远。我在那里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房间。我们在厨房吃饭,母亲是一位身材丰满的老罗马人,她做的家常意大利面、面疙瘩 (gnocchi) 和罗马式朝鲜蓟 (carciofi alla romana),和好餐馆里做的一样美味。没有浴缸,也没有暖气,但这不成问题,因为每当寒冷把我赶出房间时,我都可以躲到大学图书馆里。手持优秀的旅行俱乐部 (Touring Club) 指南,我游览了罗马。我在那里度过的六个月对于这个目的来说绝不算太长。罗马确实是永恒之城:所有时代都在那里融为一体,被时间的铜绿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尽管被古典艺术的杰作所震撼,我却自诩为未来主义者 (Futurist),并常去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聚集地,除了以下收获外,我获益甚少:在运动的领袖、颇具传奇色彩的菲利波·马里内蒂 (Filippo Marinetti) 家中,我看到了翁贝托·博乔尼 (Umberto Boccioni) 的作品,包括他那令人钦佩的三联画《告别》("The Farewells")、《远行者》("Those who go") 和《留下者》("Those who stay")。我不知道这幅三联画现在在哪里;我只希望这三块画板没有被分开。我得知博乔尼在战争期间英年早逝,于1916年。
我和维托的长子爱德华多·沃尔泰拉 (Edoardo Volterra)——他本人也注定拥有辉煌的事业——一起去奥古斯都陵墓音乐厅 (Augusteo) 听音乐会,买的是最高层站票。音乐会结束后,我们会互相护送回家,来回走上好几个小时;很快我们就亲如兄弟。我和他一起参观了苏比亚科 (Subiaco) 著名的本笃会修道院 (Benedictine monastery)。它坐落在罗马高处的山坡上,是意大利印刷术的摇篮之一。我希望僧侣们仍然在那里,他们的好客仍然像以前一样慷慨。至于奥古斯都陵墓音乐厅,那个奇怪地容纳在一座继承自古罗马的圆柱形建筑里的音乐厅,已经不在了——法西斯政权的又一个受害者。“那个人,”维托·沃尔泰拉后来谈到墨索里尼 (Mussolini) 时不无夸张地说,“在罗马造成的破坏比在马德里 (Madrid) 还多。”
被如此多的新印象所淹没,我工作适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城市中漫步时梦想着数学。我相信自己对线性泛函 (linear functionals) 有些想法。无论这些想法多么不成形,沃尔泰拉都会以不知疲倦的耐心倾听。我经常见到他的得意门生范塔皮耶 (Fantappié),他一直是沃尔泰拉的最爱,直到有一天他来找沃尔泰拉,赞美墨索里尼步希特勒 (Hitler) 后尘刚刚在意大利推行的反犹立法。沃尔泰拉是犹太人,这一点无人不知。“怎么可能,”他叙述这段插曲时说,“我当时竟然没有当机立断把他扔下楼梯?” 但在1925年,情况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范塔皮耶已经在他的纽扣孔里佩戴着法西斯徽章 (distintivo),但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会讨论泛函演算 (functional calculus)。他从一开始就提议我们使用熟悉的称谓方式,这让我很为难:我的意大利语知识还没扩展到第二人称单数。
当时罗马还有另一位师范生,盖拉尔·德·洛里耶 (Guérard des Lauriers)。我想是韦肖推荐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享有盛誉的奖学金之一。我们俩都定期参观罗马的教堂,但我们碰面的机会很小:我追寻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而他则在寻求大赦 (indulgences),据说在所谓的1925年“禧年”("jubilee" year) ,大赦的条款特别有利。我有时问他:“盖拉尔,你为我祈祷吗?”——他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韦伊,我为你祈祷。” 离开罗马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得知他成了一名多明我会士 (Dominican)。在他对我妹妹的《致一位修士的信》(Lettre à un religieux) 的回应中,他以几次大公会议的权威指责她,因为她暗示一个未受洗就夭折的婴儿的永恒命运与一个受洗婴儿的不会有太大差别。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Vatican Council) 在他眼中不那么受待见。我被告知他陷入了极端保守主义 (integrism),并且在被逐出教会 (excommunicated) 的状态下去世了。
盖拉尔和我并不是罗马唯一的外国数学学生:曼德尔布罗伊特 (Mandelbrojt) 和扎里斯基 (Zariski) 也在那里。扎里斯基前一年刚刚结婚。塞韦里 (Severi) 好心地为我们举办了几场讲座,概述了代数曲面 (algebraic surfaces) 理论的基础知识。他是阿雷佐人 (Aretine),口才很好;他的意大利语比我听过的任何意大利语都更优美。听他讲话时,我很难集中注意力于他谈话的内容,对此我记得很少;充其量,我从中受益也只是无意识的,如果真有受益的话。对于恩里克斯 (Enriques) 邀请我们去他家参加的一系列关于同一主题的非正式谈话,这一点甚至更适用。莱夫谢茨 (Lefschetz) 对罗马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我问塞韦里他对莱夫谢茨工作的看法。“他很棒”(È bravo),塞韦里告诉我,意思或多或少是“他很有才华”:bravo 这个词,据我所知,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他不是庞加莱 (Poincaré),”塞韦里补充道;庞加莱是一只鹰,“一只鹰”(un'aquila)——说到这里他把手举得很高;莱夫谢茨是一只麻雀,“一只麻雀”(un passero),他把手放下一半;但莱夫谢茨很有才华,“不过他很棒,他很棒”(è bravo però, è bravo)。
碰巧,一个远不那么重要的场合,一位我已忘记名字的美国女数学家在罗马的出现,对我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后果。在她应邀就丢番图方程主题进行了一场讲座后,她分发了抽印本。在她的参考文献中,她引用了莫德尔 (Mordell) 如今著名的1922年论文。这个问题与我前一年的思考太接近了,不能不激起我的好奇心。因此,我读了莫德尔的论文,但暂时没有利用它。意大利对我的吸引力太强了。我的第一次意大利之旅圆满结束于那不勒斯 (Naples)、拉韦洛 (Ravello) 和西西里 (Sicily) 的复活节假期,随后是从罗马返回巴黎的旅程,途中我在翁布里亚 (Umbria) 和托斯卡纳 (Tuscany) 逗留。我从这些旅行中获得的收获并非可以长篇大论地汇报;不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浪费了时间,我会非常惊讶。
那时是时候为下一年做计划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刚刚开始其国际项目,优先考虑了一个旅行资助计划,数学家长期有资格申请。该基金会采纳了以下座右铭:“提升山峰;勿求填平山谷。”("Raise the peaks; seek not to fill in the valleys.") 其欧洲项目主任特罗布里奇先生 (Mr. Trowbridge) 是位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在世界各地搜寻最合格的候选人。1926年,他咨询了沃尔泰拉,后者立即建议提名我获得资助。意大利之后,我的愿望是访问德国 (Germany)。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我所要做的就是选择我想去的地方和我希望与之合作的人,并获得此人的同意。我选择了哥廷根 (Göttingen) 的库朗 (Courant),因为线性泛函。不久之后
,我表示希望在这一年中也包括在柏林 (Berlin) 的逗留;这个请求也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项目。维拉 (Villat),一位流体动力学家,也是《数学科学备忘录》(Mémorial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的主编,以对年轻人感兴趣而自豪。他对我略有了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米塔-列夫勒 (Mittag-Leffler) 关于多项式级数 (polynomial series) 的专著,准备发表在《备忘录》上。一两年前,他曾派一位师范生去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撰写此文。他认为有理由相信文章已接近完成,便建议我来完成它。在德国大学的冬季学期和夏季学期之间,我的计划中有近两个月的空档。我提议只在斯德哥尔摩待一个月,不多不少,并尽力在那段时间内完成它。他同意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同意了。在我看来,我关于线性泛函的想法,或者说我认为是我的想法,很可能适用于多项式级数。
再次绕道而行——途经比利时 (Belgium)、荷兰 (Netherlands) 和莱茵河谷 (Rhine Valley)——我于1926年11月抵达哥廷根 (Göttingen),正好赶上冬季学期的开始。我立刻去见库朗 (Courant),他正等着我,在他位于弗里德兰德韦格 (Friedländerweg) 的大房子里,离当时大多数数学活动集中的大学主楼很近。这是在他建造数学研究所(他因希特勒 (Hitler) 而只主持了很短时间)之前(真是 sic vos non vobis...⁵)。我有时会想,上帝,凭着他的智慧,有一天后悔没有让库朗出生在美国 (America),于是他特意把希特勒派到世上来纠正这个错误。战后,当我把这话告诉赫林格 (Hellinger) 时,他对我说:“韦伊,你是我认识的嘴巴最刻薄的人。”
库朗热情地欢迎了我。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拉大提琴:每年他妻子都会组织一个小型的室内乐小组,那年正需要一位大提琴手。听说我不会,他很失望,但还是盛情邀请我参加小组活动。然后我开始解释我关于泛函演算的想法。简而言之,我想把贝尔分类 (Baire classification) 扩展到线性泛函;我被法国学派赋予这个分类的过分重要性误导了,我相信这种方法总有一天能为当时所谓的“第一类积分方程”("integral equations of the first kind") 带来新的启示。库朗耐心地听着。后来我得知,从那天起,他断定我将是“没有成果的”("unproduktiv")。离开他家时,我遇到了他的助手汉斯·勒维 (Hans Lewy),前一天我刚认识他。他问我:“库朗给你题目了吗?”我惊呆了: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罗马,我都从未想过可以“被给予”一个研究题目。据说,对于那些向他要论文题目的人,西尔万·莱维会回答:“你跟我们上课两年了,还没注意到仍然有问题需要解答吗?”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回答汉斯·勒维的;尽管如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从库朗和他的团队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少。而且,我几乎每次和他的一个学生说话,后者不久就会离开,说“我得去为库朗的书写一章”。希尔伯特 (Hilbert) 即将退休。他是数学学会会议上庄严的主席,尽管他不再提出那些人们事后会模仿他波罗的海口音 (Baltic accent) 重复的尖刻俏皮话了。很可惜这些话没有在为时已晚之前被记录下来。康斯坦斯·里德 (Constance Reid) 的希尔伯特传记中引用的英文翻译样本,只给出了他尖锐智慧最苍白的概念。他那个学期仍在教的课(我相信是最后一次了),我只听了部分,对此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显然试图通过讨论动力学来引起物理学家的兴趣。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物理学在哥廷根正蓬勃发展: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正处于孵化阶段。令人瞩目的是,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对此发展我竟毫无察觉。
埃米·诺特 (Emmy Noether) 好脾气地扮演着母鸡和守护天使的角色,不断地在一群人中咯咯叫着,这群人中范德瓦尔登 (van der Waerden) 和格雷尔 (Grell) 脱颖而出。如果她的课程不那么混乱,会更有用,但尽管如此,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以及与她周围人的交谈中,我开始接触到当时开始被称为“现代代数”("modern algebra") 的东西,更具体地说,是多项式环中的理想理论 (theory of ideals in polynomial rings)。保罗·亚历山德罗夫 (Paul Alexandrov) 经常在她家出现。当我告诉他我在巴黎听过勒贝格关于“位置分析”(analysis situs - 即拓扑学) 的课程时,他坚持要看我的课堂笔记,结果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他不知道的东西,大失所望。
我母亲的妹妹住在法兰克福 (Frankfurt)。她丈夫瓦格纳式的名字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配上相当非雅利安的姓氏菲利普松 (Philippsohn)。他们收藏了大量精美的古版画。我在他们家度过了圣诞假期,离动物园 (Tiergarten) 不远,并利用这次旅行联系了法兰克福的数学家。西格尔 (Siegel) 著名的演讲,收录在他全集第三卷的结尾,让人得以了解那里氛围的非同寻常。围绕在马克斯·德恩 (Max Dehn) 周围的有赫林格 (Hellinger)、爱泼斯坦 (Epstein)、萨斯 (Szasz) 和最新加入的西格尔 (Siegel)。我在此提及这个团体,不能不带着感激和深情。
我一生中遇到过两个让我想起苏格拉底 (Socrates) 的人:马克斯·德恩 (Max Dehn) 和布里斯·帕兰 (Brice Parain)。他们两人——就像我们从他弟子记述中想象的苏格拉底一样——都拥有一种光辉,让人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记忆面前鞠躬:一种智力与道德兼备的品质,也许用“智慧”("wisdom") 这个词最能传达;因为圣洁 (holiness) 完全是另一回事。与智者相比,圣人也许只是一个专家——一个圣洁方面的专家;而智者没有专业。这绝不是说德恩不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数学家;他留下了一系列非常高质量的工作。但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真理是浑然一体的,数学只是反映它的镜子之一——也许比其他地方更纯粹。德恩包罗万象的头脑对希腊哲学和数学有着深刻的了解。赫林格虽然不那么热情,却是德恩的同道中人。当然,他不可能像马克斯·德恩仅凭存在就获得的那样,对周围人拥有道德权威,但这两个人似乎天生就能互相理解。他们得到了爱泼斯坦和萨斯的有力协助,他们四人都为有西格尔在身边而深感自豪。我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如此紧密团结的数学家群体。
作为一位人文主义数学家,德恩将数学视为人类心智史上的一个章节——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他不能不为数学史研究做出原创性贡献,也不能不让他的同事和学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这个贡献,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创造,就是法兰克福数学研究所的历史讨论班。没有比这更简单、更不 pretentious 的了。选择一段文本,用原文阅读,努力不仅紧跟表面的推理线路,还要把握其背后思想的主旨。这里我是在预言,因为我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讨论班因假期而暂停了。只是后来,在我后续访问法兰克福时,我才参加了讨论班,我尽可能常去那个地方。我不确定是否早在1926年夏季学期,在一个专门讨论卡瓦列里 (Cavalieri) 的讨论班上,德恩展示了如何必须从作者的角度来阅读这段文本,既要考虑他那个时代普遍接受的东西,也要考虑卡瓦列里尽其所能试图实施的新思想。每个人都参与讨论,尽其所能为集体努力做出贡献。
在1926年的圣诞假期期间,我只遇到了德恩,以及在我即将离开时,与西格尔短暂地见了几分钟。西格尔已经是个传奇人物;我被告知他有几抽屉充满灵感却秘而不宣的手稿。关于这一点,德恩解释了当时在法兰克福流传的理论:数学有被无休止的出版物洪流淹没的危险;但这场洪水源于少数原创思想,每个思想只能被利用到一定程度。如果这些思想的原创者停止发表它们,洪流就会枯竭;然后就可以重新开始。为此目的,德恩和他的同事们克制发表。但写作没有暂停,更不用说在新年或生日等特殊场合赠送朋友一份手稿了。
也许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确保西格尔继续工作,当时美国格言“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 的态度已经侵入了德国大学,并日益让西格尔和像他一样的人感到厌恶。无论如何,德恩拥有一份西格尔为他五十岁生日而赠送的关于超越数 (transcendental numbers) 的手稿。我问是否可以阅读。德恩允许了,条件是在他家读。我甚至被允许做笔记,但附加条件是不能将笔记传给其他人。除了这些条件,德恩并没有坚持对这份工作保密,这份工作后来成为了发表在柏林科学院院刊 (Abhandlungen of the Berlin Academy) 上的长篇论文的第一部分。但手稿结尾处有以下精心勾勒的文字,并未出现在印刷版本中:Ein Bourgeois, wer noch Algebra treibt! Es lebe die unbeschränkte Individualität der transzendenten Zahlen!! ⁶ (搞代数的都是小资!超越数无限的个性万岁!!)
这段插曲之后是另一次访问柏林,这次访问虽然对我富有成果,却不值得如此详细描述。我重新开始了对丢番图方程的思考。霍普夫 (Hopf) 从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回来,正在教授布劳威尔 (Brouwer) 的拓扑学 (topology)。他帮我安排了住处,离他住的地方很近,离市中心相当远,我们会一起乘坐漫长的有轨电车去大学。有一天我问他,当他对拓扑学感到厌倦时会做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但我永远不会对拓扑学感到厌倦!”
埃哈德·施密特 (Erhard Schmidt) 以他真正的贵族风范接待了我。他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他的大理石半身像。它酷似古罗马贵族的半身像,而他也酷似他的半身像。他敏锐的头脑几乎可以与阿达玛媲美——这样说绝非微不足道的恭维。他非常愿意极其专注地听我想告诉他关于泛函演算的事情。他认为这与冯·诺依曼 (von Neumann) 尚未发表的工作有些联系,并建议我应该去认识冯·诺依曼。但冯·诺依曼不在柏林,我直到几年后才见到他。
我也去听音乐会。感谢富特文格勒 (Furtwängler),我意识到贝多芬 (Beethoven) 的交响乐不仅仅是一种周日仪式,就像它们在巴黎给我留下的印象那样。我渴望听到著名的维拉莫维茨 (Wilamowitz) 关于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的讲座。由于我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我需要维拉莫维茨本人的特别许可。尽管魏玛共和国 (Weimar Republic) 废除了所有尊称,我还是被建议称他为“阁下” (Exzellenz)。他在家接待了我,起初似乎为有一位法国学生——战后第一位——来访而欣喜若狂。得知我不是希腊文化研究者 (hellenist),他似乎有些失望,但对我的态度并未因此减少半分。他即将退休,我参加了他的最后一堂课。那天,他放下前一堂课讲解的文本,宣布他将阅读并翻译伯里克利 (Pericles) 的葬礼演说 (Funeral Oration)。他这样做的时候,明显很激动。
于是我该动身去斯德哥尔摩了——并非没有犹豫。有一天在柏林,听完 L. E. J. 布劳威尔 (L. E. J. Brouwer) 关于直觉主义 (intuitionism) 的讲座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去了咖啡馆。我发现自己坐在布劳威尔旁边,向他坦白了我对同意为米塔-列夫勒做的工作的疑虑,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 “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他告诉我,“和他闹翻 (verkrachen Sie sich mit ihm)。” 确实,对布劳威尔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我没有和米塔-列夫勒闹翻。我和他在一起的一个月对我来说非常愉快,但对维拉和他的《备忘录》毫无用处。我很快就认定我前任准备的草稿毫无价值。
我住在米塔-列夫勒位于尤尔斯霍尔姆 (Djursholm) 的别墅里,和他进行了数次谈话,模式都一样。谈话用法语开始,评论几句幂级数 (power series) 和魏尔斯特拉斯 (Weierstrass) 对此的热情。然后米塔-列夫勒会转到他对魏尔斯特拉斯的回忆,接着是索尼娅·科瓦列夫斯卡娅 (Sonia Kowalevska),然后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说德语;之后,他累了,就会换成瑞典语 (Swedish)。最后他会猛地一惊,说:“但我忘了你不会瑞典语。我们下次再继续工作吧。” 事实上,两周后,我已经懂足够的瑞典语来跟上这种类型的对话了。我真诚地开始写一篇《备忘录》文章;但约定是我最多只花一个月时间。月底,我进展甚微,于是彻底放弃了这个项目。
这次旅行的一个好处是我了解了斯德哥尔摩。这是一个可爱的城市,春天最后的冰融化时,它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此外,米塔-列夫勒承诺将我未来的论文发表在《数学学报》(Acta) 上;而且我有幸不是白天而是晚上在他美丽的图书馆度过,那里 meticulously 分类保存着半个世纪以来与欧洲所有伟大数学家积累的通信。夜晚潜入爱尔米特 (Hermite)、庞加莱 (Poincaré) 和潘勒韦 (Painlevé) 的存在中,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激动;在小灯罩投下的私密圈子里,仿佛外部世界已不复存在。
我没有停止我惯常的旅游:在返回哥廷根的路上,我在哥本哈根 (Copenhagen)、吕贝克 (Lübeck) 和汉堡 (Hamburg) 停留。出于对一种仍然相当少见的交通方式的好奇,我从哥本哈根乘飞机去了吕贝克。当时,较小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是非常小的飞机,乘客在其中能真正体验到飞行的物理感觉——这在如今很少发生。我开始将这种普通的旅游形式与一种特定的数学变体结合起来。我形成了像阿达玛一样成为“全能”数学家的雄心:我的表达方式是,我希望对每个数学主题都比非专家了解得多,比专家了解得少。自然,我两个目标都没达到。这时,大会、座谈会和其他“研讨会”("symposia") 尚未流行;此外,对我来说,在人们的自然栖息地与他们相遇,即使是科学家,似乎总是比在随机混合的人群中更有价值。在某人自己的环境中与他相遇似乎更容易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有时,会明显看出他的著作不值得阅读。尽管这种方法会带来各种错误,但实际上它节省了大量时间。
在汉堡,我没能找到阿廷 (Artin)。另一方面,我参观了一个大型的诺尔德 (Nolde) 作品展,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后来,回到巴黎,我热情地向几位热衷现代绘画的朋友谈起他。其中一位经营着一家著名画廊的朋友打断了我:“他从未在巴黎展出过。” 显然,这就算给他定了性。
我回到哥廷根意味着重新开始研究丢番图方程。自从访问柏林以来,我已经能够为代数曲线表述并证明我称之为“分解定理”("decomposition theorem") 的东西,该定理扩展到簇 (varieties) 后,将构成我论文的第一章。突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相同的原理使得有可能看清莫德尔关于椭圆曲线 (elliptic curves) 计算的真正含义,并且通过这种解释,我能够将这些计算扩展到亏格大于1的曲线上。我手头没有莫德尔的论文,在图书馆也找不到。奥斯特洛夫斯基 (Ostrowski),当时是哥廷根的无薪讲师 (privatdozent),不仅以其才华闻名,也以其博学闻名,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使他成为抽印本的收藏家:我跑到他家,果然他有莫德尔的文章,他很乐意借给我。在我兴奋的状态下,重读它只用了几分钟,并证实了我寻求的一切。第二天,我把它还给
奥斯特洛夫斯基,并告诉他我可以将结果推广到任意亏格的曲线:这是对庞加莱二十五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不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相信我。事实上,我宣布我的结果有些过早;我的想法需要大量的改进,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进行,并且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完全发展它们。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试图引起埃米·诺特和她的代数家小组的兴趣——但徒劳无功,因为数论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的注意力被超复数系 (hypercomplex systems),即非交换代数 (non-commutative algebras) 所垄断。幸运的是,西格尔,我在一次访问法兰克福时能够与他长谈,并向他解释了我的分解定理,他对我的第一个发现的价值给予了肯定。
赫林格,无疑被我年轻的热情所打动,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我在泛函演算领域的初次尝试。他与当时来访的朋友兼合作者特普利茨 (Toeplitz) 一起,正忙于为德国百科全书撰写关于积分方程的 обширный 部分。这篇文章至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关于该主题的宝贵信息的金矿。当特普利茨在法兰克福时,他是历史讨论班的常客,法兰克福的数学家们视他为自己人。我乐于想象他们最终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
关于我的返程,我只提两件事:在陶伯河畔罗滕堡 (Rothenburg-ob-der-Tauber)(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座城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教堂里)长时间凝视蒂尔曼·里门施奈德 (Tilman Riemenschneider) 的祭坛,以及我在慕尼黑 (Munich) 与哈托格斯 (Hartogs) 的会面,正如我说过的,自从进入高师以来,我就一直钦佩他的工作。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是一个胆怯、谦逊的人,看起来像一只无害的啮齿动物。我从我们的会面中收获不多,但这并未减少我对他的钦佩。
是时候完善我关于丢番图方程的想法并将它们转化为博士论文了,我在1927年夏天及随后的一年里致力于这项任务。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发现一笔微薄的资助足以满足我 modest 的开销。那年夏天我自学了打字。从节省时间和掌握这项简单技能所赋予的更大独立性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花在学习打字上的几周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时光,我从未停止鼓励所有年轻数学家,乃至其他所有人,都这样做。计算机的时代尚未到来——无论如何,我一直没有它们也过得很好。夏天结束时,我很高兴回到阿达玛的讨论班、梅耶的课程和巴黎的音乐会。
写论文,甚至自己打字,本身还不够:我还需要让大学接受它。我首先去找阿达玛征求意见。我告诉他我的论文解决了一个庞加莱提出的问题。我犯了个错误,补充说我曾希望同时证明现在被称为莫德尔猜想 (Mordell's conjecture) 的东西,即所有亏格大于1的方程解的有限性,但我尚未成功。“韦伊,”他对我说,“我们中有好几个人很看重你;你应该在提交论文时,不要半途而废。你所说的表明你的工作尚未成熟。” 于是我重新努力——但很快我决定就按原样提交我的论文。我的决定是明智的:证明莫德尔猜想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数论 (Number theory) 在法国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学科,但我的论文也讨论了代数函数 (algebraic functions) 和阿贝尔函数 (Abelian functions)。我认为去见埃米尔·皮卡 (Emile Picard) 会很合适。他因为曾是我执照考试 (Licence examination) 部分的考官而认识我。他曾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但也是一位重要人物,法国科学院 (Academy of Sciences) 的常任秘书和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成员。甚至在1914年战争之前,他的头衔和荣誉列表在《数学学报》(Acta Mathematica) 中就占了一页多。我没指望他会读我的工作;我希望他只是做当时情况所需的事情,即提交一份有利的报告。我没有意识到他的职业责任感。在批准论文之前彻底阅读是一项他非常认真对待的职责。也许他也对我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冒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感到恼火。不管怎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很乐意主持我的论文委员会,但我必须找别人来提交报告。
与此同时,西格尔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评价。在巴黎,每个人都告诉我:“这很有趣,你为什么不去找某某某呢?”我听过勒贝格的课。我的主题对他来说完全陌生,而且当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担任论文委员会成员也不是惯例;但他以打破常规为荣。我决心告诉他:“我的论文很好,得到了西格尔的认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要求你读这篇论文;只是为了形式,同意提交报告。” 这或多或少就是我在周一科学院会议上对他说的话,他召我去那里与他谈话。他让我等他,走开与皮卡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回到我身边:“你的手稿带来了吗?”“是的。”“打辆出租车去加尼耶先生 (Monsieur Garnier) 那里,告诉他皮卡先生希望他负责你的论文。” 加尼耶刚刚被任命到索邦大学的一个职位;
据说,没有皮卡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位候选人(传言是法图 (Fatou))可能并且本会获得这个任命。我直接去找加尼耶,复述了我的说辞。他刚要说:“这很有趣……”时,我说了那句有魔力的话。“啊,”他闷闷不乐地说,“如果皮卡先生希望的话……” 于是他被委托负责提交我论文的报告,他尽职尽责且仁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没有注意到我证明中的一些漏洞,但确实在逗号方面给了我一些有用的建议。这段插曲使他成为了所有关于代数和算术论文的官方报告人。谢瓦莱 (Chevalley) 的论文一定比我的更让他头疼。
现在我只需要让我的论文发表。米塔-列夫勒曾承诺在《数学学报》(Acta) 上给它版面。他在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继任者诺尔隆德 (Nörlund) 同意履行承诺。我也到了该服兵役的时候了。我已经在罗马的法国领事馆被征兵委员会传唤过,当时我和一群法国神学院学生一起赤身裸体地出现,他们正取笑他们的德国神学教授,互相讲着关于教会的笑话。由于我的年轻和学生身份,我的兵役被推迟了,第二年在巴黎又被推迟了一次;但这种喘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我的情况很麻烦。我是一个旧制度的最后幸存者,在这个制度下,所有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都自动以少尉军衔开始服役,此前需要经过一些我没有参加过的初步训练。有人建议我去找潘勒韦 (Painlevé),他是众议院议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曾担任过战争部长。他确实给了我一封信,写给一位以极高尊严承担着令人印象深刻头衔——步兵总监——的公务员。决定让我加入步兵,这与惯例相反(理科师范生通常在炮兵服役),并且我将先当一个月列兵,再当一个月中士,剩下的一年当少尉,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地进行,并且全都在巴黎卫戍部队的一个团里。
这个计划带来了一个非常平静的一年,期间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第31步兵团对师范生并不陌生,并且知道不要对他们期望过高。我对步兵军官印象不深。他们中有些是从士兵提拔上来的;都参加了1914年战争的全过程,我相信大多数人表现得非常光荣。但我很震惊地看到,这些在真正危险面前无所畏惧的人,在某个将军或其他什么人来进行视察时,仅仅是接近就似乎吓得魂不附体。女人,即使不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至少也是这些男人之间谈话的主要话题。有一天在军官食堂,一位营长倾诉了这番忧郁的告白:“我什么样的女人都玩过,甚至叙利亚 (Syria) 的贝都因女人”(谈话的其余部分透露,她来找他治牙痛时,他强奸了她);“但我从未有过修女……现在太晚了。” 另一次,在一次行军途中,将包括在香槟地区 (Champagne region) 宿营数日,我听到一位军士长向他的部下(“男人”("man") 指“士兵”:军官不再是“男人”)训话如下:“宿营时,在姑娘们面前规矩点。有机会就和她们睡觉,但要尊重她们,永远要表示尊重!”
这就是营队生活的乐趣,我急于摆脱它们。通过玩弄一些相互矛盾的规定,我设法将我的服役期缩短了近两个月,还不算以需要校对我论文校样为借口获得的假期。差不多是时候给自己找份“真正的工作”了。斯特拉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的一个职位即将空缺,但将由我的朋友亨利·嘉当 (Henri Cartan) 填补。一两年前,我就一直在对西尔万·莱维说,我很乐意去印度 (India)。1929年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你真想去印度吗?”“当然。”“你愿意教法国文明吗?”“法国的或其他任何的,我不在乎;为了去印度,他们想让我教什么都行。”“好吧,打辆出租车,马上到我这儿来。”
在西尔万·莱维家,我发现一个高个子男人,他宽阔的身材、洪亮的嗓音和响亮的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他是那种无论在哪儿都能让人感受到其存在感的人之一。西尔万·莱维和他似乎相互尊重。他名叫赛义德·罗斯·马苏德 (Syed Ross Masood)。后来我得知,E.M. 福斯特 (E.M. Forster) 将他的《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 题献给了他。
这个人是海得拉巴邦 (state of Hyderabad) 的教育部长。在欧洲旅行期间,他收到一封电报,邀请他担任离德里 (Delhi) 不远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的校长(拥有传统的副校长 (Vice-Chancellor) 头衔)。他不可能拒绝这个邀请;这所机构在整个穆斯林印度享有极高声望,由他的祖父创办,当时正处于严重的衰落状态。马苏德被授予全权来拯救它于此境地,他认为这是一项家族义务,毫无疑问,也是通往更高命运的垫脚石——尽管他从未实现。当我遇见他时,他正准备缩短假期,以便能立即返回阿里格尔。他希望法国文化能在印度与英国文化并存,作为开始,他计划在他的大学设立一个法国文明教席。他问我是否
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月薪1000卢比。我对卢比的价值毫无概念,便转向西尔万·莱维,他告诉我这足够了。事实上,这笔钱绰绰有余,但这并非我首先考虑的因素。我同意了条件。马苏德告诉我,我的正式任命通知以及旅费津贴,很快会电汇给我。
然后,几个月里,我杳无音信。我时不时问西尔万·莱维这整件事是否是认真的;他不置可否,建议我等待。得知阿里格尔没有法语书籍,我走访了多家出版商,主要征集文学和历史书籍的捐赠。我甚至从教育部获得了一小笔补助金。最后我收到一封电报:“无法设立法国文明教席。数学教席空缺。电复。” 我回了电报。不久之后,我确实收到了我的旅费津贴。在我与马苏德的会面中,一秒钟都没有提到数学这个话题。是西尔万·莱维告诉他我是数学家吗?这当然似乎是合理的。但我从未被告知。
注释:
¹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18)。 ² Radical-Socialist: 法国的一个政党名称(Parti radical-socialiste),尽管名字中有“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政党,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影响很大。 ³ Carl Gustav Jacob Jacobi (1804-1851): 德国数学家,对椭圆函数、微分方程、行列式、数论等领域有重大贡献。他组织的学生研讨会可能是现代学术讨论班的早期形式之一。 ⁴ 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 法国著名的比较神话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其对印欧社会和宗教结构的研究而闻名。Archicube 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的一种非正式称谓,通常指比应届生年长几届的校友。 ⁵ Sic vos non vobis...: 拉丁语,引自维吉尔,意为“你们如此劳作,却非为自己……”常用来感叹徒劳无功或成果被他人占有。这里韦伊用来讽刺库朗为建造数学研究所付出了努力,但很快因纳粹上台而无法享用其成果。 ⁶ 意思是嘲讽那些只停留在(基础)代数层面的人思想保守狭隘,并赞美超越数(不能作为任何整系数代数方程根的数)所代表的无限多样的个体性。这反映了当时德国数学界可能存在的一种对过于“按部就班”或缺乏深刻洞察力的研究的不屑。
第四章 印度
(Chapter IV India)
我从未写过日记,但在印度期间,我每周都会准时给家里寄一封信。在一周的某一天——我想是周五——P & O 公司(全称是半岛与东方航运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Navigation Company))的轮船会离开孟买 (Bombay),载着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寄往母国的“家信”("home-mail")。就像印度文官 (Indian Civil Service) 的行政官员,或者总督华丽的卫队一样,这个机构也具有帝国 (Empire)——在英印行话中被称为“英属印度”("British Raj")——的所有威严和近乎神圣的特性。在每一个邮局,即使是在印度最偏远、几乎未被文明触及的角落,人们都可以询问家信的情况,并立刻被告知其出发的日期和精确时间。邮件船准时在指定日期出发,驶往马赛 (Marseilles),邮件也同样准时到达目的地,比现在更规律,也许更快。
不幸的是,我每周寄给家人的信几乎全部似乎都永远丢失了。没有这些信件来唤醒我的记忆,我只能满足于从我所拥有的记忆中收集点滴。
要去印度,旅行者可以选择 P & O 公司或意大利里雅斯特劳埃德航运公司 (Lloyd Triestino) 的船只。我从在巴黎认识的印度学生那里得知,P & O 公司主要是英国官僚光顾,气氛相当沉闷,而且(用当时还不流行的词来说)“殖民主义”("colonialist")。为了比当时更了解英国人,我认为最好等到我可能去他们本土拜访他们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印度,可不是为了和那些最无趣的英国人打交道。因此,我选择了一艘意大利船,于1930年初在热那亚 (Genoa) 登船。
当时,这些船的吨位还相当小;从热那亚到孟买,航程只需两周。除非特别努力地孤立自己,否则十五天的时间足以让船上的每个人——乘客、船员和水手——相互熟悉。船上没有电影,但有用船员编织的绳圈玩的“甲板网球”("deck-tennis")。气氛愉快而轻松。自然地,船上发展出了一些风流韵事,但只要船一靠近孟买码头就烟消云散了;但表面上,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十足的体面。这些船仍然使用早已在欧洲旅馆过时的份饭制 (table d'hôte):
 A.W. 在阿里格尔 (Aligarh) 与维杰亚拉加万 (Vijayaraghavan) 和两名学生合影 (1931年)
A.W. 在阿里格尔 (Aligarh) 与维杰亚拉加万 (Vijayaraghavan) 和两名学生合影 (1931年)
船长坐在一等舱餐厅桌子的首位,其他军官则主持二等舱的餐桌。我们享用了美味的意大利食物。用餐时间之外,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舱位间走动,不会引起异议。当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和红海 (Red Sea) 时,我们都把床垫搬到了甲板上。一天晚上,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我爬上了散步甲板上的挡风帆布,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差点在我睡梦中提前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
乘客来自世界各地;甚至有两个芝加哥 (Chicago) 本地人,去印度卖冰箱。他们让我初次领略了美国文明。“禁酒令是件好事,”他们说,“我们都赞成。但为了身体健康,每周需要喝一次酒。” 对他们来说,“每周一次”意味着从周六一直持续到周一早上的威士忌狂饮。还有统舱乘客:这些人大多是年轻的德国人,由于日益严重的危机而被沦为失业者,皈依了佛教 (Buddhism)。他们穿着黄袍,剃光头,正前往锡兰 (Ceylon) 的一座寺院,费用由佛教社团承担。他们安静地通过阅读德文版的佛陀布道来温习他们的新宗教。
我没有在孟买逗留。尽管能看到印度洋 (Indian Ocean)、马拉巴尔山 (Malabar Hill) 和象岛 (Elephanta Island),它仍然是一座缺乏吸引力的城市。我在该市一个伟大的穆斯林 (Muslim) 家族的家中初次体验了印度菜,我在巴黎认识了他们家在留学的儿子。众所周知,印度菜非常辛辣,主要使用辣椒,这是葡萄牙人 (Portuguese) 在十六世纪从美洲 (America) 引入印度的。碰巧,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婚宴。在这个相当西化的家庭里,不遵守普达 (purdah,字面意思是“窗帘”或“面纱”),即妇女被隔离的习俗。我有幸坐在女主人旁边,她好心地向我保证,为了我,她已经确保菜肴不会太辣。尽管如此,食物还是辣得灼口,我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不适。
这些朋友也帮我准备了逗留期间的行装。看到我在巴黎认为有必要装备上的软木头盔,他们忍不住流露出一丝讽刺。但他们让我购买了必不可少的卧具,这成为我在印度期间的旅行伴侣。它由一个薄床垫、一个枕头、一对床单和一个蚊帐组成,全都卷在一个厚帆布提袋里。在火车上,人们会把它铺在卧铺上;拜访朋友时,则会把它放在主人提供的帆布床上。从孟买到德里 (Delhi) 的旅程很快就让我有机会练习使用这套卧具,也让我有机会熟悉了印度平原无处不在的灰尘和车站人群的喧嚣。从德里到阿里格尔 (Aligarh) 不远,我在车站受到了迎接。芬芳的花环戴在了我的脖子上。虽然惊讶又有点尴尬,但我小心翼翼地没有表现出来。“真可惜你没有早一天来,”有人告诉我,“我们一年一度的花展刚刚结束。”“没关系,”我回答,“明年我会看到的。” 我自发的回答让我的对话者很高兴,他告诉我:“你已经是印度人了。”
就这样,在1930年1月,开始了一段持续两年多的逗留,给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印象宝库。这种丰富的刺激只能与一个小孩在地球上生命最初几年所吸收的东西相提并论——只是我从一开始就完全有意识,并且至今仍有生动的记忆。在梵语中,婆罗门 (brahmin) 被称为“再生者”(dvija):第二次生命是由婆罗门圣线赋予他的。就在我即将返回法国前不久,我的朋友维杰亚拉加万 (Vijayaraghavan) 给我系上这样一条圣线,这并非仅仅是个玩笑。难道它不是我第二次诞生的象征吗?
在阿里格尔,我发现马苏德 (Masood) 和我在巴黎见到时一样。几个星期里,我住在他家,和他一起吃饭,因此有机会适应了印度菜,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它。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巴贝尔·米尔扎 (Baber Mirza),刚从法兰克福大学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毕业。他声称自己是莫卧儿 (Mughal) 血统。马苏德在德国遇到他,并当场将他招募到阿里格尔。巴贝尔·米尔扎和我成了好朋友,并将在校园边缘合住一所房子。他未婚,对自己的单身状况抱怨不已。第二年,他利用假期回到德国,带回了一个漂亮、看似天真无邪的小个子德国女孩,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成了纳粹同情者,并说服她丈夫支持亲日派。
在等待我们的房子准备好期间,我必须熟悉我的新环境以及我的新职责。我毫无经验,而且西尔万·莱维对马苏德明显的尊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期望后者能引导我克服面前的许多障碍。在印度的穆斯林社群中,阿里格尔大学的副校长是一位重要人物,马苏德将这个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看着他主持一群尊贵的晚宴客人,用英语 (English) 和乌尔都语 (Urdu) 滔滔不绝地讲述无穷无尽的轶事,这是一场百看不厌的景象。很久以后,回到法国后,我才明白这个光鲜的外表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一个巨大的空虚。
碰巧,马苏德被任命担任此职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清洗教职员工。尽管教员中有几位聪明人(其中包括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但教学人员的资质差得可怜,尤其是在科学学科。马苏德被授予全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解雇教员,无论是否事先通知。这正是我现在所担任的职位发生的情况:我的前任,一个留着胡子、娶了两个妻子(重婚对穆斯林是合法的)的穆斯林,被调到了教育学院院长这个无足轻重的职位上。他曾在德国学习数学,不知怎么设法在那里弄到了博士学位,不择手段。在德国和法国一样,当时普遍认为给印度人或其他“土著”("natives") 授予文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欧洲,一旦回国,他们就会成为他们留学国家的活宣传员。
在这个充满阴谋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感到受到威胁。尽管我很天真,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我的一位同事是一位和蔼的波斯 (Persian) 后裔,教授波斯语言和文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当我问及原因时,我被告知:“你还能指望什么?他是个波斯人。”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所大学(在这方面与其他印度大学并无不同)与英国人费心在印度保留下来的王侯宫廷 (princely courts) 非常相似,这些宫廷直到印度独立后才消失。第二年,我有机会参观了这种宫廷的一个典型样本,在兰普尔 (Rampur),那里的纳瓦卜 (nawab) 音乐家的名声吸引了我。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王侯(或者用他更喜欢的空洞头衔“统治者”("ruler"))的心血来潮,阴谋诡计不断地在他周围上演和瓦解。阿里格尔的情况也是如此,无数的阴谋围绕着马苏德这个人展开。有段时间,我跻身于宫廷宠臣之列,并受到了相应的待遇。不用说,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众所周知,没有哪所大学机构能免受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但在我逗留于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期间,我所见到的阴谋比我此后四十年职业生涯中所见到的更多、更复杂。我对它们只有模糊的记忆,但我确实记得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此类杰作,不是关于大学,而是关于一个宫廷。这段插曲,在我看来,堪比拉摩的侄子津津乐道讲述的阿维尼翁叛教者的故事¹。这与手头的事情几乎没有跑题。
在海得拉巴邦,王侯(尼扎姆 (Nizam))有一位宠爱的妻子或妃子:自然她有敌人,他们结成了一个反对她的党派。这个女人有一个弱点:她没有生育。如果能为尼扎姆生下一个孩子,就能一劳永逸地巩固她的地位。
印度盛产圣人,他们的才能扩展到能为不孕妇女的结合赐福。虽然结果有时可能是通过自然手段实现的,但涉及到尼扎姆的配偶时,就需要更微妙的方法了。一位圣人住在城郊。通过在市民中巧妙散布的谣言,他的声誉被建立起来,并有充足的时间让效果显现。据计算,迟早,这位女人会派信使去找圣人,以获得渴望已久的怀孕秘诀。
她确实这样做了。圣人的指示很容易遵循。女人要请尼扎姆和她共进晚餐,甜点时要献上她用圣人提供的魔法面粉亲手制作的美味点心。之后,她只需留尼扎姆与她共度一夜,怀孕就会随之而来。晚餐按计划进行。在关键时刻,仆人们冲进来喊道:“殿下被下毒了!” 点心被喂给了尼扎姆最喜欢的一条狗。动物在他们眼前倒地毙命。自然,圣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那位女士,她的命运我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了。
自然,我在大学里没有目睹任何如此戏剧性的事情;但我会补充一个更无伤大雅的轶事,也发生在大学之外,但在阿里格尔镇上。我的一位同事,一位年长的穆斯林,教化学,非常喜欢番石榴。每年番石榴季节,他都会从相当远的地方订购几箱优质水果运给他。有一年,他没有收到货。经过询问,他开始怀疑阿里格尔火车站的员工。第二年,他去了水果产地,给每一只要寄给他的番石榴注射了强力泻药。然后他回到家,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车站。他发现整个车站的工作人员都因腹部绞痛而弯着腰。
不管怎样,大学短期内期望我做的,除了教授要求不高的相当低水平的数学课程外,就是为我的系里的教学人员出具一份报告。每个人的合同续签或终止都取决于这份报告。和每个系一样,数学系的教员,用从英国传统教育体系引进的术语来指定,由一位教授 (professor) 和一位副教授 (reader) 组成,底层有两位讲师 (lecturers)。副教授是一位来自孟加拉 (Bengal) 的印度教徒 (Hindu),身材矮小,卑躬屈膝,曾在加尔各答 (Calcutta) 师从加内什·普拉萨德 (Ganesh Prasad)。这位如今完全被遗忘的教授,曾将他的教学成果散布到整个印度北部。两位讲师都是穆斯林,其中一位因乐于助人——加上在政府竞争性考试中零星几次成功——以及他那染成先知胡子颜色的红色胡须,而在学生中极受欢迎。另一位声称曾着手研究一部阿拉伯文的数学著作(《马苏第教规》(Qanun Al Masudi)),其著名的手稿曾属于阿里格尔大学,但已被卖到德国;据说他们保留了一份影印本,我从未见过。这位副教授比其他人有一个优势:在加尔各答,他学到了均匀收敛 (uniform convergence) 的概念。除此之外,三个人都同样毫无优点。
因此,二十三岁的我,掌握着这三个可怜角色的命运,他们对我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这种情况的认识。此外,我只有几周时间来完成我的报告。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既是人事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但马苏德以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为由,拒绝给我任何指示。不用说,我甚至没有考虑咨询我的前任。此外,教学大纲和考试制度在我看来急需改革,但我在这方面的 modest 尝试几乎不受欢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最终垮台的根源:它们有可能引起太大的动荡。
我很乐意一下子摆脱我这三个追随者,但大学里没有人能告诉我是否能找到替代者。我知道的唯一印度数学家的名字是拉马努金 (Ramanujan),但他早已去世。最后,我只好勉强留下了那位副教授。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两位讲师中,我解雇了第二个,并给了第一个,那个红胡子的人,一年的缓期。他似乎哲学地接受了他的失宠,但如果留他在职位上,尽其所能履行职责,也许会更明智。
在此期间,我和巴贝尔·米尔扎租住的房子正在准备入住,家具是我按照巴黎的设计定制的。幸运的是,它不是最近建造的结构。厚厚的泥墙,厚实的茅草屋顶(住着一家猫鼬),一个环绕整个屋顶的大露台,几个阳台,宽敞高挑的房间:一切设计都旨在减少夏季月份的热量影响,并在冬季霜冻期间保温。没有任何我们(无论对错)称之为“便利设施”("conveniences") 的东西:没有浴缸,没有自来水。亚洲人传统上对他们视为欧洲人沉浸在自己污垢中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在这里,日常洗澡意味着用水罐夫 (bhishti) 带来的水冲洗自己,水在厨房加热。做饭是在花园(或者用当时的英印行话说是“院子”("compound"))尽头的柴火上进行的。仆人们和他们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我从未弄清楚他们有多少人,也与他们没有太多交集;我把这些事情留给了我的朋友巴贝尔。他们住的地方也许相当狭窄,但我不认为他们不快乐;受雇于欧洲人或西化的印度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特权,意味着更好的工资和在他们社会群体复杂等级中的更高地位。据说,在花园尽头还有几条眼镜蛇 (cobras),更不用说至少一条珊瑚蛇 (coral snake) 了,巴贝尔有一天在他的拖鞋里发现了它。许多涉及此类蛇的可怕轶事流传着,至少在英国人中间是这样。据说一位英国法官在家里备有血清,以备不时之需。有一天他被叫出家门,发现一辆东加车 (tonga),一种轻便的两轮车,乘客背对着(通常很难闻的)马和车夫乘坐。座位上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显然情况很糟。载他来的那个人说他被蛇咬了。“他伤得太重了,我帮不了他,”法官说,“立刻送他去医院。”“先生 (Sahib),我们刚去过那里;他们把我们赶出来了。”“他们为什么那样做?”法官问。“先生,他们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至于我的眼镜蛇,我从未见过它们;我只看到其中一条的皮,挂在灌木丛中。因为这些蛇,在花园小径上行走时必须稍微小心,尤其是在雨季。除此之外,它们并不可虑。而且它们是神圣的动物,我们的印度教仆人会小心翼翼不去伤害它们。
我们搬进去时,房子里没有电,因此也没有电风扇。取而代之的是“潘卡” (panka)。这是一块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布,通过一根长绳,由一个不幸的男孩懒洋洋地拉动,他驻扎在阳台角落。随着炎热季节的临近,午睡变得必要,有段时间我依赖潘卡来缓解炎热。自然,男孩会打瞌睡。感觉不到温热的空气拂过我,我就会醒来喊道:“潘卡瓦拉!”("Pankevale!") 他会动一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再次让潘卡动起来。虽然我不是进步的狂热爱好者,但当房子里安装了电时,我还是很高兴的。
房子前面,巴贝尔种了玫瑰,它们在印度北部的气候下茁壮成长。后来我的朋友扎基尔·侯赛因 (Zakir Husain),当他成为印度总统后,向我展示了他在总统府后面建造的一个奇妙的玫瑰园。我们还有一些树,上面住着长尾小鹦鹉 (parrokeets) 和那些在美国很常见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很新鲜的小松鼠。夜晚在深沉的寂静中度过,只被守夜人 (chowkidar) 哀伤的叫声打断。据说这个职位只能由一个“改过自新”的职业土匪种姓成员担任,他们宁愿选择稳定的微薄收入,也不愿承担以前职业的风险。每个人负责一组房屋,他应该用叫声来驱赶夜间闯入者。叫声越响亮、越频繁,叫喊者就认为自己越对得起薪水。我礼貌地请求我的守夜人克制他的热情。之后我的夜晚确实更宁静了。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我把床搬到了屋顶上。我从未如此充分地体验过在星空下睡觉的美妙。正如我后来在巴西观察到的那样,热带地区的夜空极其清澈纯净,那里的星星看起来比我们温带气候下的更亮、更多。至少过去是这样;如今,人们说,污染改变了这一切。
引用康德 (Kant) 的话或许是老生常谈:“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 至于道德律,唉,这句话听起来空洞,无论对柯尼斯堡 (Königsberg) 的老大师应有的尊重如何。但我从未能在夜深人静时 (cum tacet nox⁷) 看到星空而不为之动容。在意大利时,它在我看来就比在法国更明亮。那么,当我得以凝视印度天空的景象时,我该如何用言语表达它对我的影响呢?我又该如何描述这些纬度下的月光,而不至于显得可笑呢?月光如此强烈,甚至可以借着它读报纸——尽管那将是对它的可悲利用。旅行者和导游们对月光下的泰姬陵 (Taj Mahal) 赞不绝口。毫无疑问,它配得上“神奇”("magical") 这个当然已被用在其上的形容词;但我从未真正欣赏过这个意大利巴洛克 (Italian baroque) 嫁接到莫卧儿暴君炫耀性奇想上的杂种后代。阿里格尔的一个满月之夜让我看到了更好的东西:那就是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Fatehpur Sikri)。
故事众所周知:阿克巴 (Akbar) 曾想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都;由于缺水,该地被遗弃了,但在此之前,阿克巴和他的一些朝臣已经为自己和他们的妻子建造了宫殿,而正是这种缺水帮助保存了这些宫殿。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离阿格拉 (Agra) 不远,而阿里格尔则位于阿格拉和德里之间。开车走这些距离并不算远。
当我在阿里格尔时,没有出租车或公共交通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东加车 (tongas)。当我和几个朋友决定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度过一个满月之夜时,东加车对我们几乎没什么用。我们求助于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地主,他为自己与大学的良好关系而自豪。他有一辆汽车和一个司机,他慷慨地借给了我们。
如今,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理所当然地受到考古当局的保护,被围墙环绕。法塔赫门 (Fateh Darwaza),那座辉煌的胜利之门,设有售票窗口;入场需凭票,并限制在特定时间。当我参观该地时,它随时向所有游客开放。实际上来的人很少。一家简陋的旅馆有几张床,使我们得以过夜。直到凌晨时分,我们才在这座鬼城里徘徊。我们不知疲倦地探索着画廊和后宫,它们被精心雕刻的石栅栏围起来,这些栅栏曾让她们得以满足对过路人的好奇心,而自己不被看见。月光反射在瓦片屋顶上,穿透窗户的格子,用其超现实的光芒照亮墙壁。我不记得我们最终何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番景象,如今没有哪个旅行者能目睹了。或者,某个有进取心的印度推广商是否已经在那里组织了一场“声光秀”("Sound and Light" show),按人头收费?
阿里格尔本身并没有这样的景点,或者说,没有任何景点。我进城只是为了坐火车。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广阔的北部平原及其辽阔的地平线,只有灌溉渠和多干的榕树林 (banyan trees) 打破了这片辽阔,黄昏降临时,无数绿色的小长尾小鹦鹉会来此栖息、啁啾。我经常进行长途散步,有时和我的某个学生一起。我们不时会绕过一个村庄,那里有卑微的泥墙棚屋,上面覆盖着晒干用作燃料的牛粪或水牛粪。
但炎热的季节临近了,随之而来的是假期,那年定在四月、五月和六月。我计划和一位印度同事在克什米尔 (Kashmir) 度过假期,他是一位友好的年轻阿拉伯语学者,为了好玩给我上乌尔都语课。另一方面,马苏德的彻底清洗生效了,留下了大量空缺职位。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讲师职位。按照程序,每个职位都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根据资历对申请人进行了初步筛选,选定的候选人被召集到一个为做出最终选择而成立的委员会面前。这些委员会定于五月底开会。由于我的系正在进行招聘,我既不愿意也不能缺席这个过程。我们商定我会中断我的假期——尽管在最炎热的季节前景令人不快——快速回一趟阿里格尔。至于初步筛选,马苏德的助手,一位拥有副校长头衔的苏格兰人(他将在夏天结束前死于中暑)向我保证他可以轻松处理。我不信任他的判断,坚持要求在适当的时候将完整的候选人名单及其资质摘要寄到克什米尔给我。申请人超过一百名。最荒谬的申请来自法国在金德讷格尔 (Chandernagor) 的贸易站,附有一封法文私人信件,结尾如下:“……我相信,当选择权掌握在一位法国绅士手中时,我作为法国公民的个人身份必须占优势”(这位误入歧途的人用了“贵族绅士”(gentilhomme) 这个词来指代“绅士”)。名单送到了我在古尔马尔格 (“玫瑰谷”("valley of roses")) 的手中,这是一个中等海拔的山区度假胜地,可以欣赏到喜马拉雅山脉 (Himalayas) 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南迦帕尔巴特峰 (“裸山”("naked mountain")) 的壮丽景色。我很快就看出这份名单上只有一个数学家,按照我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这是哈代 (Hardy) 的一个学生,名叫维杰亚拉加万 (Vijayaraghavan),他有几篇关于逼近论 (approximation) 和陶伯定理 (Tauberian theorems) 的文章,但没有学位,因此不在苏格兰人的短名单上。我跑到最近的电报局,告诉他将维杰亚拉加万加入名单。一在阿里格尔见到他,我就确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摆脱掉我的孟加拉副教授,因为维杰亚拉加万完全有资格担任那个职位。他无可挑剔的牛津英语 (Oxford English),带着轻微的马德拉斯 (Madras) 口音,以及他同样无可挑剔的生丝头巾 (turban),也使他为其他人所接受。我得以乘火车返回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在那里我需要转车去克什米尔。
对于那些歌颂克什米尔的诗人和旅行者的合唱,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我曾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它们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满足。我和我的朋友阿比德 (Abid) 首先租了一艘 houseboat,这是一种为游客装备的驳船,配有合适的船员,以适中的价格提供了探索斯利那加 (Srinagar) 及附近湖泊链的最愉快方式。克什米尔位于古老的商队路线上,这条路线自古以来就连接着中亚 (Central Asia) 与印度,以及与阿拉伯 (Arabia)。这里曾居住着世故的莫卧儿王侯,他们对葱郁景色的热爱促使他们用自己的公园来点缀这些本已无与伦比的地点。
克什米尔当时是一个“土邦”("native state"),当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主要是穆斯林的人口名义上由一位印度教大君 (maharajah) 统治。这个国家非常和平,旅游业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游客被无情地剥削,但是,就像在意大利一样,总是带着微笑,任何能够自卫的游客并不会因此受到更差的待遇——恰恰相反。正是在克什米尔,我获得了讨价还价的初级段位,这是东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入门始于意大利:正如意大利人所说,东方始于那不勒斯 (Naples)。我和一位古董和地毯商人待了几天,他的店铺(也是他的家)堆满了奇珍异宝。按照惯例,我和他聊天,他给我沏茶,并为他的访客和潜在客户一张接一张地展开华丽的地毯。讨价还价的艺术首先要求顾客对自己最想获得的东西假装漠不关心。在印度,流传着一个村庄说书人的故事,他有一天决定转行,在集市上开了一家小店。他不幸的崇拜者们决定迫使他重操旧业。他们私下商定,从他那里买东西绝不讨价还价。几周后,他因无聊而屈服,关门大吉。我的地毯商人几乎不可能害怕同样的事情。当我最终离开他时,我已经以在我看来适中的价格获得了两三张来自波斯或中亚的华丽祈祷毯。它们后来遭遇了可悲的结局,在战争期间被存放在仓库里,被蛀虫吞噬了。
游览完斯利那加的湖泊后,我们去了古尔马尔格,那里喜马拉雅山的景色令人难忘。然后,随着五月底酷热的到来,我短暂地回了一趟阿里格尔。对于我们旅程的第二部分,我们计划沿着印度河 (Indus) 上游河谷追溯到佐吉拉山口 (Zoji La pass),甚至再往前一点——在不需要当局特别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佐吉拉山口绵延数英里,海拔11,000英尺,标志着与拉达克 (Ladakh) 的边界。这个省在地理上是西藏 (Tibet) 的一部分(其人口在种族和语言上是藏族,宗教上是佛教徒),当时处于英国统治之下。靠我自己,我永远无法安排这次探险,也无法将费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在我的同伴阿比德的帮助下,一切都相当顺利。我们的准备工作包括组织一个小小的商队,包括赶骡人、一个厨师和几头骡子来运载我们的帐篷和给养,因为沿途我们只能指望找到鸡蛋和瘦小的鸡。这位厨师曾为欧洲人工作过,表现得足够聪明和能干。虽然我没有预见到主要的登山活动,但我还是 succumbed to the temptation of 一把我在斯利那加偶然发现的登山冰镐——这次购买在几次偏离常规路线的短途旅行中派上了用场。它的使用,尽管有限,却为它在我家至今仍保留的其他过去遗物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印度河的峡谷据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之一,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不会试图去描述它们。我们的路线是通往中亚的那条路,也是从中亚下到麦加 (Mecca) 的商队所走的路线。除了在索纳马格 (Sonamarg),我相信是那里,我们没有遇到其他游客,在那里路线进入一个宽阔的山谷,六月份(我们恰好在月中在那里停留)绚烂的花朵为其赢得了恰当的名字(“金色草甸”("golden alp"))。然而,我们确实不时与牦牛 (yaks) 拉的商队擦肩而过,这些雄伟、毛皮厚实的牛科动物装载着各种货物:编织和刺绣的纺织品、茶砖(藏族人加黄油和盐饮用)、来自新疆 (Sin-Kiang) 绿洲的甘美杏干,其奇妙的味道和气味,直到四十年后在撒马尔罕 (Samarkand) 我才再次遇到。这些水果在我们过夜的村庄商店里出售,为不可避免的单调饮食增添了美味。
这样的旅程若没有一些冒险就不完整。在佐吉拉山口,即使在六月也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层,一支前往新疆的商队派来一个信使,他费了很大劲才用蹩脚的乌尔都语让我的同伴明白他的意思。这支商队是从麦加返回的。前一个冬天,在向西通过山口时,商队遭遇雪崩,人员、牲畜和货物都损失了。目前,几米厚的积雪覆盖了整个区域。幸存者继续了他们的旅程,现在正在返回途中。他们希望找回同伴的尸体,为他们举行体面的葬礼;也许他们也想找回丢失的珍贵货物。但他们该从哪里开始挖掘呢?他们完全没有头绪,并且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奇迹,指望我们提供能看透积雪的双筒望远镜。唉,我们无法提供这样的帮助,只好分开了。商队司机们和我们一样目瞪口呆,同样失望。
在拉达克本身,离佐吉拉山口两天路程的地方,就在我们准备返回时,我们发现自己同样无法应对一个更普通却更直接悲惨的情况。在一个农舍里,我们看到一个在事故中受伤的男人,他的眼睛严重受伤,已经严重感染。他的同伴们临时做了一个绷带。对于这些人,就像我们称之为“原始”的许多人群一样,每个欧洲人既是医生、外科医生,又是奇迹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建议将受害者送到最近的医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但是拉达克的首府列城 (Leh),那里无疑有一位英国或印度教医生,离那里有好几天的路程;斯利那加更远。幸运的是,我们不必过多纠结于这件事。我们被邀请观看两支当地球队之间的马球比赛。这项运动不仅在这些地区是传统的,据说还起源于此。
不久之后,回到了阿里格尔,这次是在雨季闷热的天气里。维杰亚拉加万刚刚抵达,准备开始新学年。正如他的名字所示,他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婆罗门。他来自泰米尔语 (Tamil) 国家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印度的传统文明以可能是其最纯粹的形式幸存着。他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 (pandit)。与父亲相比,维杰亚拉加万说,他自己的梵语知识很差。尽管他很谦虚,但他对梵语和泰米尔语的古代文学都非常熟悉。就像我带着我的袖珍《伊利亚特》,甚至带到了克什米尔一样,维杰亚拉加万从未离开过一本用泰米尔字母印刷的《摩诃婆罗多》,它占据了两大卷灰色布面装帧的书。年轻时在马德拉斯考试不及格后,他离开去牛津 (Oxford) 跟随哈代学习,在我遇到他时刚刚回到印度。他是一位非常敏锐的数学家,无疑受到哈代的过度影响;但由于没有文凭,他几乎没有机会在任何印度大学获得职位,更不用说像阿里格尔这样的穆斯林大学了,要不是我碰巧在那里这个幸运的意外。他抱着侥幸心理申请了这个职位,结果发现自己被传唤面试,然后被选中担任该职位,这让他非常惊讶。没过多久,维杰亚拉加万和我就成了挚友。夸张点说,我几乎从未离开过他身边。就连他的母亲,家族中执掌大权的 matriarch,在我第一次拜访时观察到我不仅能忍受而且津津有味地吃一道极辣的菜肴——我确信这是她准备的,暗地里希望一劳永逸地吓跑我——之后,也把我纳入了她的羽翼之下。我是第一个被允许进入她家的欧洲人。即使关系到她儿子的事业,这种对种姓规则的违背对她来说也一定带来了一些痛苦。
在《唱赞奥义书》(Chandogya Upanishad) 最美丽的故事之一中,一个名叫萨蒂亚卡玛 (“真理爱好者” - Satyakama) 的年轻人寻求成为一位著名大师的弟子。按照规定,他必须是婆罗门出身。当被问及这一点时,他毫不犹豫、毫无窘迫地回答说,他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他母亲告诉他,他是在家里非常忙碌的时候怀上的,她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她的名字叫贾芭拉 (Jabala),他的名字叫萨蒂亚卡玛。“因此我是萨蒂亚卡玛·贾芭拉,”他总结道: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有婆罗门才能如此真实地说话,”大师回答道,并接受了这个男孩做他的弟子。我喜欢想象,我朋友的母亲,注意到我喜欢她做的辣咖喱,一定也同样得出结论,我是一种她尚未认识的婆罗门,或者我前世是婆罗门,这次为了赎罪而降生在欧洲,她可以这样欢迎我。无论如何,她收留了我。她只说泰米尔语。我深感遗憾,无法与她进行超过微笑的交流。
自然,我们构想了一起读梵语的计划,但我朋友的梵语知识太好了,而我的太有限了,这项活动并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维杰亚拉加万是个讲故事成瘾的人。稍加提示,甚至完全不提示,他就会开始讲述他钟爱的《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或者有时他会引用并评论梵语或泰米尔语的格言诗、情诗或神秘主义诗歌。古印度文化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它涵盖了从逻辑、语法和形而上学最抽象的精妙之处,到最炽热的感官享受,再到最纯粹的神秘主义。维杰亚拉加万带我超越了我在巴黎大师们那里得到的启蒙:正是 благодаря 他,我才得以真正沉浸在这些文化财富中。
后来,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他送给我一条婆罗门圣线。这发生在达卡 (Dacca),在那里他还告诉我:“如果你留在印度,随着习俗变化如此之快,等我女儿到了结婚年龄,你会娶她的。” 她是个迷人的女孩,七岁。他在开玩笑——但是,像往常一样,只是部分玩笑。他真的认为仅仅十年就足以让这样的婚姻被他母亲接受吗?维杰亚拉加万自己是在童年早期结婚的,他的妻子在还是个小女孩时就来和他家人住在一起了,远在他们能够完婚的年龄之前;他对遵循这种安排感到庆幸。在他游历欧洲和美国期间,我确信他始终对妻子绝对忠诚,就像他始终保持严格的素食主义一样。我认为这与其说是因为不忠,或者吃鸡蛋或肉,在他眼中构成了罪过;如果他,例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肉,他事后不会感到任何悔恨,事实上他自己就向我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对他来说,罪过意味着违背了他自愿许下的誓言。有一天在巴黎,当他明显带着钦佩谈论一位女士时,我父亲问他是否没有感到任何“诱惑”("temptations")。维杰亚拉加万回答说:“我可以欣赏一辆劳斯莱斯 (Rolls-Royce),并乐于想象片刻它属于我,而不会被诱惑去偷它。” 当他在旅途中感到“肉体的刺痛”("prickings of the flesh"),用拉伯雷 (Rabelais) 幽默的说法,他会禁食两三天。要是他能更经常禁食就好了!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非常肥胖了。长远来看,他的心脏无法承受移动如此沉重身躯的负担。他的儿子向我描述了维杰亚拉加万的去世:感觉临终将近,他要求听他最喜欢的毗湿奴 (Vishnu) 礼拜仪式段落,正是这些诗句伴随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刻。
因此,维杰亚拉加万是我1930年招募的新成员,很快我们开始为系的未来制定计划。我尽可能多地继续旅行。大学里假期频繁,我充分利用了它们。自然,所有穆斯林节日都放假。此外,由于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并且寻求(按照良好的穆斯林传统)讨好当局,大学也热衷于遵守英属印度的所有假期:圣诞节和复活节,以及皇室生日。而且,尽管有官方名称,大学以不搞宗派主义而自豪:有少量印度教学生,大部分是本地招收的,还有一位学者 (pandit) 教授梵语和印地语 (Hindi)。事实上,阿里格尔镇的大多数居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和睦相处。至少,在我逗留期间,我很幸运没有目睹任何如今仍然是印度社会溃烂伤口的社群间冲突,我当时的印度朋友普遍将其归咎于警察挑衅和英国殖民政治的精巧手段。无论如何,出于对周围居民的礼貌,大学也遵守主要的印度教节日。对我来说,这些中断为旅行提供了受欢迎的机会。
铁路系统非常出色。所有印度铁路的总时刻表成了我的睡前读物,至今我仍不能不想起它而不感到怀旧。印度的距离很长,但即使没有飞机,它们也并非遥不可及。一夜的旅程不算什么;24小时的旅程几乎不算什么。每个人都有便携式卧具铺在卧铺上。当时有四个等级:一等、二等、“中间等”("intermediate") 和三等。一等舱主要是英国人和担任要职的富裕西化印度人乘坐。我更喜欢二等舱,在那里我遇到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印度人。乘坐“中间等”舱的花费较少的旅客英语懂得不多;因此,我只在和朋友一起时才乘坐中间等舱。三等舱是为大众准备的,拥挤不堪、五花八门的人群会把车厢挤得满满当当。我避开它并非出于阶级偏见,首先是因为身体上的不适,其次是因为语言障碍会把我与同行的旅客隔离开来。确实,我和我的朋友阿比德开始学习乌尔都语,这种语言虽然用波斯字母书写,但在结构上与印地语相同。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从未找到时间达到流利的口语或阅读水平。此外,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它也没什么用。
在整个印度,传统的好客仍然是规则。根据某些古典文献,穷人是指无法在家中接待许多客人的人。除非非常不幸,否则无需求助于旅馆。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要去某某地方时,他总会问我打算住在谁家。如果我说我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我就会得到一个地址。有时,在火车上,一位同行的旅客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如果需要,他会带我回家。确实,这样的客人不需要单独的房间;一个带帆布床的露台或门廊就是旅行者铺开卧具所需的全部。浴室很少配备自来水。印度人很少邀请英国人到他家,后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很不自在。但对印度人来说,我不是殖民者。确实,在许多方面,法国人对待印度支那人 (Indochinese) 比英国人对待印度人要糟糕得多,但印度人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我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不久之后,我采用了“阿奇坎”(achkan),即“尼赫鲁束腰外衣”("Nehru tunic"),这是许多同事和大多数学生穿着的实用服装。我开始穿黑色哔叽布的,但后来,出于对我很快结交的支持甘地 (Gandhi) 的朋友的同情,我也做了一件土布 (khadi) 的:这是按照甘地的教导手工纺织的粗布。我还戴着同样面料的“甘地帽”("Gandhi cap"),在法国可能被称为警察帽。从远处看,我可以冒充印度人;有时,心血来潮时(自从很久以前读了安德烈·纪德 (André Gide) 的《梵蒂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 以来,我就乐于冒充非我之人),我会自称是克什米尔本地人。克什米尔人肤色很浅,他们的方言与其他任何方言都如此不同,以至于在省外他们只能说英语。经过系统的学习,我不仅习惯了所有类型的印度烹饪,甚至连最辣的也品尝得津津有味。我甚至喜欢嚼槟榔 (betel nut)。我的主人们很高兴发现我对他们的烹饪如此热情,乐于为我提供食宿和他们陪伴的乐趣。
因此,我在印度的逗留使我得以从一端到另一端游览它,从克什米尔到孟加拉,从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 (Cape Comorin)。不言而喻,我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在我设法看到的离阿里格尔或近或远的地方中,有马图拉 (Mathura)、斋浦尔 (Jaipur)、马德拉斯 (Madras) 和加尔各答 (Calcutta) 及其博物馆,桑奇 (Sanchi) 及其佛塔 (stupa),阿克巴在锡坎德拉巴德 (Sikanderabad) 的陵墓,维查耶那加尔 (Vijayanagar) 及其寺庙,以及德里 (Delhi),我曾多次返回那里。但是,除了重新点燃我的怀旧之情,这样一份随机的杰作清单又能有什么用呢?至于用华丽的辞藻描述这些地方,旅游指南和艺术史做得足够多了。只需说我很少感到失望就够了。需要补充的是,印度在风景方面不亚于其纪念碑吗?如果我克制不谈前者,并非因为我对它们的记忆不那么珍贵。
在这些旅行过程中,我也发现印度在数学家方面并不像我最初担心的那样贫乏。我在北部遇到过几位,1930年印度数学学会 (Indian Mathematics Society) 在特拉凡哥尔邦 (state of Travancore)(今喀拉拉邦 (Kerala state) 的一部分)首府特里凡得琅 (Trivandrum) 举行年会时,我在南部看到了更多。除了想见数学家,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印度南部。两三天的火车旅行似乎不再是令人生畏的前景。我出发了,只在马德拉斯停留。虽然我很想参观南部的大寺庙——坦贾武尔 (Thanjavur)、马杜赖 (Madurai)、甘吉布勒姆 (Kanchipuram) 等等——但时间有限,我不得不将这些访问推迟到另一个场合。我几乎不知道我将不得不等待三十多年。在马德拉斯,我遇到了阿南达·劳 (Ananda Rau),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分析学家,以及瓦伊迪亚纳塔斯瓦米 (Vaidyanathaswamy),也是一位友善的人,一位并非没有才华但范围相当有限的数学家。在他的陪伴下,我完成了从马德拉斯到特里凡得琅的旅程。
在这次会议上,我只遇到了南印度人。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都是婆罗门,从他们的名字和许多人额头上绘制的标记就可以认出。这些标记表明他们属于两大群体中的一个,称为湿婆派 (shaiva 或 ayyar) 或毗湿奴派 (vaishnava 或 ayyengar),取决于他们主要崇拜湿婆 (Shiva) 还是毗湿奴 (Vishnu)。那年数学学会的主席是一位来自班加罗尔 (Bangalore) 的极高种姓的婆罗门,他带着妻子和几位女眷及仆人随行。他立刻明确表示,他不会碰任何非这些妇女亲手准备的食物。种姓规则规定,一个好的印度教徒不得吃任何由他认为低于自己种姓成员准备的东西,也不能与任何来自这样种姓的人一起用餐。这位先生,作为学会主席,而且还是大君的私人客人,意在传达没有任何人,即使是大君专门为招待最尊贵客人而雇用的厨师,有资格为他准备食物。尽管人们假装对这种傲慢一笑置之,但它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主席是班加罗尔一所学院的教授。他的兄弟,一个修行所 (ashram) 的负责人,自认为是神的化身,我看到过他的一些宣言,在其中他充当上帝以第一人称说话的解释者。
我们享受了一次到科摩林角的精彩远足,那里是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在那里,我的同伴们并非没有感情地唱起了《致敬母亲》(Bande Mataram),这曾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颂歌,后来成为独立印度的国歌。我们还被邀请观看卡塔卡利 (kathakali) 表演。这种戏剧形式以舞蹈和哑剧表演《摩诃婆罗多》的片段。在场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是特拉凡哥尔邦的总理,他戴着庄严的头巾,形象威严。但我最清晰的记忆是一件既有趣又具有启发性的事件,值得在此叙述。
学会成员被安置在当地学院学校的宿舍里,并在学校食堂用餐。与印度北部相比,南部更持续地遵守着传统习俗。用餐时,每个人都盘腿坐在地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坐在单独的木块上。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是严格的素食,盛在铺在每个人面前地上的香蕉叶上。用右手吃饭,不用叉子或刀子,用左手喝水;饭前饭后仔细洗手。作为在场的唯一欧洲人,我被授予了住在“邦宾馆”("state guest house") 一个房间的荣誉,该宾馆通常为特拉凡哥尔邦的英国客人保留。第一晚我就是在这里吃的晚餐。当然,英国烹饪名声糟糕是有道理的,而在印度被称为英国烹饪的东西甚至更糟。此外,独自用餐的前景并不令人愉快。因此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希望和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
我知道我的请求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欧洲人,我低于他们的种姓,或者至少在体系之外。第二天,在食堂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让我和瓦伊迪亚纳塔斯瓦米以及一两位显然习惯于与欧洲人交往的同事坐在一张桌子旁。我们吃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饭菜。我假装无知,甚至坚持要在主餐厅本身吃下一顿饭,并且即使到这种极端程度也得到了满足。
但第二天,我发现房间被重新安排了。有人向我解释说,我们这群人太多了,容纳不下所有人,所以开了第二个餐厅;我被护送到了这个房间。那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年轻人,气氛很愉快。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
询问此事毫无意义,所以我从未问过。一些年长的同事,也许没有直接抗议我的存在,但一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遵守传统字面意义的权利;如果年轻人希望偏离它,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就这样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令所有人表面上都满意。
在这次会议上,我像在别处一样,被打动的不是数学水平——充其量是平庸的——而是年轻一代中显而易见的热切和思想开放,这与他们长辈陷入的常规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认为这是印度数学未来的好兆头。这种乐观主义实际上有些过早,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我在特里凡得琅的经历也让我反思了南部婆罗门在当代印度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感谢维杰亚拉加万,我已经对这个作用有了一瞥。观察到在过去一两个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中,犹太人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其实际人数重要得多,这 hardly original。这在科学领域尤其如此,首先是在数学领域。在印度,南部婆罗门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仅举一例,当我1968年访问孟买的塔塔研究所 (Tata Institute) 时,我可以看到数学专用楼层办公室门上的名字:绝大多数是南部婆罗门的名字,他们的名字甚至比西方国家犹太人的姓氏更具特征性。这种我在特里凡得琅意识到的类比需要解释,而解释显然既不在于裙带关系(尽管这有时在两个群体的成功中起作用),也不在于想象中的种族因素。然而,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神秘之处。
为了描述印度教社会,西方引入了“种姓”("caste") 这个词,它被广泛误解了。印度人更喜欢说“社群”("communities")。在这个意义上,“社群”并非基于种族或宗教来定义,而是通过特定的行为模式,包括内婚倾向、烹饪习惯和各种仪式。整个印度社会就这样被划分在一个体系中,这个体系包括了所有人,除了圣人,他们被普遍共识置于种姓之上,就像甘地这个最著名的现代例子一样。即使改变宗教也仅仅意味着离开一个社群并加入另一个。所有拒绝种姓制度的改革运动(包括很久以前的佛教;中世纪哲学家马德瓦 (Madhva) 的学派;以及上个世纪的梵社 (brahmo samaj))仅仅创造了额外的社群。不可否认,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种社会划分有所松动,尤其是在甘地影响下,这种松动是件好事。尽管如此,这个体系在印度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我们无法认真设想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在其本质上它并非等级制的,无论我们一些最好的社会学家可能相信什么:种姓的相对优劣绝非这个概念所固有的,并且在存在这种等级的地方,它们常常基于印度人完全意识到的主观因素。对于两个印度教徒,很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种姓比对方好。
据我所知,西方社会从未如此严格地分层;无论如何,“社群”的概念今天只能适用于少数群体,例如犹太人,或者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此外,如果情况允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脱离这些群体,这种可能性在印度不存在。这种差异无疑使得在我们眼中如此模糊和被误解的种姓概念,在印度教徒眼中却如此清晰。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犹太人和印度南部的婆罗门都是两千年来不懈地致力于语法和神学最抽象精妙之处的社群。对犹太人来说是研究《塔木德》(Talmud),这项任务常常父子相传;对婆罗门来说是《梵书》(Brahmanas) 和《奥义书》(Upanishads)。毫不奇怪,年轻一代,当他们的时代到来时,转向了科学,并且更倾向于最抽象的科学:这一趋势仅仅是千年传统的自然延伸。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成功日益与某些智力品质相关的社会中,犹太人和婆罗门都激起了他人的嫉妒,结果是西方的反犹主义,以及印度的非婆罗门政党和运动。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南部婆罗门似乎确实成为了西方犹太人在印度的同源物,针对他们的敌意采取了西方社会反犹主义所采取的某些相同形式(例如固定配额)。但直到后来,这些源于我在印度经历的想法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至于1930-31学年,并非没有波折。我的教学既受到我缺乏经验的影响,也受到学生准备不足的影响。维杰亚拉加万是我唯一可以指望提供帮助的人。系图书馆里唯一的英文教材完全过时了;我从马苏德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并开始与莱比锡 (Leipzig) 的书店进行谈判。我任命了科萨姆比 (Kosambi) 担任下一年的职位。他是一个思想独特的年轻人,刚从哈佛 (Harvard) 毕业,在那里他开始对微分几何产生兴趣。我在贝拿勒斯 (Benares)(现瓦拉纳西 (Varanasi))遇到他,当时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临时职位。我自作主张不仅在课程设置上,而且在考试制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后者坦率地说,是荒谬的。然而,这是英国人在整个印度建立的制度,我的计划让学生们陷入了混乱。我仍然被视为马苏德的走卒,一份乌尔都语的小册子流传开来,抨击他,并批评我将法国数学引入印度:根据小册子的作者,只有英国数学才适合印度人的思维。
马苏德认为,他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他曾在他手下担任部长)那里获得了用于设立两个资金雄厚的物理和化学教席的资金,这对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来说是一大成功。化学教席他任命了一位年轻的英国人,我无法欣赏他的优点,但觉得他很友好,他成了我的邻居。在物理学方面,马苏德认为他力排众议任命了一位德国人是巨大的胜利,这位德国人唯一的资格是爱因斯坦 (Einstein) 的推荐信,而在爱因斯坦眼中他的优点可能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失业的犹太人——因为他从未表现出任何其他品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认为任何欧洲人都足以胜任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为了使这项任命正式生效,程序要求召集一个特设委员会,并邀请一位外部专家参与。错误在于邀请了著名的 C.V. 拉曼 (C.V. Raman),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自己当时正好有一个学生在寻找职位。我相信这个学生并非没有优点;无论如何,他无疑优于马苏德的候选人。我也是委员会成员。马苏德在欧洲,用电报下达命令。违抗他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危机,我的委员会同僚们,而且他们完全没有资格判断问题的实质,绝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拉曼理所当然地被激怒了,威胁要揭发此事并制造丑闻。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维杰亚拉加万和我一起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大声疾呼只会加剧本已非常不适的局面。
1931年,暑假直到五月才开始。我决定在欧洲度过,部分原因是为了去莱比锡的书店,正式为我的系购买图书馆藏书。当然,我也在巴黎、哥廷根和柏林停留。就在我抵达巴黎时,布鲁诺·瓦尔特 (Bruno Walter) 正在香榭丽舍剧院 (Théâtre des Champs-Elysées) 指挥莫扎特 (Mozart) 全部伟大歌剧的系列演出。我有幸观看了这些演出,令人难忘。我只买了一系列演出的票,但被深深打动,以至于无论如何都想至少再听一次《魔笛》(The Magic Flute)。被告知一张票都没剩了,我穿上我的尼赫鲁束腰外衣,冒充一个专程来巴黎看这场演出的印度人。我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我如愿以偿了。
从欧洲返回阿里格尔,我发现那里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对整个大学,尤其对我个人而言。我在那里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这场失败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及我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仍然是一场惨败。维杰亚拉加万已经不在那里了。在我缺席期间,他成功申请到达卡的职位,并已经搬到了那里。我感到震惊和沮丧。后来他告诉我,在我去度假后,马苏德找他谈话,告诉他,他,马苏德,计划摆脱我,并把我的职位提供给他。维杰亚拉加万对这种我当然丝毫没有怀疑的欺骗行为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他抓住第一个机会就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
尽管如此,我仍在为系里酝酿更多的计划。书从莱比锡运到了,这是一套相当不错的基础教材和期刊,是我精心挑选的,作为严肃科学工作的基础。感谢科萨姆比,我并不孤单。我在德里遇到了乔拉 (Chowla),并计划聘用他。事实上,我唯一的关切就是聚集——在哪里并不重要——一个真正热爱工作的年轻数学家团队。我相信这样一个团体将对印度数学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也许我的推理是正确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更多时间,首先需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十一月,大学行政部门找了个借口与我发生争执。我忽略了寻求官方授权去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 参加一个省级科学院的成立会议。(命运弄人的是,多年后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我会因为类似的轻罪而被一位院长训斥。)但在阿里格尔,我还雪上加霜地拒绝帮助学生俱乐部选举计票。争吵迅速变得激烈。一月份,就在我写辞职信的时候,大学通知我我的合同被终止了。天真的我,甚至从未要求看过这份合同。毫无疑问,这幕剧是预谋好的。
几乎在几天之内,我发现自己失业了。确实,我曾向我的一些巴黎老师,首先是西尔万·莱维,告知了我的不稳定处境。我被保证,一笔来自后来成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的研究资助,将在我抵达法国时等着我。此外,马苏德在我被招募时给予我的薪水确实非常慷慨。虽然我生活时没有为未来储蓄的想法,但我也没有家庭负担,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笔让我能舒适生活几个月的钱。当时甚至没有货币兑换限制来阻止我在我想要的地方消费它。
圣诞假期期间,我刚和埃利·福尔 (Elie Faure) 一起访问了拉杰普塔纳 (Rajputana),他是一位医生,后来成为颇受尊敬的艺术史家。六十多岁的他决定环球旅行,在访问日本后,出于我未知的原因,在阿里格尔停留。无法想象比他更惬意的旅伴了。他不断地从他无限的故事库中汲取素材,从他对印象派画家的回忆到他的风流韵事和日本之行。描述一段让他饱受嫉妒折磨的恋情时,他告诉我:“如果我做了笔记,我会超越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碰巧我们抵达乌代布尔 (Udaipur) 的前一天,当地王侯(殿下马哈拉纳·萨希卜·巴哈杜尔 (His Highness the Maharana Sahib Bahadur),用他的官方头衔)计划了一场猎豹活动。福尔和我毫不费力地获得了陪同王侯的邀请。我们一起高高地坐在一头大象上,甚至使用了——也许是不审慎地——托付给我们的猎枪。我从未弄清楚我们的努力是否取得了任何成功。
一旦与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分离,我并不想念它。我有些遗憾我的努力失败了,但至少它们成功地在维杰亚拉加万、科萨姆比和乔拉之间建立了友谊的纽带,这三位年轻数学家在我看来是当时最有前途的。我也后悔不得不离开印度,而没有时间像我打算的那样认真学习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无论如何,我并不急于返回法国。
我制定了大胆的计划。一个是经由中国 (China) 和苏联 (Soviet Union) 返回。我的妹妹比我更了解远东局势,尽力劝阻我。另一个计划,涉及飞机、火车甚至巴士旅行,是访问波斯和土耳其 (Turkey)。西尔万·莱维建议我去日本 (Japan),那对我吸引力不大:埃利·福尔描述的极端军事化让我反感。
最后我采纳了一个更温和的计划。维杰亚拉加万邀请我去他在达卡的家,想住多久都行。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然后乘坐我惯常的里雅斯特劳埃德航运返回法国。途中我在加尔各答停留,那时它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据各方描述,变成贫民窟的集合。我不仅记得博物馆,那里收藏着理应著名的巴尔胡特 (Bharhut) 雕塑,还记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诗人,不是他的画家兄弟)的水彩画展,非常壮观。这次展览让我产生了去参观他的寂乡 (Santiniketan) 基金会的想法,这是一个非传统的机构,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教学结合在一个离加尔各答不远的乡村环境中。西尔万·莱维的一位学生在那里教藏语。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将我介绍给诗人,一位庄严的人物,他在公园里主持着场面,穿着华丽的紫色丝绸长袍,周围环绕着恭敬的弟子。
维杰亚拉加万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他和他的母亲、妻子以及他们可爱的女儿住在大学主楼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睡在一个有顶的门廊上。我面前是一棵开着大红花朵的树,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从未知道树的名字,也不知道星星的名字)。我喜欢认为它和《摩诃婆罗多》中纳拉 (Nala) 和达玛扬蒂 (Damayanti) 的插曲里,达玛扬蒂向之发表如此诗意演说的阿育王树 (ashoka tree) 是同一种。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用餐,遵守马德拉斯的习俗:穿着传统的兜提 (dhoti),我们坐在地上,由他的母亲和妻子侍奉。物理学家克里希南 (Krishnan)(拉曼的学生,即使没有分享他老师的诺贝尔奖,至少也分享了导致获奖发现的工作)是维杰亚拉加万的密友。我们在他花园的玫瑰丛中拜访了他。我们的团体由肖蒂恩·玻色 (Shotyen Bose) 完成,即所谓的爱因斯坦-玻色统计 (Einstein-Bose statistics) 中的 S.N. 玻色 (S.N. Bose)。
拉达克里希南 (Radhakrishnan),刚刚被任命为在沃尔泰尔 (Waltair)——位于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之间——新成立大学校长的哲学家,得知了我在达卡的消息。他提议让我担任他的数学系主任。我期待着很快返回法国;尽管如此,在与维杰亚拉加万商议后,在我看来,为了印度的数学事业,我没有权利拒绝——前提是我在选择数学家团队方面拥有全权 (carte blanche)。然后我被告知当地政治使得这个条件不可能实现,这个计划也就无果而终了,除了几年后乔拉被任命担任该职位。
这些回忆若不最终包含一位对我来说不亚于维杰亚拉加万的挚友,就不算完整:扎基尔·侯赛因 (Zakir Husain)。我在巴黎遇到了他的弟弟优素福 (Yusuf),他正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告诉我的关于扎基尔的事情让我渴望见到这位哥哥,抵达阿里格尔后不久我就找到了他。他是帕坦人 (Pathan) 后裔,但出生在联合省(“U.P.”,今天称为北方邦 (Uttar Pradesh))的一个村庄。他曾是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学生,并且是那些在甘地影响下离开大学创办一个实验性机构并成为其校长的人之一。这就是国立伊斯兰大学 (Jamia Millia Islamia),或多或少受到泰戈尔及其在寂乡的学校的启发,在某种意义上是它的穆斯林版本。像泰戈尔的基金会一样,扎基尔的既不是学校也不是大学。其目标是为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符合甘地贫穷原则(在欧洲会被称为方济各会 (Franciscan) 原则)的整体教育。国立伊斯兰大学坚持伊斯兰教的理想和实践,但并非宗派机构:那里有印度教学生,我访问时甘地的儿子德奥达斯 (Deodas) 正在那里教书。
在印度的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纯粹的英国世界观不适合印度。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苏德才把我带到阿里格尔。我相信,扎基尔是最早不仅理解这个概念而且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之一。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曾在柏林学习了几年,并在那里提交了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他的德语几乎和他的乌尔都语、英语和波斯语一样好。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把他的弟弟优素福送到了巴黎。
我来到阿里格尔时,扎基尔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了。感谢优素福,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他立刻提出,只要我想去德里,就做我的主人,事实上我总是他的客人,甚至在我最后一次访问时也是如此:那是在1968年初和我的妻子一起。那时扎基尔已经是印度共和国总统,他安排我们住在前总督府,那座骄傲的总督官邸(改名为总统府 (Rashtrapati Bhavan):“帝国主人的住所”),欢迎同样热情、同样朴素,就像早些时候,他只有一个没有电的穷房子,在旧德里的一个偏远地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女儿以及必不可少的男仆住在一起。我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她遵守普达,这是印度几乎所有穆斯林以及(可能是在模仿下)北部某些印度教徒遵守的幽居习俗。当我足够了解扎基尔可以问他这个问题时——也就是说,几乎是立刻——他告诉我:“她就是那样被抚养长大的;我不试图以任何方式影响她。我想她会永远遵守这个习俗,而我的女儿永远不会。” 他的预言成真了。
这是该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凡的时刻。当我抵达印度时,甘地正准备通过他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来发起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以抗议政府的盐税。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人们装作不把他当回事。虽然马苏德和我大多数同事绝非亲英派,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忠诚派,出于政治信念和传统。他们没有准备好理解甘地即将掀起一股足以席卷全印度的浪潮,仅仅通过在海边一个小锅里准备一把盐。甘地自己很清楚。抛开所有道德判断,可以说他和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传代理人之一。
就像在季风季节,印度报纸追踪其从科摩林角到喜马拉雅山的进展一样,同样地,在1930年春天,它们追踪了甘地进军的进展。人群在每一个转折点都膨胀。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甘地很快被监禁,民族主义政党,称为印度国民大会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被宣布为非法。对此可能性已经做了周密的准备。注定要保持秘密状态的人员经过精心挑选,数量限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该党在每个村庄都有分支机构。随着地方组织的已知成员被投入监狱,他们会指定继任者,后者又会轮流加入他们。有些人是出于无私的理想主义,另一些人,毫无疑问,是出于对未来政治生涯的野心。渐渐地,监狱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争夺这份荣誉的人。政府不知所措。必须承认,与在别处所见相比,所使用的镇压措施可以说是温和的。有人告诉我,作为他所谓的“政府暴行”的一个例子,他在入狱体检时被脱光了衣服。我能想到的只是我在罗马征兵委员会面前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公民不服从运动之所以取得相当不流血的成功,是因为甘地对抗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 (Stalin),而是英国人。据我所知,他从未明确说过这一点,但他太现实了,不可能不知道。
尽管扎基尔·侯赛因与运动领导人关系密切,但他与该党没有正式联系。在整个运动期间,他继续致力于他的教育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能够如此频繁地见到他。我利用拜访他的机会,尽情欣赏旧德里的辉煌:红堡 (Red Fort)、大清真寺 (Jami Masjid,“星期五清真寺”)。自然,我也渴望见到甘地享有盛誉的核心圈子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甘地本人。感谢扎基尔和其他朋友,我在那两年里,在他们不在监狱的短暂时期,见到了其中一些人。此外,这些人乐于尽可能地让所有人接近。就这样,有一天在阿拉哈巴德,维杰亚拉加万和我和甘地同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的朋友把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就在那时,给我们端来了茶——用咖啡杯装着。甘地笑了。“很容易看出你不是英国人,”他轻声说。“英国人绝不会容忍这种失礼行为。”
在同一场合,我结识了著名的拉贾戈帕拉查里亚 (Rajagopalacharya),被称为“南方甘地”("Gandhi of the South"),他将在36年后在马德拉斯告诉我(那时他已近90岁):“我完全记得你;你一点也没长进。” 我早在1930年秋天就在度假小镇马苏里 (Mussoorie) 见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当时我正在从雨季末在阿里格尔染上的发烧中恢复。他因医疗原因被短暂 reprieve from prison,正在他父亲莫蒂拉尔 (Motilal) 的房子里休养。他向我解释说,一旦印度开始让英国付出的成本超过她带来的收入价值,她就会获得独立:运动的目标是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
几乎所有曾与甘地亲近并直接受到他影响的人,似乎都承袭了圣雄 (Mahatma) 人格的某些方面,当然他们不这样称呼他:对他们来说,他是甘地吉 (Gandhiji),或者更好的是巴普吉 (Bapuji),一个表达孝子般深情的称谓。扎基尔采纳了甘地的贫穷态度和绝对奉献精神。他没有表现出那种似乎从不允许甘地休息片刻的、消耗一切的活动需求,无论是清理厕所还是推翻印度政府。为此,扎基尔的身材太庄严了。他欣然自称为“我的球形”("Meine Kugelhaftigkeit (My Sphericity)")。在甘地被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所驱动的地方,扎基尔表现出客观头脑的完美平静。无论是谈论他生活中的琐事还是他国家的未来,他总是用最日常的语气说话;他的言语从不华丽或 pretentious。我确信,这一定是他与尼赫鲁和真纳 (Jinnah) 在准备分割印度时在阿里格尔进行的著名会谈中所采取的日常语气。扎基尔恳求他们不要让局势发展到那一步,并迫使这两个骄傲的人物互相拥抱。这次会谈没有产生更多结果,我相信,是他一生中巨大的失望之一。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段插曲,但多年后扎基尔来芝加哥看我时,我问了他关于分治及其周围屠杀的事情。我问他自己的生命是否曾处于危险之中。“非常危险,”他告诉我,“而且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 生病后,他决定去克什米尔休养。完全没有注意日期(“像个傻瓜,”他说),他预订了就在英国政府即将停止存在、印度将被一分为二的那天晚上的卧铺。他在指定时间离开了德里。半夜,火车在新边境被拦下,穆斯林被带下车杀害。在另一边,印度教徒正在被杀害。毫无疑问,无法判断屠杀是从哪里开始的。一个声音向他喊道:“博士先生”("Doctor Sahib")(这是他在他的国立伊斯兰学校被亲切称呼的方式),“你在这里做什么?马上跟我来。” 他被带到火车站的一个办公室里锁了起来。门口站了一个哨兵,并被告知如果他看守的人发生任何意外,他将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价。扎基尔叙述这件事时,就像在讲述最平庸的事件。
在阿里格尔期间,我常读《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北部的主要日报。在英国法律下,新闻界享有很大的自由;谁会想到四十年后,尼赫鲁的女儿兼继任者会试图扼杀它呢?当我有一天读到甘地在德里与总督本人进行谈判时,我搭上第一班火车,飞速赶到扎基尔家。我发现他对处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边缘和我一样好奇。他带我去了富有的医生安萨里博士 (Doctor Ansari) 的家,他是甘地的私人朋友,甘地每次来德里都住在他家。像印度这种场合的常态一样,气氛类似于狂欢节或朝圣。谈判持续了数天,为伦敦圆桌会议 (London Round Table Conference) 做准备。每天,一辆劳斯莱斯从宫殿派来接甘地;它会在傍晚祈祷 (gayatri) 时间之前把他送回安萨里博士家,祈祷由一位名叫米拉本 (Miraben) 的忠实英国女弟子演唱。尤其是在祈祷时间,各种各样的人都挤过来看甘地:即使是贫穷的村民也会远道而来见他。在印度,见到(darshan)一位伟人,尤其是一位被视为圣人的人,具有宗教价值,类似于教皇为一群天主教徒祝福。
米拉本的声音非常动听。据一个关于她的故事说,她曾向甘地抱怨她的头发常常引起男人过多的钦佩。甘地回答说:“如果它这么困扰你,你只需要把它剪掉就行了。” 她剃了光头。正是米拉本承担了为巴普吉准备膳食的责任,这项任务她绝不会交给任何人。
在他每周守默日那天,甘地不去总督府。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在那天陪他散步的一小群追随者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试图跟上他而气喘吁吁。另一天,碰巧总督(这是欧文勋爵 (Lord Irwin),后来成为哈利法克斯勋爵 (Lord Halifax))希望避免因晚餐而中断谈话,邀请甘地在宫殿用餐。甘地说:“那不可能;米拉本已经准备好了我的饭菜。” 总督建议把米拉本准备的食物带到宫殿,甘地接受了。就这样,在这个许多地位显赫的印度人曾以能被邀请哪怕只喝一杯简单的茶而感到荣幸的宫殿里,在这个只有穿着正装才能进入、只有用最精美的瓷器才能用餐的地方,甘地,穿着他的兜提,吃着他的一盘扁豆——最卑微印度农民的典型食物——由总督穿着制服的仆人端给他。这件事具有明显的象征价值和宣传潜力,报纸第二天没有不强调这一点的。成群的印度农民,吃着他们简朴的晚餐,从那时起就知道甘地在总督宫殿里分享了同样的饭菜。
在另一个场合,我几乎目睹了一场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骗局——其部分目的可能是为了嘲弄英国行政当局。在这方面它成功了。印度国民大会党非常民主的章程只授予中央委员会一年的权力。这些权力每年必须通过党代会,即由600多名地方和省级代表组成的类似议会的会议(党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的投票来更新。那年,尽管该党处于非法状态,会议还是在德里召开了。自然,警察知道了,但每天有无数人群通过火车或汽车、步行或骑自行车,或乘坐牛车进出德里,不可能真正检查每个人的身份,只有大约一百名代表被拦截。晚上,所有其他代表都收到书面通知,要求早上六点在旧德里中心主干道月光集市 (Chandni Chowk) 集合。警察当然发现了,并采取了相应行动。凌晨三点左右,所有代表都被信使口头命令四点集合的消息叫醒。于是,四点钟,巡逻月光集市的两三名警察被大批代表淹没。主席立即通过口头表决指定,爬上了一辆汽车的车顶。同样通过口头表决,通过了一些决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得到了更新。当警察大部队赶到时,代表大会已经处理完了当天的事物。大多数代表按计划被送往监狱,国大党赢得了胜利。那天早上从阿里格尔抵达,我几乎从扎基尔那里听到了所有这些细节;其余的我第二天从阿查里亚·克里帕拉尼 (Acharya Kripalani) 那里得知,他策划了整件事。他当时选择暂时保持地下状态,我在他未婚妻家人的陪伴下见到了他,他正躲在那里——如果那能被称为躲藏的话。如果我对情报部门效率还保留着任何从吉卜林 (Kipling) 那里获得的宏伟观念,它们在那天就会被摧毁。
英国人,在他们那边,也在寻求宣传,但不太成功。1932年,当需要任命欧文勋爵的继任者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从天而降——字面意义上——新总督来创造奇迹。由于波音飞机尚未发明,他被安排乘坐一艘飞艇,结果飞艇在离贡比涅 (Compiègne) 不远处起火坠毁。我当时在达卡。报纸以最恰当的悲剧性措辞宣布了这场灾难。整天,人们都会带着灿烂的笑容互相打招呼,说些诸如“你对这场悲剧怎么看?太可怕了,不是吗?”之类的话。
所有这些时间里,数学方面发生了什么?在那方面也没有闲着。我在丢番图方程上陷入了僵局。阿达玛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建议是放弃问题几年,以便以后能以全新的头脑重新审视它。在他的讨论班上,他经常强调当时所谓的“遍历假设”("ergodic hypothesis")。在这个主题上,他从未超越庞加莱和玻尔兹曼 (Boltzmann)。甚至在离开法国之前,我就想过将冯·诺依曼最近关于希尔伯特空间 (Hilbert spaces) 中酉算子 (unitary operators) 的工作应用于这些问题。1931年我与冯·诺依曼谈论此事时,在我看来这个想法他当时还没想到,他对此表示了兴趣。当我猜想了被称为L²意义下的遍历定理 (ergodic theorem in the L² sense) 的真理性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我与埃利·嘉当谈论此事时,他反对说这个发现在研究微分方程方面过于笼统和不精确,无法真正有用,我最终被他说服了。我曾一度冲动想涉足天体力学 (celestial mechanics),我知道西格尔正在研究它;我很快就放弃了。无论如何,我回到了庞加莱著名的关于旋转数 (rotation number) 的定理;我找到了一个证明——而且是优雅的证明——我希望它能将该定理推广到二维以上的环面上;但这个意图没有实现。无论如何,我想将它推广到环面上所有没有奇点的一阶微分方程,以及后来推广到更高亏格紧曲面上的方程。对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被 H. 克内泽尔 (H. Kneser) 解决了,我从未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证明。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根本没走多远。回到巴黎后,我设法让我的朋友马尼耶 (Magnier) 对此产生了兴趣,但就在他开始取得成果时,环境迫使他放弃了研究。
我在多复变函数方面取得了更多成功。我已经思考这些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离开巴黎前,我和亨利·嘉当 (Henri Cartan) 就此进行了几次谈话,这重新激发了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也许我们的讨论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法国传统教导说,单变量函数理论由柯西积分 (Cauchy integral) 主导;事实上,它只是众多可用工具之一,但我认为我通过证明一个将柯西积分推广到非常一般的“伪凸”("pseudoconvex") 域的公式,取得了重大进展。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数学家都经历过,即使只是很少几次,那种清醒的亢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奇迹般地相继出现,而潜意识(无论人们如何解释这个词)似乎在其中扮演着角色。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庞加莱描述了他如何在这样的时刻发现了富克斯函数 (Fuchsian functions)。关于这种状态,据说高斯 (Gauss) 曾这样评论:“构思是快乐的”(Procreare jucundum);然而他补充道,“但分娩是痛苦的”(sed parturire molestum)。与性快感不同,这种感觉可以一次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一旦你体验过它,你就渴望重复它,但无法随心所欲地做到,除非或许通过顽强的工作,它似乎以其出现来回报这种工作。诚然,所体验到的快乐不一定与其相关发现的价值成正比。
我在哥廷根时曾因丢番图方程而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我曾怀疑,并担心,它们是否还会再来。当它们真的回来时,我欣喜若狂。我当时在阿里格尔,维杰亚拉加万在达卡。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新的多复变函数理论今日诞生,”他开玩笑地回复道:“祝贺。电告母亲健康状况。” 我当然是在夸大其词;但也许我对我的发现感到高兴并非完全错误,它与斯特凡·伯格曼 (Stefan Bergmann) 同时期获得的结果相似,但也许更完整。我做的第一个应用是解决了一个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多项式级数的问题。冈洁 (Oka),对这个他做出了如此宝贵贡献的理论非常了解,很久以后向我保证,我的发现曾在一段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如何,这个结果为我赢得了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欣慰的赞誉。1932年5月我回家途中,在罗马停留看望维托·沃尔泰拉并向他解释我的公式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公寓后面,对他妻子喊道:“维吉尼亚!维吉尼亚!韦伊先生证明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定理!” (Virginia! Virginia! Il signor Weil ha dimostrato un gran bel teorema!)
注释:
¹ Rameau's nephew... recounted with such gusto: 指狄德罗 (Diderot) 的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其中拉摩的侄儿讲述了各种社会见闻和讽刺故事,包括一个关于阿维尼翁 (Avignon) 叛教者的故事。韦伊用此比喻他听到的关于海得拉巴宫廷阴谋的精彩程度。 ⁷ cum tacet nox: 拉丁语,意为“当夜晚寂静时”。
第五章 斯特拉斯堡与布尔巴基
(Chapter V Strasbourg and Bourbaki)
当我在印度时,母亲一直让我了解我妹妹(我们在家里称她为“女巨魔” - trollesse)在勒皮 (Le Puy) 多彩多姿的生活,她在那里获得了她作为女子中学哲学教授的第一个职位。她在那一年及随后几年的活动,佩特尔芒 (Pétrement) 的传记中有生动的细节描述;我在此不再赘述。只需说,因为西蒙娜 (Simone) 胆敢在公共广场上与失业工人握手,然后陪同他们的代表团去市议会,学校行政部门曾威胁要对她进行纪律处分。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正与阿里格尔的行政部门进行着我自己的斗争,自然地,我对妹妹对抗当局的方式感到着迷。我给她写了一封祝贺信,称她为“惊人的现象”("Amazing Phenomenon")——她回信时则哲学地称我为“本体”("noumenon")。勒皮属于克莱蒙 (Clermont) 学区。1932年5月我返回巴黎途中,在克莱蒙停留,那里有我的朋友,我趁机拜访了学区长。他对妹妹的壮举似乎颇为 amused,这无疑给他例行的行政工作带来了有趣的消遣。他告诉我,勒皮的气候“对她不好,真的不好”。得知那时她自己也希望调到别处,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友好地告别了。
回到巴黎后,我询问了数学方面的空缺职位,被告知马赛 (Marseilles) 有一个。在圣米歇尔大道 (Boulevard Saint-Michel) 上,我遇到了著名的当茹瓦 (Denjoy),他对我的情况表示了友好的兴趣,并问我:“年轻人,你在编制 (cadres)¹ 内吗?”我完全不知道编制除了装裱画作还有什么用;在他看来我一定显得很愚蠢。“但是,”他对我说,“这对你的退休金 (retirement pension) 非常重要。” 这最后一个词对我来说几乎和编制一样没什么意义,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的建议是多么中肯。他离开时对我说:“年轻人,考虑一下你的退休问题。”
在教育部,我被保证将被任命为马赛大学 (University of Marseilles) 的讲师,并被建议写信给我未来的院长。得知他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我很高兴,于是称呼他为“先生暨亲爱的老学长”("Monsieur et cher Archicube")。我很快发现他对这种称呼感到震惊,并且毫不掩饰他的不快。他告诉我他计划让我教“普通数学”("general mathematics") 课程,这是为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后来被称为“预科”("propaedeutic");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这项任务几乎无法激发我的热情。他敦促我在学年开始时就到马赛,不要等到我的任命正式生效。“你不会想看到你的课程被你的某个同事破了处吧,”他写道。我对这种“破处”毫不在意。最终我的任命在教育部的官方公报上宣布了,生效日期为12月1日。我通知院长我将于该日期到达马赛,不会提前。他很清楚他不能要求更多。
与此同时,我利用夏天和秋天去旅行了。印度之后,我很好奇想看看英国人在他们本土的样子。因此我在英国 (England) 待了几周,在那里我对剑桥 (Cambridge) 及其学院产生了持久的好感。我在曼彻斯特 (Manchester) 拜访了莫德尔 (Mordell);他亲切地欢迎了我,当我告诉他没有他1922年的文章我就无法完成我的论文时,他似乎感到受宠若惊——然而,他对我的论文却毫无好奇心。这种缺乏兴趣几乎不足为奇。早在印度时,当 C.V. 拉曼 (C.V. Raman) 问我有多少人读过我的论文时,我回答说(想到西格尔 (Siegel) 和阿廷 (Artin))“肯定一个,也许两个。” 拉曼为我的这种缺乏成功而同情我,并惊讶地看到我对此并不失望。在剑桥,R.E.A.C. 佩利 (R.E.A.C. Paley) 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比我小一岁,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分析学家。第二年,他在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s) 的一次滑雪事故中去世。我们的谈话转向了比较我们的工作方法。起初,我们似乎完全不在一个波长上。最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他只有在与他人竞争时才能富有成效地工作:身边有一群同伴激励他更加努力,试图超越他们。相比之下,我的风格是寻找那些我觉得完全没有竞争的课题,让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思考多年。毫无疑问,每个科学学科都有容纳这种性情差异的空间。某个研究者主要是被赢得诺贝尔奖的希望所驱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在我看来,印度教的知识之神象头神 (Ganesh),会为他的每一位追随者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诱饵,无论高尚还是粗俗。
夏天剩下的时间我在瑞士 (Switzerland) 度过,九月份国际数学家大会将在苏黎世 (Zurich) 举行。天气对这次活动很友好。湖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短途旅行,即使一位执意用他最新发现轰炸我的同事也没有破坏气氛。埃利·嘉当 (Elie Cartan) 发表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演讲,语气平静,就像有一天我们在盖-吕萨克街 (Rue Gay-Lussac) 散步时他对我说的那样:“我正在研究位置分析 (analysis situs),我想我或许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苏黎世博物馆正在展出毕加索 (Picasso) 的展览。无论对错,在我看来,他的艺术将深刻的严肃性与恶作剧并置——这种混合对我内心仍然存在的那个师范生来说,并非没有魅力。我们数学家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所谓的“危机”("the crisis")。大会出席人数众多,但还不至于让人迷失在人群中——这种感觉自那时以来破坏了我参加的许多其他会议。最重要的是,我还年轻。苏黎世在我记忆中是我参加过的所有大会中最美好的。
从苏黎世回来后,我还有几周的自由时间,我在汉堡 (Hamburg) 和柏林 (Berlin) 度过。因此我有机会在汉堡更好地了解了阿廷 (Artin),在柏林听了一场布鲁诺·瓦尔特 (Bruno Walter) 指挥的音乐会和一场《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s) 的演出。这次旅行之后,我必须去马赛,那里的职责既轻松又乏味。幸运的是,对我的财务状况来说,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以其缩写 CNRS 更为人所知)在那年成立了,对其将扮演的角色有些混乱。有人想到用它作为向那些对当时刚刚开始被称为“研究”("research") 表现出某种倾向的大学教员发放补充收入的手段:直到那时,这被称为“个人工作”("personal work")。我被告知我已被选中获得这样一笔资助。结果,几年来每三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张国家财政部开出的支票,我会在巴黎里沃利街 (rue de Rivoli) 兑现。当人们问我妹妹她哥哥是做什么的时,她会回答:“他做研究。”“研究什么?”“如何从政府那里搞钱。” 我从印度带回来的钱让我感觉更加富有了。我习惯了乘坐卧铺车旅行。就像印度铁路的总时刻表曾是我忠实的床头伴侣一样,现在我总是随身带着米特罗帕 (Mitropa) 年鉴,上面有所有主要国际列车的时刻表。就这样,1933年一个冬夜,我发现自己在魏玛 (Weimar),看到当地剧院张贴着《特里斯坦》(Tristan) 的海报,这家剧院声誉不错。当我在售票处要座位时,被告知所剩座位不多,我只能有什么要什么。人们似乎都在专注地盯着我看,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中场休息时在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同一个方向。当我问:“出什么事了?”(Was ist los?) 时,我被告知:“那是元首。”(Das ist der Führer.) 我没有试图靠近他。后来我才知道,我亲历了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希特勒 (Hitler) 刚刚被归化为图林根州 (Land of Thüringen) 的“公民”("citizen"),正作为魏玛贵族的客人。
马赛这座城市并非没有魅力——至少,在战争摧毁旧港之前是这样。尽管如此,我并不渴望留在那里。亨利·嘉当 (Henri Cartan) 已经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那里即将有一个职位空缺。我们俩同样渴望能在一起。1933年11月新学年开始时,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我在那里教书直到1939年,除了1937年在美国 (United States) 度过的一个学期。那是快乐而富有成效的岁月。
我来自“内地”("the interior")(阿尔萨斯人当时,也许现在仍然,用这个词指法国其他地区),首先被大学主楼的外观所震撼。这座建筑,像周围大部分街区一样,是威廉二世 (Wilhelm II) 时代的典型产物。我告诉嘉当,我担心自己无法适应它的丑陋。他对我说:“你会看到的,过一段时间就忘了”——但我从未习惯过。幸运的是,数学系宽敞舒适的设施包括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它不仅远优于当时“内地”省立大学所能找到的,而且——并非不重要地——对教员和认真的学生来说更容易访问。这个藏书的卓越主要归功于1918年以前在那里的德国数学家。然而,自那时起,十五年过去了,维持和发展这个优秀的设施并非易事。教员唯一的房间只是图书馆旁边一个类似过道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个人办公室。
我是大约十位来自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数学家之一,虽然分散在各省及巴黎的大学里,但自从离开高师后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中我最好的朋友,除了亨利·嘉当,还有让·德尔萨特 (Jean Delsarte) 和克洛德·谢瓦莱 (Claude Chevalley)。德尔萨特是南锡 (Nancy) 的讲师,他整个职业生涯都留在那里,不幸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因1968年的英年早逝而中断。谢瓦莱从德国回来,住在巴黎。他刚刚结婚并完成了他的论文。自从埃尔布朗 (Herbrand) 1931年7月登山遇难后,谢瓦莱和我是法国仅存的从事数论研究的人。每次我在巴黎,我们必定见面。
我曾在德国大学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许多朋友也仿效了。在那里,讨论班 (seminars) 在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法国当时经历过的唯一讨论班是阿达玛的——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指望模仿的模式。我们决定在巴黎组织一个讨论班,作为定期会面的论坛。当时,这样的事业需要一个“赞助人”(patron),哪怕只是为了能使用索邦大学 (Sorbonne) 的一个房间。儒利亚 (Julia),曾是我们在高师最年轻的老师,很乐意协助我们,所以这个讨论班被称为“儒利亚讨论班”("Julia seminar")。它一直持续到1939年。与阿达玛的不同,我们的讨论班每年关注一个不同的主题:1933-34年是群与代数 (groups and algebras),然后是希尔伯特空间 (Hilbert space),然后是埃利·嘉当的工作,等等。讨论班的油印笔记可以在亨利·庞加莱研究所 (Institut Henri Poincaré) 的图书馆找到。儒利亚是这个讨论班的常客,毫无疑问,他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将余下科学生涯致力于希尔伯特空间的想法。战后,“儒利亚讨论班”以一种相当不同的形式从灰烬中重生,被称为“布尔巴基讨论班”("Bourbaki seminar")——并非布尔巴基本身比早先儒利亚对“他的”讨论班有更多参与。
我经常去巴黎,有时在南锡停留。1929年,我家搬到了奥古斯特·孔德街 (Rue Auguste Comte) 3号一栋新建建筑的六楼公寓,他们为我在七楼租了一个工作室,可以俯瞰整个巴黎,从卢森堡公园 (Luxembourg gardens) 到蒙马特 (Montmartre) 的圣心大教堂 (Sacré Coeur church)。从这个距离看,这座纪念碑勾勒在地平线上,失去了其狰狞的特性,几乎成为无与伦比城市景观的一个基本元素。我的大部分藏书都放在这个工作室里。我的妹妹,继续着她多姿多彩的事业,开始相当频繁地在我们父母家接待她的德国朋友。我们的父母有时对这些冗长的访问感到困扰。这些德国人大多是逃离希特勒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当时我并不知道,甚至托洛茨基 (Trotsky) 也在1933年底在我工作室住过一次。所有这些来来往往让我得以一窥不断演变的政治局势,却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卷入其中的愿望。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谁是“左派”("on the left") 谁是“右派”("on the right") 是相当普遍的知识,我无疑被算作前者。但那里的政治热情并不强烈,我相处得最好的同事之一是一位地质学家,虽然 notorioulsy 保守,但也具有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我不能不与之分享。1934年6月,在我最后一次短暂逗留于希特勒德国期间(不包括几次去黑森林 (Black Forest) 的短途旅行),汉堡的一些年轻同事向我询问关于集中营恐怖行径开始流传的谣言。关于那个主题,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中有些人拒绝相信我,但有一个很容易就被说服了。后来,喝咖啡时,他开始用相当大的声音开“颠覆性”("subversive") 玩笑;他的妻子害怕了,告诉他:“汉斯,小声点!”他回答说:“我加入冲锋队 (S.A.) 的原因就是为了能说出我的想法。” 战后我再次见到了他;他没有发生任何不幸。1934年是长刀之夜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的年份,期间希特勒暗杀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合作者。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正在孚日山脉 (Vosges mountains) 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里批改学士学位会考 (baccalaureate examinations) 试卷。从那时起,我放弃了去德国旅行。斯特拉斯堡的吸引力之一是它靠近法兰克福和南锡的数学研究所,但前者已被政权 dismantling。只有西格尔在那里又待了几年,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无价的。我们几次在瑞士或黑森林度过冬季假期,正是在1935年圣诞节在阿罗萨 (Arosa),他告诉了我他关于二次型 (quadratic forms) 的发现。至于我在法兰克福的姨妈和她的家人,他们足够明智及时离开了德国。我后来在美国与他们团聚。
尽管我对在斯特拉斯堡的逗留感到满意,但我并未失去旅行的兴趣。对我影响最深的旅行之一是1934年8月和9月的一次西班牙 (Spain) 之旅,我访问了托莱多 (Toledo)、北部海岸和卡斯蒂利亚 (Castille)。我明智地将对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的访问推迟到以后,最终在1936年复活节成行。我在1925年获得的意大利语熟练程度让我能够轻松地,即使只是肤浅地,接触西班牙语——但这两种语言的音调非常不同,每种语言似乎都不可思议地适合某些风景和某些心境。你能想象在意大利举行斗牛 (bullfight) 吗?我确实目睹了这场与死亡的游戏,在当时还没有人想到锉掉公牛的角,让斗牛士 (torero) 能以廉价的英雄主义表演来玩弄动物。斗牛艺术 (tauromachy) 当时仍处于鼎盛时期。在马德里 (Madrid) 竞技场,我看到了传奇人物多明戈·奥尔特加 (Domingo Ortega) 表演的一场斗牛,即使无知的我也能欣赏,第二天的报纸上对其进行了 lavish detail 的颂扬。第二年,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 (Federico Garcia Lorca) 将发表他的《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挽歌》(Llanto por Ignacio Sanchez Mejias)。这首为一个著名斗牛士写的挽歌,在内战初期他被佛朗哥 (Franco) 的支持者暗杀时,成为了洛尔卡自己的安魂曲。早在1934年,洛尔卡的巨大成功是他的《吉普赛谣曲集》(Romancero Gitano),一本弥漫着死亡观念的薄薄诗集:但是,每次从西班牙文化的源泉中饮水时,难道不都是在杯底找到这个观念吗?诚然,据我所知,在西班牙没有像墨西哥 (Mexico) 那样实践的亡灵节 (Dia de los Defuntos) 的恐怖仪式;但西班牙内战难道不就是一场巨大的死亡之舞 (dance of death) 吗?“死亡万岁!”(Viva la muerte!),据说佛朗哥的一位将军在占领萨拉曼卡 (Salamanca) 后喊道。1934年,奥维耶多 (Oviedo) 报纸上描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局势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应对即将向当地极端组织运送武器的谣言,警察在道路上设立了岗哨。夜间一辆汽车驶过,没有听到停车命令。警察开了枪,有人被打死。今天,这样的事件可能会被当作“行政疏忽”("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而不了了之。但完全相同的事情在第二天晚上再次发生——却没有引起丝毫惊讶的表示。
我从西班牙带回的书中有一卷圣特蕾莎 (Saint Theresa) 的著作。由于熟悉《薄伽梵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熟悉印度教神秘主义诗歌(后者是译本),我对一种一直让我感到陌生的思维方式感到好奇。我也曾徒劳地寻找过十字若望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的作品。他诗歌中闪耀的美丽或许比圣特蕾莎更能打动我,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他的作品。我读了一点圣特蕾莎,很快就确信神秘主义思想在所有时代和地方本质上是相同的:阅读铃木 (Suzuki) 关于禅宗 (Zen) 的通俗著作很快证实了这个结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真理。如果我在这里提及它,并非愚蠢到要为此邀功;但我的这些思考似乎不可能没有以某种方式传递给我妹妹,也许她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影响。也许我们从未明确谈论过它。但我们彼此如此了解,以至于最轻微的暗示——最常隐藏在我们惯常的讽刺中——就足以让我们互相理解。
我1934年的假期结束于参观布尔戈斯 (Burgos) 附近的圣多明各-德西洛斯修道院 (Santo Domingo de Silos monastery),吸引我的是一座理应著名的罗马式回廊 (Romanesque cloister)。本笃会 (Benedictine) 僧侣,我相信他们隶属于索莱姆修道院 (Solesmes abbey),非常热情好客。在我们例行穿过回廊散步过程中的谈话里,有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谈到一位行为有些古怪的圣人时,一位僧侣温和地评论道:“但基督教就是疯狂”(el cristianismo es una locura)。这句完全正统的话常常在我思考我妹妹一生时浮现在脑海。
等待我返回斯特拉斯堡的是亨利·嘉当和“微分与积分学”("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课程,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在这里我得以逃脱了被强加“普通数学”的命运。我们对传统上用于微积分课程的教材越来越不满意。因为嘉当不断问我处理课程某个特定部分的最佳方式,我最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审判官”("Grand Inquisitor")。而我,就我而言,也未尝不向他求助。一个让他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将斯托克斯公式 (Stokes' formula) 推广到何种程度。
这个公式写成如下形式:
其中 是一个微分形式 (differential form), 是它的导数, 是它的积分域,而 是 的边界 (boundary)。如果例如 X 是一个定向球体的无限可微映像,并且如果 是一个具有无限可微系数的形式,那么这没有任何困难。这个公式的特例出现在经典论著中,但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应付这些。
埃利·嘉当在他关于不变量积分 (invariant integrals) 的书中,追随庞加莱 (Poincaré) 强调了这个公式的重要性,提议扩展其有效域。从数学上讲,这个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所能预见到的。它不仅牵涉到同调理论 (homology theory),以及其重要性刚刚显现的德拉姆定理 (de Rham's theorems);而且这个问题最终也为分布 (distributions) 和流 (currents) 的理论以及层 (sheaves) 的理论打开了大门。然而,暂时,嘉当和我的当务之急是在斯特拉斯堡教我们的课。1934年底的一个冬日,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结束我朋友持续不断的提问。我们有几位朋友负责在不同大学教授相同的主题。“我们为什么不聚在一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你就不会再用你的问题来烦我了?” 我几乎不知道,就在那一刻,布尔巴基 (Bourbaki) 诞生了。
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综合记忆,是事后回顾重构的,如果这次谈话真的或多或少像我记忆中固定的那样发生了,那么确定它的日期对布尔巴基的传记作者来说将至关重要;但唉,我不能。我们都知道,即使最清晰的记忆也没有刻上日期,也不会自动按正确的时间顺序排列。在许多方面,记忆就像一个装满旧照片或胶片条的盒子,其中一些已经半模糊;我们对其进行筛选并按时间顺序重新分类的各种尝试都遇到了困难,事实上我们的结论常常是错误的。因此,就像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布尔巴基确切的出生日期将永远模糊不清。这完全适合他。
无论如何,这次或类似的谈话很快导致了定期的会议,包括嘉当、德尔萨特、谢瓦莱、迪厄多内 (Dieudonné)、我自己以及其他几个人,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家现已倒闭的巴黎餐馆举行。刚才提到的这些人是与布尔巴基的联系一直持续到最后的人,也就是说,直到他们达到五十岁,他们自己指定的退休年龄。后来这几个人被称为“创始成员”("founding members")。
曾有过布尔巴基档案,德尔萨特很早就负责保管。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保存在南锡大学的数学系;现在它们在巴黎。不幸的是,关于这里讨论的时期,它们相当不完整。因此,以下内容主要基于我自己对布尔巴基的记忆。
一系列传说围绕着布尔巴基的名字聚集起来。在他的合作者中,不乏这些传说的宣传者。是时候揭开这些神秘面纱了。一旦集体署名出版的计划成形,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能用一长串名字填满整个封面。一个古老的高等师范学校恶作剧恰好在此时回到了我们的脑海。
当德尔萨特、嘉当和我在高师时,1923年新入学的理科班收到了行政部门官方信笺的通知,称一位名字有点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教授将在某某天、某某时间举办一场讲座,并强烈建议出席。演讲者是拉乌尔·于松 (Raoul Husson),一位更高年级的学生,一个温和的恶作剧者,他后来从事统计员的职业,之后转向了音韵学 (phonology) 和歌唱的科学研究,据说他在这些领域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贡献。1923年,他戴着假胡子,操着难以形容的口音,出现在新“入伍者”面前,发表了一场演讲,从一点点经典函数论出发,不知不觉地上升到最离奇的高度,最后以一个“布尔巴基定理”("Bourbaki's theorem") 结束,让听众惊得目瞪口呆。至少,传说是这样的,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即参加讲座的一名学生声称从头到尾都听懂了。
我们的师范校友从与拿破仑 (Napoleon) 有关的那位将军那里借用了他定理的名字。当我在印度时,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的朋友科萨姆比,他在一份他伪装成对某个省级科学院院刊的严肃贡献的滑稽注释中使用了它。我们小组很快同意让布尔巴基作为未来著作的作者。我们还需要具体说明我们的作者是哪个布尔巴基。这个问题在1935年具体化了,当时我们决心通过在法国科学院院刊 (Comptes-Rendus) 上以他的名义发表一篇注释来无可辩驳地确立布尔巴基的存在:我们必须决定一个名字。我未来的妻子埃夫琳,当时在场参与了这次讨论,成为了布尔巴基的教母,并给他取名为尼古拉 (Nicolas)。我们还需要让一位科学院院士提交这篇注释。我们毫不怀疑,科学院常任秘书埃米尔·皮卡,如果得知此事,会气得中风。我自告奋勇写这篇注释,并附上一封支持信寄给埃利·嘉当。
埃利·嘉当了解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计划。我为他编造了一份尼古拉·布尔巴基的传记,将他描述为波尔代维亚 (Poldevian) 后裔。我强调,提交注释的科学院院士有义务确定其科学内容的有效性,但无需核实作者传记的细节。一群科学院院士习惯于每周在会议前聚餐,仍然被称为“年轻院士午餐”("young members' lunch");说实话,他们的年轻那时已经相当古老了。埃利·嘉当出席了这次午餐,并在上利口酒时,就我的信咨询了他的同僚。他获得了他们的批准。至于注释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幻之处——尽管后来有人坚持认为其中包含一个错误:这难道是布尔巴基诅咒不可避免的效果吗?
波尔代维亚,布尔巴基的祖国,是高等师范学校另一个恶作剧的产物。据故事说,大约在1910年左右,几位师范生走遍了蒙帕纳斯 (Montparnasse) 街区的咖啡馆,召集了一群不同国籍的人,并将他们(在几杯酒的帮助下)转变为波尔代维亚民族的代表。学生们代表这些波尔代维亚人写信给著名的政治、文学和学术人物,开头是这样的:“您无疑熟悉波尔代维亚民族的不幸……” 同情的表示开始涌入。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安排了一场公开会议。主要发言人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演讲,结尾大致如下:“就这样,我,波尔代维亚议会议长,流亡在外,生活如此贫困,甚至连条裤子都没有。” 他爬上桌子,确实被看到没穿裤子。
为了结束关于布尔巴基名字和起源的这段题外话,我将补充一个更近期的插曲。大约在1948年左右,妮科尔·嘉当 (Nicole Cartan) 叫她丈夫接电话,说:“布尔巴基想和你说话。” 电话里亨利·嘉当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叫布尔巴基,我想见你。”“我想你有一把白色大胡子吧?”嘉当回答道。(这确实是我们喜欢想象我们创造物的方式。)“不,我没有胡子,我想见你。” 感到困惑的嘉当建议了一个他们见面的地方。在约定的时间,一位看起来很有身份的男士出现了,并立即出示了一份以希腊大使馆官员尼科莱季斯-布尔巴基 (Nicolaides-Bourbaki) 名义签发的外交护照。他解释说他的家族广为人知。布尔巴基家族的祖先包括两兄弟,他们在十七世纪克里特岛 (Crete) 抵抗土耳其人 (Turks) 的斗争中表现出色。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的领航员是一位布尔巴基。为了表示感谢,拿破仑授予这位布尔巴基让他的儿子在拉弗莱什军校 (Prytanée de la Flèche)——为军官和政府官员子弟设立的国家预备军校——接受教育的特权。这个儿子成为了一名法国军官,正是从他那里传下来了拿破仑三世 (Napoleon III) 的那位在历史上扮演了众所周知角色的将军。尼科莱季斯-布尔巴基认为他拥有一份完整的家谱,而这份家谱中没有数学家。他想知道,怎么会有数学著作以这个名字出版呢?嘉当告诉了他整个故事。从那时起,几年来,他一直是我们大会结束晚宴的常客。1950年,当我访问希腊 (Greece) 时,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他在雅典 (Athens) 亲戚的信,我在那里受到了极其盛情的接待。很可惜我没能也去克里特岛,因为我被告知,为了纪念尼古拉·布尔巴基,那里肯定会为我烤一只整羊。
但仅有作者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出版商。当时法国的数学出版市场由戈捷-维拉尔出版社 (Gauthier-Villars publishing house) 主导,它在这个领域几乎形成了垄断。但我们丝毫没有寻求他们合作的诱惑;他们对我们来说太学院派了。幸运的是,我们甚至不必考虑这个方案。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位出版商:他的名字是恩里克·弗雷曼 (Enrique Freymann)。
他是一个既迷人又多彩的人物。听他说话,你几乎会以为他是纯正的墨西哥血统:“我是阿兹特克人 (Aztec),”他喜欢说。据我所能弄清楚的,他来自奇瓦瓦州 (state of Chihuahua),他的一位祖先,一个因1848年事件被迫离开的德国人,在那里定居并组建了家庭。在弗雷曼所说的任何事情中,无论是关于他自己还是任何其他主题,试图区分事实与虚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字面真理与本质真理,都是徒劳的。在布尔巴基邀请他参加的一次晚宴上,弗雷曼的妻子恳求他讲某个轶事。他推辞道:“那个还没准备好。” 弗雷曼说他最初是画家。在世界各地闯荡了一番后,他加入了墨西哥外交使团,并娶了老学长赫尔曼 (Hermann) 的孙女,赫尔曼是一家科学出版社的创始人,这家出版社虽然从未真正与戈捷-维拉尔匹敌,但仍然出版了重要的著作,例如1922年埃利·嘉当关于不变量积分的著作。弗雷曼接管了这家出版社,他在索邦街 (Rue de la Sorbonne) 的小办公室后面指导着它,依靠两位忠实的员工和一个跑腿的小厮。事实上,弗雷曼就是赫尔曼出版社。他几乎从不离开他的后办公室,除非去参加图书拍卖会。在圣日耳曼大道 (Boulevard Saint-Germain) 一个尘土飞扬的仓库里,他堆积了大量珍本书籍,他从未真正试图出售它们。1929年,他创办了《科学与工业动态》(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系列丛书,这像一张蜘蛛网,他设法通过它将国际科学精英中的精华,以及一些糟粕,诱入他的巢穴。对于他的系列丛书,弗雷曼对所有想法都持开放态度,从最基于研究的到最异想天开的,他喜欢说后者中的一些在商业上是最成功的。他对公司的商业方面考虑不多,只要能勉强维持生计就行。用一份出版物的收益弥补另一份的损失,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尽管我从未知道这样做是否不需要奇迹般的 juggling。总有好心人警告说他濒临破产,尽管他从未看起来像那样。在他的后办公室里,他似乎整天除了闲聊什么也不做。除非我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否则我甚至不会去那里,而且我总是后悔不得不离开。最终弗雷曼和我成了真正的好朋友。战争期间,他把我的图书馆保存在他圣日耳曼大道的仓库里,救了我的书。他一直保留着的墨西哥外交护照,使他得以安然度过那些艰难岁月。1945年,他亲自告诉我他是如何经历巴黎解放的。一天早上,他在美第奇广场 (Place de Medicis)(可惜后来改名为埃德蒙·罗斯丹广场 (Edmond Rostand))的公寓里听到街上有枪声,谨慎地决定待在家里。枪声停止了,像往常一样,好奇心战胜了他。他下了楼,走到圣日耳曼德佩区 (Saint-Germain-des-Prés),看到该街区已经在自由法国 (Free French) 手中。报摊已经公开出售以前被迫转入地下的报纸。他买了《解放报》(Libération) 和《战斗报》(Combat),放进口袋,沿着林荫大道和埃科尔街 (Rue des Écoles) 朝索邦街走去。在一个街角,他被一个德国巡逻队拦住了。军官手持枪支,搜查了他,并用法语问他:“你从哪里弄到这些报纸的?” 弗雷曼认为说实话也没什么损失,回答说:“你不知道它们在圣日耳曼德佩公开出售吗?”“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和它们一直以来的价格一样,每份五法郎。” 军官仍然拿着枪,把两份报纸放进口袋,拿出十法郎递给弗雷曼。“我不是报贩!”弗雷曼惊愕地喊道。“是的,但你可以再买,我不能。” 然后他命令他的巡逻队:“前进!走!”(Vorwärts! Marsch!)
谈论弗雷曼时,我陷入了他轶事般的模式,让自己被带跑了。当布尔巴基开始形成身份时,弗雷曼已经很熟悉我们了。我想在去印度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他了。1931年,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对雅克·埃尔布朗 (Jacques Herbrand) 最近在一次登山事故中去世深感悲痛,这在我们中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我们决定通过出版一本题献给他以示纪念的文章集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埃米·诺特、冯·诺依曼 (von Neumann) 和哈塞 (Hasse) 欣然加入了我们的计划。弗雷曼毫不犹豫地同意出版这本合集,在他的坚持下,它采取了在他的《动态》系列中发表一系列出版物的形式,而不是一本书。他一听说布尔巴基,就同样准备好承担出版商的角色。事实证明,他信任我们并从一开始就给予我们持续的鼓励,并没有理由后悔。布尔巴基注定要成为赫尔曼公司的经济支柱之一。但在我所指的那个时候就拥抱我们的冒险,这为他增添了光彩。不乏假正经的学究警告弗雷曼,说他参与一场粗俗的大学恶作剧是在出洋相。也许正是尼古拉·布尔巴基的名字和传说,弗雷曼热情地帮助和怂恿其发展和传播,吸引了他参与我们的项目。
我们事业的性质起初对我们来说并不清晰。最初,我们有一个或多或少的教学目标:勾勒出大学水平数学教学的主要脉络。很快我们开始谈论制作一本用于这个水平的分析教材或论著,以取代古尔萨 (Goursat) 的教材作为基础课程。我们在巴黎的会议致力于决定章节主题和分配工作。布尔巴基要求他的合作者就从集合论到解析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的众多主题提交报告。渐渐地,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巴黎的会议不足以像需要的那样充分讨论这些报告,所以我们决定集体拿出两周暑假时间,在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一起度过。克莱蒙大学在贝斯-昂尚德斯 (Besse-en-Chandesse) 有合适的设施,暑假期间未使用。第一次布尔巴基大会就是1935年7月在那里举行的。
如今这个想法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远非如此。稍后,德国的纳粹数学家产生了组织“工作营”(work camps) 的想法,模仿将年轻失业德国人送去做体力劳动的劳改营 (Arbeitslager)。自那时起,这个制度已遍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并成为将政府补贴导向通常相当有价值的科学活动的最常见方式之一。但即使它们最终产生了出版物,这些座谈会、会议、研讨会、大会,无论它们叫什么,主要还是设计为相互学习的聚会。布尔巴基大会从来不是这样,它们过去举行,事实上现在仍在举行,目的是集体起草和撰写文本。这并非说它们不为参与者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但这种交流并非它们构思的目的。
至于外部资助,直到战后才完全没有。既然我们选择为自己的目的而聚会,我们自己买单似乎是很自然的。1948年后,法国的情况使得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资助。资助被批准并被感激地接受了。之后,支付给布尔巴基的版税足以支付我们的费用。
贝斯-昂尚德斯的布尔巴基大会之后,我被征召参加在沙隆 (Châlons) 附近的穆尔默隆 (Mourmelon) 军营为期三周的军事训练。在那里,作为预备役中尉,我发现了一些对军事生活和我一样热情的师范校友。如果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这种生活主要在于等待,虽然夜晚睡眠不足,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瞌睡。以参加第一届莫斯科国际拓扑学会议 (First International Topological Conference in Moscow)——我和其他一些法国数学家都被邀请了——为借口,我获得了上校的许可,提前一两天离开军营。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分遣队的指挥官是谁?” 我有足够的急智回答“当茹瓦先生,科学院院士”;确实,当茹瓦也在受邀之列。许可被批准了,所以我得以飞往华沙 (Warsaw),在那里我搭上了去莫斯科 (Moscow) 的火车,不用担心“分遣队”。我及时赶到了会议,会议定于9月4日至10日这一周。感谢我俄国同事的慷慨,我将逗留时间延长到十月,包括对列宁格勒 (Leningrad) 的短暂访问。
这次会议是在苏联 (U.S.S.R.) 举行的第一次如此规模的数学会议。(几年前在哈尔科夫 (Kharkov) 举行的苏联会议,有少数外国人参加,包括阿达玛,但并未真正算作国际会议。)它不仅是第一次,也是斯大林 (Stalin) 政权下举行的最后一次此类会议。我自己算不上拓扑学家,尽管我对拓扑学的快速发展并非漠不关心。我的邀请是在四月份收到的,归功于我与保罗·亚历山德罗夫 (Paul Alexandrov) 的友谊。我对苏联太好奇了,只能立刻接受。它使我得以获得免费签证,在我的护照上如此注明 (besplatno)。在俄国 (Russia),我被告知这可不是小恩惠。在莫斯科,外国会议参与者被安排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主要酒店。我们主要靠会议期间在走廊里供应的鱼子酱小面包 (caviar canapés) 过活,因为那时和现在一样,任何试图在酒店餐厅用餐的尝试都会遇到工作人员几乎不可战胜的消极抵抗。有一句现代俄国谚语大意是“俄国人民通过他们最优秀的代表的器官吃鱼子酱”;显然,在会议期间,我们被算作那些代表之一。会议结束后,我表示希望将访问延长几周,我在苏联科学院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的同事们好心地邀请我做一系列报酬丰厚的讲座。他们安排我住在莫斯科河 (Moskva River) 岸边的学者之家 (Scholars' House),在那里我也可以简单用餐而不用浪费太多时间;俄国人的好客包揽了其余的一切。我交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庞特里亚金 (Pontrjagin),他后来变化如此之大⁹。那时他还年轻、无忧无虑、善于接受、充满想法,而且据我所见,思想开放、精神独立。他失明了,和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我早先在德国见过施尼雷尔曼 (Schnirelmann),在莫斯科又见到了他。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数学家,1938年的英年早逝使他未能充分发挥潜力。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自杀身亡的。他是个迷人的年轻人。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是他的住所不过是一间破旧的带家具的房间,他羞于带朋友去那里。他非常尴尬地让我看过一次。人们告诉我,仅仅是这一点就阻止了他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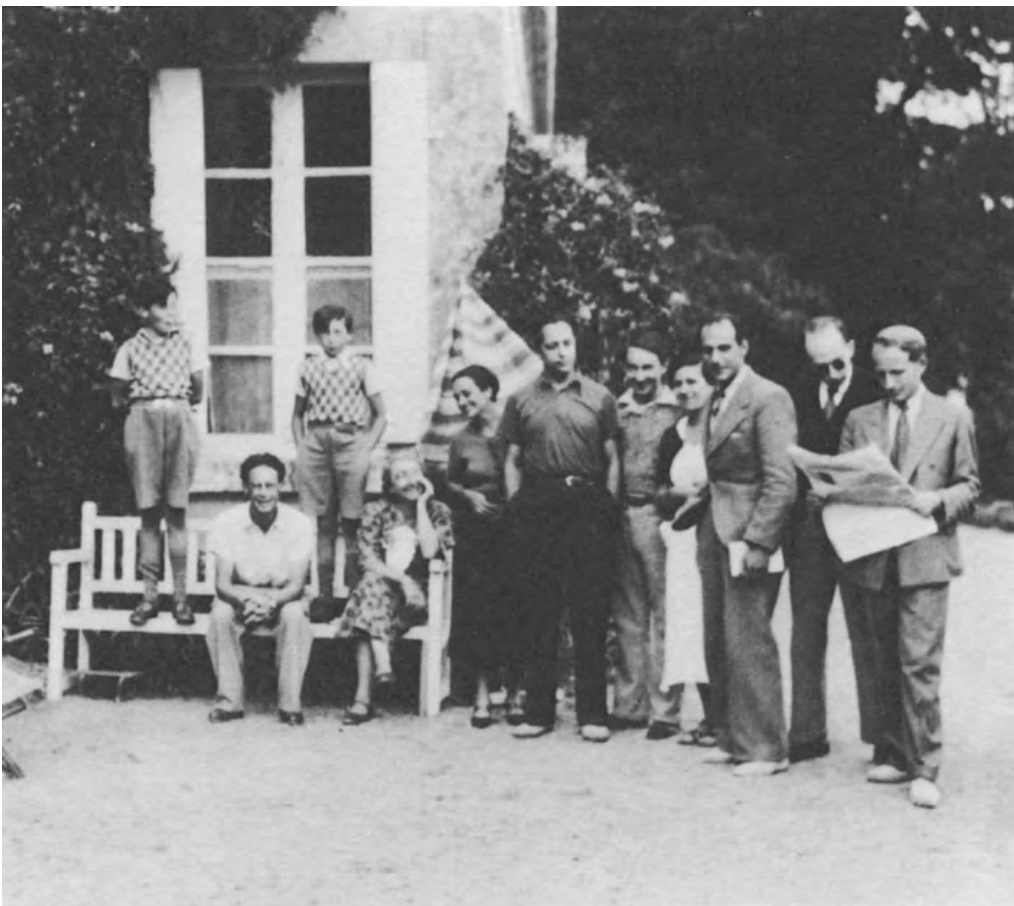 布尔巴基在尚凯 (Chancay) 的大会 (1936年)。站在长凳上:C. 谢瓦莱的外甥们;坐着:A.W. 和谢瓦莱的母亲;站着,从左到右:妮内特·埃雷斯曼 (Ninette Ehresmann),R. 德波塞尔 (R. de Possel),C. 谢瓦莱,雅克琳·谢瓦莱 (Jacqueline Chevalley),米尔莱斯 (Mirles,“试验品”),J. 德尔萨特,C. 埃雷斯曼 (C. Ehresmann)
布尔巴基在尚凯 (Chancay) 的大会 (1936年)。站在长凳上:C. 谢瓦莱的外甥们;坐着:A.W. 和谢瓦莱的母亲;站着,从左到右:妮内特·埃雷斯曼 (Ninette Ehresmann),R. 德波塞尔 (R. de Possel),C. 谢瓦莱,雅克琳·谢瓦莱 (Jacqueline Chevalley),米尔莱斯 (Mirles,“试验品”),J. 德尔萨特,C. 埃雷斯曼 (C. Ehresmann)
显然,我对苏联的局势只能获得最肤浅的了解。我去那里时并没有当时一些法国知识分子陷入的幻想。我妹妹与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圈子接触太多,以至于我不可能对真实情况毫无察觉。在“左派”知识分子中,她是最早不仅看穿这些幻想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真实本质,而且也认识到好列宁 (Lenin) 与坏斯大林的神话是另一种幻想的人之一。尽管如此,1935年在我看来,某种乐观主义,并非全是装出来的,被一些俄国知识分子所共享,他们似乎相信最坏的压迫已经过去,政权将逐渐变得更加自由。例如,数学家们很可能相信当局对他们会议的支持是这种演变的一个症状。也许我让自己被说服了。唉,没过多久,大清洗 (great purges) 就让所有人都睁开了眼睛——除了那些有眼无珠的人;这样的人总是有的,就像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 (Algerian war) 时期和美国越南 (Vietnam) 时代所看到的那样。
至于俄国数学家,他们大多未受清洗影响。在莫斯科时,我听说过一个关于此事的轶事。俄国数学家奥托·施密特 (Otto Schmidt),他的名字仍然与群论的一个定理联系在一起,在1917年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 后不久被任命担任政府要职。据说那时,他召集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Petrograd)(后来的列宁格勒)的主要数学家,对他们大致说了如下的话:“无论什么政权,数学家的工作对门外汉来说都太难理解了,我们不可能受到外界批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位奥托·施密特后来作为“切柳斯金号英雄”("heroes of the Tcheliouskine") 之一而闻名。他在北冰洋 (Arctic Ocean) 冰山上的奥德赛被拍成了电影,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他高贵的面容和威严的胡须,我曾在哥廷根敬佩过。施密特比斯大林活得长。我被告知,在斯大林时代,他在遥远的北方比在莫斯科附近感觉更安全。
关于1935年莫斯科普遍的心态,我还做了另一个观察。自十月革命以来,党的路线包括了严格的国际主义。1935年,俄国人再次被允许,甚至被鼓励,采取爱国立场。在我看来,他们正陶醉于这种变化。此外,战争正成为谈话的主题。当我参观刚刚向公众开放的莫斯科第一批华丽的地铁站时,我被告知它们也打算在必要时用作防空洞。当我惊讶地看到到处张贴着无处不在的“维修中”("closed for repairs") 标志,尤其是在电梯上时,我的朋友们解释说,最优秀的熟练工人都去了兵工厂。也许这过于简化了;但至少这似乎和在此联系中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和斯拉夫灵魂 (Slavic soul) 一样合情合理。
由于很少有机会听到关于政权本身的评论,我听到的那些就更让我印象深刻。我的朋友扎里斯基,已经归化为美国人并在巴尔的摩 (Baltimore) 任教,当时也在莫斯科。他有一个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是西伯利亚 (Siberia) 一家工厂的工程师,留在了苏联,来莫斯科看他。我参与了他们大部分的交流。这位兄弟参加过内战,现在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极其痛心。他所说的可以概括为几句话:“我们进行革命不是为了这个。” 同样的结论无疑每个世纪、每个国家的真诚革命者都得出过;但无论这些话多么可预见,它们怎能不触动人心呢?扎里斯基再也没有得到这位兄弟的消息。
一天在特维尔大街 (Tverskaia)(后来的高尔基大街 (Maxim Gorky Street)),我偶然遇到了一位德国汽车修理工。我用我蹩脚的俄语拦住他问路;他用德语回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们在城里的公园里见过几次面。正是在我离开那天,他开着车送我去了车站。起初我怀疑他是不是一个特务 (agent provocateur)。但特务应该让别人说话,而这个人只想自己说话,并且说得很自由。他离开德国是出于对希特勒政权的厌恶。“我不如待着,”他说,“这里没什么不同。” 这样的话出自记者或公共演说家之口 hardly moving。但出自一个亲身经历过他所谈论事情的人之口,它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
我还从苏联带回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教训。在西方,在我描述的那个时代,如果想旅行,就去车站,备好适当的钱,买张票。在苏联,这种方法很少实行。通常,人们会找一个或多或少合理的借口来获得一张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kommandirovka) 或旅行许可证。与当局关系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我早先在高师就见过这种制度在小范围内运作。到我妹妹在那里时,朗松 (Lanson) 和韦肖在行政管理上已被塞莱斯坦·布格莱 (Célestin Bouglé) 取代。前两位曾徒劳地试图用无效的约束来让学生们温顺。布格莱则通过巧妙地操纵暑期旅行资助和其他小恩小惠,实施了更大程度的控制。在苏联,同样的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最高的恩惠是国际旅行的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至今仍然如此。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规则;甚至声望也在这方面起作用。飞到东京,发表一场或多或少深奥的讲座,第二天就回来,所有费用报销,这难道不增添一个人的荣耀吗?
紧随我苏联之行的是在日内瓦 (Geneva) 的一次座谈会,原则上主题与莫斯科会议相同,但构思规模要小得多。然而,从数学上讲,它对我来说更有成果。在莫斯科,除了惠特尼 (Whitney) 关于球面上纤维丛 (fiber bundles on spheres) 的重要报告外,可能最原创的发展——由亚历山大 (Alexander) 和柯尔莫哥洛夫 (Kolmogorov) 独立报告——涉及复形 (complexes) 和局部紧空间 (locally compact spaces) 的上同调环 (cohomology rings)。然而,毫无疑问是因为我过于沉迷于探索我不熟悉的环境,我没有给予这个主题应有的关注。在日内瓦,干扰较少,埃利·嘉当和乔治·德拉姆 (Georges de Rham) 的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几年前,我就对德拉姆将他的定理应用于代数几何印象深刻;在日内瓦,我完全相信了这些定理以及德拉姆当时提出的“流”(current) 概念的至关重要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临时的概念,因为当时洛朗·施瓦茨 (Laurent Schwartz) 的“分布”("distributions") 甚至还未孕育。同样在日内瓦,上同调环出现了;虽然这里的视角比亚历山大或柯尔莫哥洛夫的处理更狭窄,但通过使用微分形式 (differential forms) 使它们更加具体化了。后者将成为我研究簇 (varieties) 最喜欢的工具之一。
我自己在日内瓦座谈会上的贡献与群 (groups) 和齐性空间 (homogeneous spaces) 上的不变测度 (invariant measures) 有关。它取自我早在1934年就开始为《数学科学备忘录》系列准备的关于群上积分 (integration on groups) 的卷册,紧随埃利·嘉当对该系列的著名贡献之后。我在1935年秋天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同时继续我的巴黎之行,儒利亚讨论班(那年致力于拓扑学)和布尔巴基会议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在斯特拉斯堡,嘉当和我绝非无所事事。那时,正如我在马赛有机会观察到的那样,法国省立大学的科学生活几乎不存在——但幸运的是,斯特拉斯堡证明是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当这座城市属于德国时,那里有一所优秀的大学:仅举一例,H. 韦伯 (H. Weber) 曾在那里长期任教。1918年后,法国人希望保持大学的声望,多年来其教员中包括了杰出甚至显赫的学者。渐渐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无论是科学界还是人文学界——都 succumbed to the charms of Paris;但斯特拉斯堡仍然 nurturing 着从普遍的法国省份灰色单调中脱颖而出的令人钦佩的雄心。这种雄心不仅限于大学,也体现在城市活跃的音乐生活中,我热切地利用了这一点。嘉当和我并不像德尔萨特决心在南锡扎根那样坚定地要在斯特拉斯堡永久扎根,但我们也没有特别想离开的冲动。我们与我们的资深同事——蒂里 (Thiry)、塞尔夫 (Cerf) 和弗拉芒 (Flamant)——关系极好,我们发现他们总是准备好尽其所能鼓励和帮助我们的倡议。我教了一门代数数论 (algebraic number theory) 课程。我相信这是自世纪初以来法国大学开设的第一门数论课程。在大学目录中,它本应列为“算术”("Arithmetic")。对院长来说,这个标题带有小学的味道;它不符合他对大学荣誉的概念,所以我们将课程名称改为“数论”("Number Theory") 或许是“高等算术”("Higher Arithmetic"),他很高兴。这位院长是地震专家。我不在他的好感范围内,因为有一天他听到我大声清楚地问一位同事:“院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934年,他因我未经官方授权就去汉堡做讲座而向我发出官方训斥(阿里格尔的阴影!……)由于这次旅行涉及国际旅行,我本应向教育部申请许可,教育部会咨询外交部,外交部会咨询柏林大使馆,大使馆又会联系汉堡领事馆…… 这位院长有一次指责我的同事塞尔夫在某个仪式上没有穿学术礼服。“我会穿的,”塞尔夫告诉他,“当关于穿着学术袍的规定得到恰当执行时。”“这些规定是什么?”“这些规定来自拿破仑,从未被废除,规定长袍应穿在传统法式服装外面,包括及膝短裤、丝袜和佩剑。” 令这位院长有些惊讶的是,不久之后,教员们选举了另一个人担任他的职位。新院长是天文学家丹容 (Danjon),他在1940年对我的支持对于我获得允许我去美国的维希护照 (Vichy passport) 至关重要。战后他将成为巴黎天文台 (Paris Observatory) 的台长。
吸引那些不仅仅关心竞争性考试常规的学生到省份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数学领域;当我在斯特拉斯堡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确实有两个学生,我能够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第一个是伊丽莎白·卢茨 (Elisabeth Lutz),我的算术课程激发了她对研究的兴趣。她关于 p-adic 椭圆函数 (p-adic elliptic functions) 的论文被哈塞接受发表在《克雷尔杂志》(Crelle's Journal) 上。更接近战争时,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学生雅克·费尔德鲍 (Jacques Feldbau),请我建议一个拓扑学方面的话题。我咨询了埃雷斯曼 (Ehresmann),他在该领域比我精通得多。遵循他的建议,我建议费尔鲍研究当时还很年轻的纤维丛概念。尽管他的方法有些笨拙(对初学者来说 hardly surprising),他还是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以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在《科学院院刊》上,后来,当维希反犹法律使得这种做法不明智时,以雅克·拉布勒尔 (Jacques Laboureur) 的名字发表。他被德国人 deport,死于集中营。
但谈到费尔德鲍,我已经扯远了,扯得很远。1936年初,我未来的妻子埃夫琳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复活节期间,我再次回到西班牙,这次和她一起,我们一直走到了安达卢西亚。在塞维利亚 (Seville) 的 feria 节上,我们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斗牛,为此我小心翼翼地通过在去竞技场路上几家可以喝到美味的曼萨尼亚雪利酒 (manzanilla sherry) 的西班牙酒吧停留来为我的同伴做准备。经过这样的准备,她——以及我,就此而言——毫无困难地分享了其他观众表现出的热情,毕竟他们在斗牛方面是比我们好得多的裁判。第二天,肉铺打广告出售前一天比赛的肉;我怀疑它一定相当老韧。返回法国途中,我被埃斯科里亚尔 (Escorial) 的建筑(那片映衬在无瑕蔚蓝天空下的凹面雕塑)所震撼,并尽一切努力安排夏季布尔巴基会议在修道院附近一所中学举行,那里在假期期间为学术客人提供住宿。我怎么会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内战呢?许多比我更精明的人也没有预料到,或者至少没有那么快。内战在七月爆发;八月我妹妹去了巴塞罗那 (Barcelona),从那里她去了阿拉贡 (Aragon) 前线。我们的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心,很快就出发去寻找她。他们费尽周折才在一家医院里找到了她,情况相当糟糕。当我收到消息时,我回了一张明信片,激怒了我的母亲——或者至少她很长一段时间假装如此:“很高兴听到你们暂时都还活着。” 毫无疑问,我知道我妹妹能够做出最鲁莽轻率的行为,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必须为布尔巴基准备一份关于一般拓扑学 (general topology) 的报告。我是在东比利牛斯山脉 (Eastern Pyrenees) 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的一家旅馆里写的。总的来说,我提出的提纲在下个月被采纳了。这项任务完成后,我花了两周时间游览科西嘉岛 (Corsica),大部分时间是在岛北部可爱的森林里徒步——如今那里似乎因反复发生的火灾而荒芜了。一天晚上我迷路了,偶然发现了来自撒丁岛 (Sardinia) 的伐木工人的棚屋。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玉米糊 (polenta),比我在最好的意大利餐馆能找到的任何玉米糊都好——而在森林中央,就在主人准备它的炉火旁吃,味道是多么鲜美!当我准备睡在他们好心为我提供的帆布床上时,我问他们第二天早上几点必须去上班。“我们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他们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是自己的主人”(siamo i propri padroni)。事实上,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出发;但这是他们自愿决定的。不用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以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热情接待。
于是,九月份,布尔巴基召开了“埃斯科里亚尔大会”("Escorial congress"),我们这样称呼它,尽管内战阻止了我们实际在那里举行。在最后一刻,谢瓦莱的母亲提出在她位于图赖讷 (Touraine) 尚凯的美丽庄园接待我们,离武夫赖 (Vouvray) 不远。自然,布尔巴基小组的工作很快就超出了我们最初设定的过于狭窄的范围。我们起初打算取代的主要经典分析教材(若尔当、古尔萨)旨在用几卷书阐述一个初学数学家在专门化之前应该知道的一切。在十九世纪末,这样的主张仍然可以严肃地提出;到现在它已经变得荒谬了。仅仅涵盖集合论以及代数和拓扑概念最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就需要比简短的引论章节多得多的篇幅。当我们着手不是为每个主题写一部完整的论著,而只是以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来处理它,以免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补充时,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放弃任何编写大学水平教材的想法之外,别无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奠定一个足够广泛的基础来支撑现代数学的核心;我们或许也可以梦想在这个基础上能建造些什么,但这并不紧迫。
在这次大会及随后的会议上,我们的工作方法形成了。对于每个主题,在初步报告和小组讨论后指定一位撰稿人。这位撰稿人提供初稿,小组会再次阅读和讨论,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甚至,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断然拒绝。然后会指定另一位撰稿人,遵循小组的指示——当然这些指示并非总被听从——来完成第二稿;如此等等。
鉴于这种方法,不可能将某篇文本归于小组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名下。此外,一致同意决定只能通过全体一致同意做出,并且任何决定都可以受到质疑;在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决定将被推迟。毫无疑问,相信这个过程会产生结果需要极大的信念,但我们对布尔巴基有信心。
尽管如此,当我们第一次批准一篇文本准备付印时,我们几乎感到惊讶。这是集合论的《成果概要》(Fascicule de Résultats),在战前以其最终形式被采纳。关于这个理论的第一篇文本,由嘉当准备,曾在“埃斯科里亚尔大会”上宣读;未能出席的嘉当收到电报通知其被否决:“并集 交集 子集 积 你被肢解了 该死的 布尔巴基 (Union intersection partie produit tu es demembré foutu Bourbaki)。” 明智地,我们决定先出版一期确立集合论符号系统的分册,而不是等待随后将要进行的详细处理:是时候一劳永逸地固定这些符号了,事实上我们提出的符号,对先前使用的符号进行了一些修改,获得了普遍认可。很久以后,我自己在这场讨论中的参与为我赢得了女儿妮科莱特 (Nicolette) 的尊重,当她在学校学到空集符号 时,我告诉她我个人对它的采用负有责任。这个符号来自挪威字母表 (Norwegian alphabet),在布尔巴基小组中只有我熟悉。
同样在“埃斯科里亚尔大会”上,确定了未来出版物的总体指导方针——甚至包括要使用的版式。令我非常满意的是(因为数学史,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伟大的数学文本,早已让我着迷),我们采纳了在每章结尾不仅附上不同难度级别的习题,而且还附上历史附录的原则;这些“历史注记”("Historical Notes") 将显著地促成我们工作的独特性。
在确定布尔巴基要承担的任务方面,随着结构 (structure) 概念以及相关的同构 (isomorphism) 概念的采纳,取得了重大进展。回顾来看,这两个概念似乎很普通,数学内容也相当贫乏,除非加上态射 (morphism) 和范畴 (category) 的概念。在我们早期工作时,这些概念为那些仍然笼罩在混乱中的主题投射了新的光芒:甚至“同构”这个术语的含义也因理论而异。存在简单的群结构、拓扑空间结构等等,然后还有更复杂的结构,从环到域,据我所知,在布尔巴基之前没有人说过,而这是需要被说出来的。至于“结构”这个词的选择,我的记忆力不行了;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它已经进入了语言学家的工作词汇,我一直与这个圈子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也许这不仅仅是巧合。
1936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为我的美国之行做准备,冯·诺依曼,至少从1930年起我们就保持着友好关系,安排我在1937年第二学期(从1月到5月)去普林斯顿 (Princeton) 的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我必须完成我为《备忘录》准备的那卷书的最后润色。在我出发前不久,我把手稿留在了戈捷-维拉尔出版社,并安排谢瓦莱在我缺席期间接替我在斯特拉斯堡的职位。按照当时的惯例,我在此期间将继续领取薪水,由我相应地支付他报酬。我们毫不费力地达成了协议。我手头已经有一个可以在普林斯顿做系列讲座的成熟主题,尽管我还需要完善细节。这就是我1934年在汉堡讲座中已经涉及的主题,我将在第二年发表在《刘维尔杂志》(Journal de Liouville) 上。于是我动身去了勒阿弗尔 (Le Havre),1937年1月10日,我在那里登上了开往纽约 (New York) 的“巴黎号”("Paris") 轮船。
幸运的是,我不晕船。航行开始时短暂的一阵晕船没有后遗症,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我看到大西洋上常见的冬季风暴时感到的乐趣。在暴风雨的日子里,甲板和餐厅几乎是空的。船上的气氛与我习惯了的往返印度时乘坐的里雅斯特劳埃德航运公司的船只完全不同。这次乘客太多了,航程又太短,我们相互认识的机会更少。我被告知我会遇到俄国雕塑家奥西普·扎德金 (Ossip Zadkine),他当时已经很有名了。据说他对色彩有如此敏锐的感觉,以至于他会准备一条与他晕船时苍白脸色相配的领带。无论如何,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他好心地打开了他的画夹,里面装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素描。在“巴黎号”上还有一位南美音乐厅艺术家,对他刚刚和搭档在女神游乐厅 (Folies-Bergère) 表演的“真猪”(real cochon) 节目非常自豪。两位在整个航行中没有一天是清醒的美国飞行员是酒吧里的常客。其中一人是继林德伯格 (Lindbergh) 之后最早飞越大西洋的人之一。他们刚从西班牙回来,在那里他们曾为共和事业效力——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因为共和派慷慨地支付他们的雇佣兵。由于曾在外国军队服役,他们预计一靠岸就会被捕——果然他们被捕了。这两人深情地谈论着他们最近在去勒阿弗尔路上在巴黎度过的日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雇佣两名妓女的服务。这些女人确信雇佣兵的钱否则会很快挥霍一空,立刻将全部款项代为保管,到了分别的时候,再归还剩余部分——当然,是在扣除了她们服务应得的合法报酬之后。
抵达纽约,我没有看到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它隐藏在浓雾后面。像所有第一次进入这座巨大城市的旅行者一样,我起初感到晕眩、震惊、不知所措。我经过多次后续访问和一次稍长的逗留才适应它并感觉有点熟悉。确实,在那个时候,它与现在已变得的样子相去甚远:摩天大楼少得多;街上行走的疯子少得多。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平静而安全。最突出的是,种族仇恨,虽然并非完全不存在,至少不那么明显;我可以独自或和朋友一起在哈莱姆区 (Harlem) 散步,去那里的酒吧或电影院,而不会遭受言语或身体攻击。我一些最愉快的夜晚是在哈莱姆区的舞厅度过的,在那里总是受到爵士乐——有时是非常好的爵士乐,据比我更懂的朋友说——的热烈欢迎。黑人邀请白人女孩跳舞并不少见。
至于等待所有新来者进入美国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我通过经常使用当时位于爱丽舍街 (Rue de l'Elysée) 的巴黎美国图书馆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而得到了相当好的免疫。我的“疫苗”("vaccine") 不仅包括阅读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的小说,尤其包括阅读 H.L. 门肯 (H. L. Mencken) 的书,即他为《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 撰写的专栏文集,里面充满了既生动又典型的美国轶事。因此,我对所见所闻或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甚至喜欢仔细阅读分类广告——这是我在国外时的惯常做法。但关于这一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别人没有说过一千遍的了。
在普林斯顿的学期期间,一次访问哈佛 (Harvard) 让我有机会参观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那里收藏了大量宋代中国画。一位坚持要带我参观展览的年轻策展人向我保证,只有了解禅宗才能充分欣赏这些画作。“那么,”我对他说,“你自己一定研究过禅宗吧?”他承认他试过,但没有成功。他和几个朋友找到了住在纽约的一位日本僧侣,并说服他来波士顿为他们启蒙。第一次课程,他们邀请了一大群人到某人家里。僧侣在指定时间到达,以莲花坐姿坐下,宣布:“今天我们将冥想以下主题,”接着陈述了一个经典的禅宗公案 (Zen koans)(也许是“一只手拍掌的声音”):这些是没有可能理性答案的问题;我想,目的是清空头脑,为顿悟腾出空间。僧侣接着默默冥想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他没有再被邀请回来。我自己通过阅读铃木论禅宗对这些方法有了一些了解(无疑是非常肤浅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轶事并不奇怪。但是,无论有无禅宗,波士顿博物馆的中国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以前所见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后来我有机会欣赏到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品虽然加强了这种印象,却从未能超越它。
普林斯顿的氛围至今仍然相当国际化,1937年更是如此。高等研究院还没有自己的建筑;大学在旧的法恩楼 (Fine Hall) 为其提供了舒适的设施,韦伯伦 (Veblen) 曾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像我这样的客人则在住宿方面需要自谋生路。这样的逗留是富有成果的,但这种经历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我能做的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按照计划,我做了一系列关于我未来将在《刘维尔杂志》上发表论文主题的讲座,看到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 是定期出席者之一,这对我的自尊心是莫大的鼓舞。通过与亚历山大接触,我试图更多地了解“组合拓扑学”("combinatorial topology"),这当时已经是布尔巴基的兴趣之一。我又见到了库朗,他邀请我去纽约附近的新罗谢尔 (New Rochelle) 拜访他,并告诉我:“我们仍然演奏音乐。” 对于我的询问:“像在哥廷根那样演奏四重奏吗?”他回答说:“不,现在是七重奏或八重奏 (Jetzt spielen wir Septett, Oktett)。” 他现在在美国了:当然一切都必须“更大更好”("bigger and better")——至少更大,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凡事皆有终结。五月,我对在普林斯顿的逗留相当满意,但没有特别想回来的愿望,我动身去了新奥尔良 (New Orleans),准备从那里乘船去墨西哥。途中我在巴尔的摩停留拜访了我的朋友扎里斯基夫妇,然后在华盛顿 (Washington),数学家马歇尔·斯通 (Marshall Stone),与我年龄相仿,坚持要我见他的父亲哈兰·斯通 (Harlan Stone),他对父亲的钦佩(理所当然地)无以复加。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Supreme Court Justice),老斯通先生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我的朋友警告我应该称呼他父亲为“大法官先生”("Mr. Justice")。我本以为会受到正式的对待,但这位大法官——丝毫没有牺牲尊严——给予了我简单而近乎慈父般的欢迎。我大胆地向他询问了当时的热点问题。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废除了罗斯福 (Roosevelt) 新政 (New Deal) 立法的一些重要条款。报纸上充斥着关于罗斯福计划提名额外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创造有利于他政策的多数派的讨论。斯通大法官向我解释说,尽管他在政治上不赞成,但他还是投票支持了罗斯福的立法,因为他在其中找不到任何违反宪法的内容,而宪法是最高法院唯一的管辖范围。这位大法官也曾试图劝阻罗斯福放弃这个计划,建议他耐心等待。最终,罗斯福放弃了它。
我在墨西哥当了一个月的游客,在那里我又遇到了我的朋友斯通及其家人和父母。六月,在坦皮科 (Tampico),我登船前往英国,埃夫琳来那里与我会合。既然她的离婚已经正式生效,我们计划在十月结婚。与此同时,1937年9月,布尔巴基将再次在尚凯开会。我的妹妹,仍然专注于提高她的数学知识,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之后带我们几个人去了她在孔布勒 (Combleux) 的朋友奥古斯丁·德特夫 (Augustin Detoeuf) 家。这位实业家兼哲学家是阿尔斯通公司 (Alsthom) 的老板,在他的帮助下,她曾成为一名工厂工人——在那里她的健康也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那年布尔巴基讨论的主题包括一般拓扑学,以及拓扑向量空间 (topological vector spaces)。几年来,我对瓦雷里 (Valéry)、里尔克 (Rilke) 和克洛代尔 (Claudel) 的偏爱促使我实践(用瓦雷里的话说)“诗艺”("the art of verse")(格律诗、自由诗、十一音节诗和十三音节诗)。仅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我在克什米尔看到的一个瀑布的记忆曾启发我写了一首诗——模仿我读过的诗人的苍白之作,但无论如何这里是开头几行:
清澈的流水在我面前,因我未能投身其中而刺痛我,带着悔恨。 远道而来的慵懒气息,沉重地载着我的惰性, 抚摸着我的身体,对我自己而言如此陌生。¹⁰
在尚凯,布尔巴基启发了我一首十四行诗 (sonnet),实际上是我们一次讨论的相当准确的总结:
设有一向量簇。一域独自行,抽象交换体。 对偶远相望,孤寂复悲啼,求同构不得,叛逆终难抑。
倏忽双线性,火花迸发急,二次分配算子,由此而生息。 乘积网罗中,向量皆被系,永恒颂赞更美结构无休已。
然基底扰乱此空中赞歌:向量迷失,坐标徒增错愕。 嘉当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
此乃终结。算子向量,皆玩完。 污秽矩阵消亡。裸域返身观, 回归自身所定法则,心安然。¹¹
回到法国,许多任务等待着我。首先,我必须在斯特拉斯堡为埃夫琳、她六岁的儿子阿兰 (Alain) 和我找到一套公寓。未来已经显得如此摇摇欲坠,以至于我们选择了一套在伊尔河 (Ill River) 岸边的小小的带家具公寓。春天时,这个地方 оказалось 爬满了臭虫。当我们告诉女房东时,她对前一个房客呻吟抱怨,用她浓重的阿尔萨斯口音告诉我们,他是波-兰-领-事 (PO-lish CON-sul)。我们大多在一家小酒馆吃午饭,在那里我们享受着迪米特里·斯特雷穆霍夫 (Dimitri Stremooukhoff) 和他的伴侣赫拉·切尔明斯卡 (Hela Chelminska) 的陪伴,他们成了我们的朋友。这位极其优雅的男士,一位沙皇将军的儿子,教俄语,而她,同样出身贵族,教波兰语。她的举止言谈强硬有力,而他则文雅细腻。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无法结婚,因为赫拉会失去她由波兰大使馆赞助的教职;迪米特里是无国籍人士,只有一个南森护照 (Nansen passport),因此无法指望改善他 modest 的讲师职位,尽管他有出色的博士论文。战后我们再次找到了他们,当时他被遣返归来。在一次大搜捕中,德国人几乎围捕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全部教员,他们曾避难于克莱蒙费朗 (Clermont-Ferrand)。他们被送到集中营劳动,在那里受到极其恶劣的对待,以至于大多数人,包括斯特雷穆霍夫,回来时健康都已毁坏。因为他的拘禁,他被归化为法国公民,
这样他终于能够和赫拉结婚,并成为索邦大学的教授,几年后因癌症和疲惫去世。
当我从美国回来时,我关于群上积分的手稿正沉睡在戈捷-维拉尔出版社——事实上,它睡得如此之沉,似乎没有什么能唤醒它。我取回了它,并于1937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结婚那天,把它交给了弗雷曼。德尔萨特,他成功地吸引了一些我们的师范校友到南锡,和我承担起责任,创办了法国数学会 (Societé Mathématique de France) 的东部分支。直到战争爆发,这个分支轮流在南锡和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在其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上,西格尔做了一场关于二次型的讲座,之后是在上쾨尼斯堡 (Haut Koenigsbourg) 的远足。与此同时,我正在就几个主题撰写论文,包括我在普林斯顿课程中使用的材料。这篇论文将(用我改编自卢克莱修 (Lucretius) 的话)题献给阿达玛,发表在为纪念他从法兰西学院退休而赠送给他的那卷《刘维尔杂志》上。
阿达玛的退休使他的职位空缺了。我认为自己并非不配接替他;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嘉当和德尔萨特,鼓励我成为候选人。在我看来,勒贝格,当时法兰西学院仅存的数学家,并不觉得我的候选资格不合适。他甚至让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我的“竞选拜访”("campaign visits") 了。这种习俗在学院,就像在科学院甚至其他地方一样,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不遵守它会显得 presumptuous。我觉得有义务遵循勒贝格的建议。但与此同时,我卷入了一场争端,对少数仍然记得它的人来说,被称为“奖章之战”("war of the medals")。
当时,法国的科学生活由两三个院士小圈子主导,他们是重要人物,其中一些人明显更多地受到权力欲望而非对科学的热忱所驱动。这种情况,加上1914-1918年几乎屠杀了一整代人的大屠杀,对法国的研究水平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尤其是在美国,我与许多真正杰出的学者的接触让我看清了法国科学研究令人沮丧的状况。从普林斯顿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法国的科学”("Science in France") 的文章,天真地投给了几家期刊。我在其中讨论了老板制度 (boss system)。这篇文章被认为不适合发表。
所讨论的小集团之一,无疑是最强大的一个,由物理学家让·佩兰 (Jean Perrin) 领导,他是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研究国务次卿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发明者。他不满足于他已经拥有的重要权力,梦想着制定计划,创建一个完整的奖章等级体系,授予奖金,从最高的金质奖章到价值10,000法郎(当时是一笔小数目)的较小奖章。建立这个体系的法令在尚凯的布尔巴基大会期间出现在报纸上。我们不难猜到这个计划将遵循“除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没有人会有才智”(Nul n'aura de l'esprit hors nous et nos amis¹²) 的格言。我们天真地认为发现的乐趣本身就是足够的奖励。最糟糕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个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我们——尽管是相对的初学者——已经意识到存在问题的环境进一步腐败。我们一致决定在大学里散发一份请愿书,希望教育部能废除这项法令。
结果,在我为请愿书征集签名的同时,我也开始了为我在法兰西学院空缺职位的候选资格而进行的一系列拜访学院教授的活动。这些教授认为接待候选人几乎是一种职业义务。因此我见到了保尔·瓦雷里 (Paul Valéry),他刚刚被任命担任诗学教席。他问我多大年纪;我31岁。“一定要抓住你的年龄,”他告诉我,“它是个素数。” 我承认,我对这位我未曾谋面却一直钦佩的人的这句俏皮话印象不大。确实,有一次访问斯特拉斯堡时,一位女士请他在她的《测试先生》(Monsieur Teste)(这本书以著名的“愚蠢非我所长”开头)上签名,瓦雷里写道:“愚蠢正成为我的所长,——保尔·瓦雷里。” 我拜访了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我知道我的梵语老师们深深钦佩他。他快要退休了。他向我解释说,很久以前他曾想出一个卡片系统,本可以让他做出重要发现。“在我能利用它们的时候,从未给予我必要的手段;现在给了我,对我来说已经太晚,没有任何好处了。”
在我拜访的过程中,我会为我们的反奖章请愿书征集签名。这几乎不利于我的候选资格——尤其因为据说金质奖章将授予阿达玛。最后,勒贝格告诉我他已经决定选择曼德尔布罗伊特 (Mandelbrojt),从而结束了我的拜访。在我看来,我的朋友们比我对这个结果更失望。
至于我们的请愿书,我们收集了超过400个签名:在大学圈子里是一次 rousing success。我们四个人——德尔萨特和我,以及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语言学家——将请愿书提交给了教育部长让·泽伊 (Jean Zay),他惊讶地问我们:“但是你们明白吗,如果这两百万法郎不分配给奖章,大学将永远看不到这笔钱?” 我们齐声回答:“是的,部长先生,”这个回答只增加了部长的惊讶。人们过于普遍地认为,滥用一笔钱总比根本不用它好。部长没有理会我们的请愿书。残局在除夕夜最后的预算辩论中上演,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来回穿梭。为了维持一个早已过时的、在新年前实际投票通过预算的虚构,这两个庄严机构的时钟通常在午夜停止。在参议院,约瑟夫·卡约 (Joseph Caillaux),所有非必要公共开支的坚定敌人,正准备好他的大斧头,准备在让·佩兰每次在众议院重新写入奖章的两百万法郎时将其砍掉。直到两周后,在仔细审查了《官方公报》(Journal Officiel) 后,德尔萨特和我才意识到我们赢了。这场胜利只是暂时的:CNRS 此后重新发明了奖章制度,看起来令所有相关人士都非常满意。
注释:
¹ cadres: 法语,指国家公务员或某些公共机构(如大学)的正式编制或职级系统。进入编制通常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和更好的福利,包括退休金。 ⁹ Pontrjagin, who was afterwards to change so dramatically: 指苏联数学家列夫·庞特里亚金 (Lev Pontryagin),他早期在拓扑学等领域有杰出贡献,但晚年政治立场变得保守,并参与了反犹运动,这与韦伊早期对他的印象形成巨大反差。 ¹⁰ 这首法文诗的大意:纯净的水流在我面前,因我未能沉浸其中而让我懊悔受伤。远道而来的慵懒叹息,沉重地载着我的惰性,抚摸着我的身体,这身体于我自身而言如此陌生。 ¹¹ 这首法文十四行诗是一首关于拓扑向量空间和算子的数学戏作,大意如下:存在一个向量簇。一个域(指代数中的域)独自运作,抽象且交换。它的对偶空间保持疏远,孤单而哀怨,寻求同构却发现其难以驯服。突然间,双线性的火花迸发,由此诞生了二次分配的算子。所有向量都被捕获在乘积的网罗中,将永远歌颂那更美的结构。但是基底扰乱了这空灵的赞歌:迷失的向量有了坐标。嘉当(可能指亨利·嘉当,或泛指研究者)不知所措,完全搞不懂了。这就是结局。算子,向量,都完蛋了。一个污秽的矩阵消亡了。裸露的域(喻指纯粹的代数结构)退回自身,回到它为自己制定的法则之中。这首诗以幽默的方式描绘了抽象结构与具体表示(坐标、矩阵)之间的张力以及研究中的困境。 ¹² Nul n'aura de l'esprit hors nous et nos amis: 法语,引自莫里哀的戏剧《太太学堂》,意为“除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没有人会有才智/头脑”。常用来讽刺小圈子的排外和自以为是。
第六章 战争与我:一出六幕喜剧
(Chapter VI The War and I: A Comic Opera in Six Acts)
序幕
(Prelude)
早在1939年9月之前,战争的阴影就已开始笼罩欧洲。一些人,并非没有某种对前景的迷恋,认为它不可避免;另一些人则认为风暴在最后一刻被避免并非不可能。我妹妹属于那些将即将来临的战争视为所有可能邪恶中最坏的一种的人。虽然她从未传播或信奉过铁杆和平主义者的幻想,但她后来为自己最初的立场而深感懊悔。至于我,我尽力相信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如果英国参战,”我说,“那么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失去印度;她永远不会接受失去印度的想法;因此她不会参战;因此不会有战争。” 这个推理所暗示的前景并不比战争本身更令人安心,但在长期来看,它们似乎给处于危机时刻的人类提供了一点喘息的空间,我相信我妹妹也持有这个观点。
尽管斯特拉斯堡几位朋友推荐,我并未读过《我的奋斗》(Mein Kampf)。如果我读了,我对我的三段论就会更缺乏信心了,而且它还有一个主要缺陷: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一场战争,即使获胜,也会导致英国失去印度——对丘吉尔 (Churchill) 来说一点也不明显,他在印度问题上总是目光短浅。
像布尔巴基的大多数合作者一样,我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在第一次征召时就可能被征召入伍。1937年,我尚未决定在战争爆发时的行动计划。在墨西哥的坦皮科,我登上一艘开往伦敦的荷兰客货两用船;那时西班牙战争似乎已经孕育着更普遍冲突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当船在休斯顿 (Houston) 停靠时,我冲出去买报纸,决心如有必要就下船,以便有时间思考。事实证明这没有必要,我继续了我的航行。
1938年,布尔巴基在迪耶勒菲 (Dieulefit) 举行了一次大会,沙博蒂 (Chabauty),他已加入大师合作者的行列,在那里有家族关系。埃利·嘉当 (Elie Cartan) 慷慨地加入了我们,并参加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这恰好是慕尼黑会议¹ (Munich conference¹) 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预兆。我们狼吞虎咽地读报纸,挤在收音机旁:这是一次几乎没有完成任何实际工作的布尔巴基大会。那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战争爆发,我将拒绝服役。在大会中途,向德尔萨特吐露心声后,我想出了某个借口离开了,去了瑞士。但战争的直接威胁似乎很快就消散了,所以我两天后就回来了。在大家离开的前一天,埃利·嘉当,他必须在黎明时分离开迪耶勒菲,和我握手告别,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当然他的意思是“在迪耶勒菲这里”,但他的话在我听来是个非常不祥的预兆。
在此说明我决定不服役的动机似乎是恰当的,尽管我担心这可能会变成一段冗长而混乱的解释。我当时认为自己完全清醒;但在做出具有严重影响的决定时,人是否曾经完全清醒过呢?我从未相信过绝对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德伦理学 (Kantian ethic),或者今天被认为是康德伦理学的东西,在我看来一直是傲慢和愚蠢的顶峰。声称总是按照普遍准则的戒律行事,要么是完全无能,要么是完全虚伪;人总能找到一条准则来证明自己选择的任何行为是正当的。我记不清多少次(例如,当我告诉别人我从不参加选举投票时)听到这样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行事……”——对此我通常回答说,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觉得没有义务将其考虑在内。
另一方面,我深受印度思想和《梵歌》(Gita) 精神的影响,正如我自认为能够解释的那样。法则不是:“汝不可杀人”,这是犹太教 (Judaism) 和基督教 (Christianity) 铭刻在其诫命中的戒律——结果如何呢?——《梵歌》始于阿周那 (Arjuna),“充满最深的慈悲”,将他的战车停在两军之间,并以他清醒地接受克里希那 (Krishna) 毫不退缩地去战斗的命令而结束。像世间万物一样,战斗是一种幻象:了知自我 (Self) 者¹,既不杀戮,也不被杀。在没有任何普遍秘方来规定每个人行为的情况下,个体内心携带着他自己的达摩 (dharma)。在《摩诃婆罗多》神话时代的理想社会中,达摩来自个体的种姓。阿周那属于刹帝利 (warriors) 种姓,所以他的达摩是去战斗。克里希那是特殊的存在,是神的化身。“每当达摩衰落,其对立面胜利时,我便再次化身,”² 他在一首著名的诗节中说道,这首诗曾被用于甘地身上。克里希那存在于达摩之外。
 布尔巴基在迪耶勒菲的大会 (1938年)。从左到右:西蒙娜·韦伊 (Simone Weil),C. 皮索 (C. Pisot),A.W.;J. 迪厄多内 (J. Dieudonné)(坐着);C. 沙博蒂 (C. Chabauty),C. 埃雷斯曼 (C. Ehresmann),J. 德尔萨特 (J. Delsarte)。
布尔巴基在迪耶勒菲的大会 (1938年)。从左到右:西蒙娜·韦伊 (Simone Weil),C. 皮索 (C. Pisot),A.W.;J. 迪厄多内 (J. Dieudonné)(坐着);C. 沙博蒂 (C. Chabauty),C. 埃雷斯曼 (C. Ehresmann),J. 德尔萨特 (J. Delsarte)。
确实,阿周那事先向克里希那描述了即将发生的致命战斗必然导致的结果:不仅是亲人的死亡,还有社会混乱、妇女堕落、种姓混淆。克里希那没有回应这个描述;但俱卢之战 (battle of Kurukshetra) 以几乎全人类灭绝而告终:终极武器掌握在阿周那手中并非徒然。这结局确实 curiously modern!化身的克里希那带给世界的只是《梵歌》。这并非小事。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教导,我们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我们现在生活在种姓完全混淆的状态中;唯一的办法是每个人尽其所能确定他自己的达摩,这只属于他自己。高更 (Gauguin) 的达摩是绘画。我的达摩,正如我在1938年所见,对我来说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尽我所能致力于数学。罪过在于让自己偏离它。
我对《克里同篇》(Criton) 和法律的拟人化 (prosopopoeia of laws) 并不陌生。但在苏格拉底对其城邦法律的至高服从和甘地的公民不服从之间,我并不觉得前者必须优先于后者。甘地并非以他选择违抗的法律是由外国政府强加的这一事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仅仅是以它们不公正这一事实。此外,对他来说(与普遍看法相反),重要的不是违抗不公正法律的权利,而是违抗它们的义务——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据甘地的说法,义务意味着只要一个人确信法律根本上是不公正的,就应该违抗它们,无论这种违抗会带来什么后果。
早在高等师范学校时,我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数学造成的破坏深感震惊。这场战争造成了一个真空,我这一代及随后的几代人都难以填补。1914年,德国人明智地试图保护他们年轻科学精英中的精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得到了庇护。在法国,一种对牺牲面前平等的错误观念——意图无疑值得称赞——导致了相反的政策,其灾难性后果可以从,例如,高等师范学校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上读到。那些是残酷的损失;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军旅生活,无论是接近死亡还是远离死亡——但无论如何远离科学——都不是恢复科学生活的良好准备:幸存者中很少有人能带着他们曾经对科学的热情回归。我认为避免这种命运是我的义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的达摩。所以我从未认真考虑过我姐夫,一位职业军官,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利用我极度近视作为理由,从步兵调到军需处 (Quartermaster Corps)。此外,回忆起人们如何轻蔑地提到“逃兵”(embusqués - 对设法在前次战争中避免参战者的俚语称呼)就足以劝阻我采用这个方案。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良心反战者 (conscientious objector),即不相信杀戮甚至使用死亡工具的人,无论他将此视为普遍有效的戒律还是他个人的达摩。在我看来,从逻辑上讲,牧师和僧侣应该属于那些将这种信念作为不可或缺生活方式的人;我从未理解他们通过何种神学上的微妙之处允许自己成为士兵。至于我自己,确实,我觉得杀戮令人反感,即使只是一只烦扰我的苍蝇;但如果我无法把它赶出窗外,对其施以暴力结局并不会让我充满悔恨。出于同样的原因,废除死刑的问题在我看来仅仅是一个实际问题,我觉得自己无法解决;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无论他站在哪一边,放火焚烧沙特尔大教堂 (cathedral of Chartres),而我手中有武器,我一秒钟也不会犹豫,会击毙纵火犯,而不是任由他行事。换句话说,我觉得自己与无条件和平主义者,就像与不妥协的爱国者(如果还有这样的人的话),或者与狂热的左派分子一样,都相距遥远。1940年,当我采取的行为路线给我带来一系列问题时,我妹妹显然因想到她战前的和平主义观点可能影响了我而感到自责。她在这个结论上弄错了;此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她的和平主义,不像我一些朋友的那样,也不是无条件的,而首先是务实的,并且,她觉得,是现实的——尽管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主意。
如果说有任何例子影响了我,那就是西格尔的。有一天,在瑞士的一家旅馆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在1918年当逃兵的。作为一名年轻学生被征召入伍后,他刚开始在阿尔萨斯服役,就决定这场战争不是他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我的战争” - Dieser Krieg war nicht mein Krieg,他说);他逃跑了,在上쾨尼斯堡附近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里他沉浸在不快的反思中。自然他被抓住了。为了使他免于军事法庭审判,他们把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他从未对我谈起他在那里的拘禁经历,但多年来他一直带着这次经历的印记。西格尔的故事对我来说具有某种美感;在我看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可以具有榜样价值。我是否自诩我的行为也能如此?很有可能:人心哪个角落能免于虚荣呢?
一个法国人,在1938年或1939年,怎么会接受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是他的战争呢?那些把他拖入战争并坚持他们有权这样做的人,正是那些其无能和盲目既使战争不可避免又预先损害了其结果的人。无论好坏,领导一个国家投入战争需要一些领导才能。此时的法国人表现得更像是听任被引导——哪怕是去屠宰场——的顺从绵羊,而不是决心捍卫他们最珍视东西的自由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理由认为,通过使自己免受兵役法的约束,我是在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允许我的小范围内,掌控自己的命运。
自然,没有什么是按计划发生的。我曾想象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比实际情况更像上一次战争。许多显然头脑清醒的人,以及绝大多数根本不清醒的法国总参谋部,都抱有这种幻想。至于特别关系到我的方面,事实证明战争对布尔巴基小组以及我这一代及随后一代其他法国数学家工作的干扰远比我担心的要小。如果我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1939年我还会采取同样的立场吗?徒劳的疑问:无论好坏,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的计划是,万一发生战争,就到一个中立国避难,然后移民到美国。那时我不知道,美国人如此热情地欢迎那些不需要他们的人,却对那些碰巧任由他们摆布的人不那么好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在慕尼黑协定签订时,我曾逃到最近的避难所,也就是瑞士。布尔巴基大会之后,乌云似乎并未散去,所以我去了荷兰等待事态发展。当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当然,还有“光荣的”和平——就像尼克松 (Nixon) 在越南战争结束时那样)时,我决定我可以返回斯特拉斯堡,途中绕道伦敦。在那里我震惊地得知,慕尼黑的谈判者们并未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关于未来的任何实质性保证。伦敦的朋友们向我保证,摊牌只是被推迟了。皇家地理学会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前一个夏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她收到了外交部 (Foreign Office) 的紧急请求,要求她提供任何她能找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信息。她并不认为这能让她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感到放心。
回到斯特拉斯堡,我发现自由大道 (Avenue de la Liberté) 已被重新命名为爱德华·达拉第大道³ (Avenue Edouard Daladier³);和平大道 (Avenue de la Paix) 现在以 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命名。这些变化在我看来充满了不祥的象征意义。评论慕尼黑协定时,亨利·嘉当说:“这就像呕吐:你感到恶心,但也松了口气。” 我继续教我的课,同时让我美国的朋友们知道,如果他们能提供给我一个他们国家的大学职位,我会非常感激。这个解决方案会大大简化我生活的下一阶段,但我的建议毫无结果。
1939年一个早春的清晨,我收到了妹妹的电报:“建议读报。” 希特勒刚刚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我立刻确信法国不会动;我也没有动。不久之后,英国开始流传下面这个针对内维尔·张伯伦的笑话,据说他说过:“在巴特戈德斯贝格 (Bad Godesberg),我意识到希特勒是个土匪,在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我意识到他疯了;但现在,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我知道他不是绅士。” 法国动员了一些所谓的“保护性”("protective") 部队。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我在去巴黎的火车上时,我听到一位来自南锡的预备役军人,在一阵阵大笑中描述他的团如何离开南锡的营房去占领马其诺防线 (Maginot Line) 上的一个工事: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结果发现负责的军官忘记带炮台 (casemates) 的钥匙了。不得不派人骑摩托车以最快速度去取钥匙。
芬兰赋格曲
(Finnish Fugue)
我和妻子是拉尔斯·阿尔福斯 (Lars Ahlfors) 的朋友。1939年,安排好我们夏天和他及家人在芬兰湾 (Gulf of Finland) 他计划租的一栋别墅里度过几周。如果到夏末战争仍未爆发,我们将返回斯特拉斯堡,或许绕道列宁格勒。否则,我的计划是留在芬兰 (Finland),我以为在那里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我的美国之行。这并非我唯一的失算。我随身携带了美元,我认为足够支付我的开销。埃夫琳当然知道我的意图,认为这些计划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与阿尔福斯一家的访问是一段纯粹宁静的时光。租来的别墅位于一个叫洛科 (Lökö,“洋葱岛”) 的小岛上,划船半小时即可到达一个更大、更繁忙的岛屿——小佩林厄 (Lille Pellinge,“小佩林厄”),该岛通过洛维萨 (Lovisa) 号轮船与赫尔辛基 (Helsinki) 相连。在小佩林厄有一个小型旅游中心,我们去那里采购物资。我们的小岛很容易探索:除了我们的别墅,远处只有一个有四五头牛的小农场。那是白夜 (white nights) 的季节,接近仲夏夜前夕。空气总是纯净清澈,透明得难以言表。由于步行的可能性极其有限,我们改为乘船进行长途出游,探索附近的岩石小岛。波罗的海 (Baltic) 的水非常冷,我们只进行短暂的浸泡。和拉尔斯·阿尔福斯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埃尔娜 (Erna),他们开始牙牙学语的女儿辛西娅 (Cynthia),还有一条漂亮的狗。埃尔娜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大约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我们会聚集在餐厅,借着落日余晖喝茶吃三明治。我们从不点灯;可能手头甚至没有灯。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是否收到报纸。日子的流逝以洛维萨号定期出现在我们岛屿海岸外为标志。我们感觉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
这次访问之后,埃夫琳和我被邀请去内万林纳 (Nevanlinna) 在离赫尔辛基不远的一个湖畔他可爱的乡间别墅里度过几天。他和他的妻子(他后来与她离婚了)以及他们可爱的女儿西尔维娅 (Silvia) 在那里,西尔维娅立刻就喜欢上了埃夫琳,尽管她们无法交流一句话。内万林纳夫妇的好客再热情不过了。内万林纳夫人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在我看来她丈夫的情感也类似。然而,从他们给予我们的欢迎来看,这些观点并未带有任何反犹主义的色彩。对他们来说,就像对许多芬兰人一样,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对俄国的仇恨密不可分,而后者又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密不可分。在他们看来,希特勒是欧洲未来的救世主,我想他们愿意(无疑太轻易地)对他政权中必定在他们看来过分的东西视而不见。在内万林纳夫人的书中,我发现了《我的奋斗》,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这让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不怀疑。
我们的下一站是在萨拉湖 (Lake Salla) 岸边的一家小旅馆,离俄国边境很近,接下来的冬天那里将发生激烈的战斗。我们的日子平静而波澜不惊。我们在旅馆的小划艇上在湖上度过了许多小时,或者坐在水边。我带着我忠实的打字机,在那里打出了我答应给布尔巴基的关于积分的报告提纲。至于埃夫琳,她带着她的小速记打字机。婚前,她曾接受过速记打字员 (stenotypist) 的培训。如果需要,她可以用这项技能养活自己,这项技能她至今从未用过。我们都同意不失去它是明智的。所以,在萨拉湖畔,我给她口述了巴尔扎克 (Balzac) 的《贝姨》(La cousine Bette),中间经常停下来欣赏周围山丘的美景。我们也会停下工作去泡个澡,或者在旅馆吃饭,那里的食物简单而丰盛。我几乎没有猜到,我们友好的主人对我们的勤奋感到不安;看到我们一边口述和打着大量的笔记,一边显然在审视周围地区,他们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我只可能是苏联间谍。从这时起,赫尔辛基的中央警察局就为我建立了一个档案。
八月剩下的时间用于一次旅行,带我们去了芬兰的最北端,到达北冰洋 (Arctic Ocean) 上的佩察莫 (Petsamo)(后来被苏联吞并,现名佩琴加 (Pechenga))。在那里我也没有错过泡个澡的机会,在一个有着丝滑沙滩的小海湾里,水清澈得不可思议,但冰冷得我无法忍受太久。午夜时分太阳几乎不落到地平线以下:我们几乎不知道何时该睡何时该醒。读报纸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纬度能找到的唯一报纸是芬兰语的,因为瑞典语 (Swedish) 只在芬兰南部被说和理解。尽管如此,当我在一家旅馆大堂看到标题时,我还是感觉自己懂芬兰语了:里宾特洛甫 (RIBBENTROP).. 莫洛托夫 (MOLOTOV)... 莫斯科 (MOSKVA)。这些宣布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条约签订的词语清晰得令人目眩。
我们在宣战前刚刚返回赫尔辛基。当消息在报纸特刊上宣布时,埃夫琳和我在滨海大道 (Esplanade) 上一家露天咖啡馆坐着,离市里的主要剧院不远。我们感觉仿佛失去了一位挚友。埃夫琳决定再和我待一段时间。邮件仍然从法国寄来,有些延迟,她继续收到家人的消息。阿尔福斯住在赫尔辛基郊区的蒙克斯奈斯 (Munksnäs),他帮我们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带家具的房间,可以使用厨房。我们在波罗的海边的公园里散步,喂那些会来坐在我们手上的温顺小松鼠。我写了许多信给朋友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让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为了简化事情,我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良心反战者。
我开始对所选避难所的安全性产生疑虑。斯大林对芬兰人的行为越来越傲慢。据说芬兰总参谋部在战争爆发时的主要担忧是,一旦芬兰人占领列宁格勒,如何养活该市的人口。即使这是夸大其词,它也准确地描绘了芬兰人对自己毫无根据的信心,因为他们是否有意向希特勒求助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必须付出的代价。我还被告知,他们故意决定使用苏联口径的火炮,以确保能从缴获的敌人仓库中持续补充弹药。
无论如何,埃夫琳不能再离开她托付给外祖母照看的儿子阿兰了。与法国的通讯随时可能被切断。她决定通过唯一仍然开放的路线返回法国:乘火车穿过瑞典 (Sweden) 和丹麦 (Denmark),从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乘飞机到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再乘火车。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即使这一点也不确定,但我们对未来仍抱有一些非理性的希望。1939年10月20日,我们悲伤地分别了。我考虑搬到瑞典等待事态发展——但这已经太晚了:由于我在法国当局那里的身份不合规定,我无法获得因战争而变得必要的瑞典签证。
十一月过得相当平静。埃夫琳已经在萨尔特省 (Sarthe department) 的小村庄帕尔塞 (Parcé) 与她的母亲和儿子团聚了,她的父亲出生在那里。担心由我签名并直接从芬兰寄来的信件可能会连累她,我求助于路易-菲利普·布卡尔特 (Louis-Philippe Bouckaert) 的好意,这位比利时物理学家我在普林斯顿结识并成为朋友,他当时在鲁汶大学 (University of Louvain) 任教。我们商定,我会寄给他写给埃夫琳的未签名信件,他会在寄给她之前签上名。
我通常和阿尔福斯一起吃饭,他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瑞典的安全地带。在烹饪方面,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完全的外行。为了我的午餐,埃夫琳给我留下了一本在我有限能力范围内的小食谱。我继续为布尔巴基工作,尽管没有太大的信念,并且我在优秀的市立图书馆为自己找书读。幸运的是,我带家具的房间里有一台好收音机,我忍不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听伦敦和柏林的广播。我听了希特勒访问慕尼黑被炸弹打断的转播。这次未遂的暗杀企图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得到解释。我听到柏林关于凯撒-威廉植物学研究所 (Kaiser-Wilhelm Institut für Botanik) 的报道。访问结束时,记者问教授:“那么,教授先生,我看到您还在继续工作?”“是的,”教授回答,“这里一切还和过去好时光一样” (hier geht es noch im guten alten Stil)。我希望他不会因为说了这番话而受苦。
我也听好音乐。有一次在给埃夫琳(也就是给布卡尔特,再转寄给埃夫琳)的信中我写道:“……我有幸偶然听到一首莫扎特的五重奏(弦乐四重奏加单簧管),是柏林转播的精彩演出。莫扎特的音乐,即使在其最美妙之处,也常常给人一种印象,某个存在,虽然因其不可理解的宁静而远高于我们,却仍然停下来片刻记起我们,来到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带着温和的嘲弄和温柔的怜悯,为我们抄录一条短暂的信息。但有时,在某些四重奏和五重奏中,以及在《魔笛》的某些部分,这同一个存在,毫不考虑我们,与他的同类交流,而我们那时听到的是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一个只允许我们匆匆一瞥的世界。”
这是龙卷风来临前的平静时刻。11月30日,俄国人在赫尔辛基投下了第一批炸弹。那天,在我住的郊区,我只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我跟着邻居们,他们正朝乡下走去。中午时分空袭警报结束,我回了家。我走近附近一个广场,看不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实上,那里有几挺高射机枪。我近视的眯眼和我明显外国人的衣着引起了注意;我被带到最近的警察局,那里通过电话联系了中央警察局。从萨拉湖时代起,那里就已经有了关于我的档案。我立刻被带到中央警察局并投入监狱。我当时最主要担心的是家里等着我的那片美味火腿——我为那天午餐计划的难得奢侈品。
我大概在监狱里待了四五天。警察在我面前搜查了我的公寓。他们发现的手稿显得可疑——就像1870年在巴黎因间谍罪被捕的索菲斯·李 (Sophus Lie) 的手稿一样。他们还在一个壁橱底部发现了几个速记打字纸卷。当我说这些是巴尔扎克小说的文本时,这个解释一定显得牵强附会。还有一封俄文信,我相信是庞特里亚金写的,回复我夏天初写的关于可能访问列宁格勒的信;还有一包属于波尔代维亚皇家科学院院士尼古拉·布尔巴基的名片,甚至还有几份他女儿贝蒂·布尔巴基 (Betti Bourbaki) 的婚礼请柬,是我几个月前在剑桥与沙博蒂和我妻子合作撰写并印刷的。加上萨拉湖的档案,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堆有罪的推定。我在警察局接受了一次相当平静但冗长的审讯。那天我才体会到“教授”这个称谓在我身上是多么根深蒂固。审讯是用德语进行的,警察(相当笨拙地)试图抓住我的自相矛盾之处。有一次他说:“你撒谎了” (Sie haben gelügt——但用了错误的语法形式)。我的直接反应是回答:“不是 gelügt,应该说 gelogen。” 幸运的是,他似乎没有被冒犯。为了证实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让警察去找阿尔福斯和内万林纳。后者,正如将要看到的,已经不在赫尔辛基了;至于前者,当他打听我的情况时,被相当粗鲁地告知最好不要卷入。在我的处境下,我无法求助于法国公使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带到了那里。我见到的公使馆官员是保罗·杜普伊 (Paul Dupuy) 的侄子,杜普伊曾长期担任高等师范学校受欢迎的校务秘书。这个人显得极其紧张;也许我冤枉了他,但在我看来他表现出所有吓破胆的症状:炸弹曾落在离公使馆不远的地方。我不得不向他承认我的非法身份。他称我为间谍和逃兵,尽管我后来得知根据法国法律,我实际上犯下的罪不过是未按时报到。总之,他明确表示对我完全撒手不管了。后来我得知他在戴高乐 (De Gaulle) 手下仕途顺利。
我不能抱怨芬兰警察给予我的款待。牢房很小,显然不是为长期监禁设计的。我和另外两个人共用它。其中一个,看起来像个海盗,曾在南中国海航行过。他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并教了我一首海涅 (Heine) 的《罗蕾莱》(Lorelei) 的洋泾浜英语版,开头是“Me no savvy..” 我一直希望能记起其余部分。
最令人恼火的情况是,该市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但牢房里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完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度过第一天,也许还有第二天。考虑到纬度和季节,这意味着我们除了在帆布床上打瞌睡和在近乎漆黑中吃送来的饭菜外,什么也做不了。第二天,牢房的小窗户被涂上了深蓝色,这样我们就可以点灯了。而且,从那天起,不再在牢房里送饭,而是带我去附近一家餐馆。我想是在第三天,出门时,我看到警察档案正被装上卡车。我推测赫尔辛基正在因为俄国军队逼近而疏散,并认为我很有可能被处决,以免给抓捕者带来带上我的麻烦。我处于一种并非不愉快的被动清醒状态;这种死法在我看来是当时感染了整个欧洲的愚蠢的一个缩影。第二天早上我被带出监狱时,我甚至没有想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命运。
根据内万林纳二十年后、换了一任妻子后告诉我的故事,发生的事情如下。我相信,他是总参谋部的一位预备役上校,在政府和军队高层都相当知名。芬兰参战那天,他离开去就任。由于明显的地理原因,他驻扎在离赫尔辛基不远的地方。12月3日或4日,他出席了一场国宴,警察局长也参加了。上咖啡时,后者走到内万林纳面前说:“明天我们要处决一个自称认识你的间谍。通常我不会为这种小事打扰你,但既然我们都在这里,我很高兴有机会咨询你。”“他叫什么名字?”“安德烈·韦伊。” 听到这话,内万林纳在他故事的这一点告诉我,他很震惊。“我认识他,”他告诉警察局长。“真的有必要处决他吗?”“好吧,那你想我们怎么处理他?”“你就不能把他押送到边境驱逐出境吗?”“嗯,这是个主意;我没想到。”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因此,我被押送到火车站,和另外三名囚犯一起被关在一个锁着的隔间里。旅途很长,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相互了解。我的邻座,德语说得还算可以,自我介绍说他曾是苏联将军,这让我有些惊讶,即使在几乎没有什么能让我惊讶的这种情况下。据我所能了解到的,他必定是沙皇军队的一名骑兵军官;内战期间他站在苏维埃一边,并且,他说,被授予了将军军衔。后来我被告知,内战期间,包括将军在内的高级军衔授予得相当随意。无论如何,内战后他来到芬兰开办了一家小企业。他的过去使他足够可疑,以至于被运出赫尔辛基。我们试图猜测我们的目的地。最合理的推测是我们将被送往一个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也许这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最好的(他声称亲眼目睹)是关于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对伏罗希洛夫 (Voroshilov) 对他傲慢无礼的行为感到恼火。托洛茨基利用一次他在彼得格勒主持的军事会议,提高嗓门对伏罗希洛夫说:“察里津前线指挥官!伏罗希洛夫同志!”然后,仿佛在下命令,“立—正!” 据故事说,伏罗希洛夫当场僵住,立正站好,这标志着他傲慢态度的终结。Se non è vero...⁴
我的狱友还教了我一句俄国谚语。隔间里的一个座位构成了一个通向铁轨的马桶。他极其礼貌地为不得不打扰我使用它而道歉,并补充道:“正如俄国谚语所说,撒尿不放屁,犹如婚礼没乐器。”
在一个停靠站,我被带下火车,在一个大型监狱里过夜。我告别了我的将军;我们互相祝愿好运。我对旅程的其余部分只有最模糊的记忆。我又被火车送走,然后被要求下车。一个警察把我的护照和被捕时身上的钱包还给了我;他指着一座大桥,示意我朝那个方向走。桥的另一端是一个瑞典宪兵哨所。
北极间奏曲
(Arctic Intermezzo)
我当时在哈帕兰达 (Haparanda),地处波的尼亚湾 (Gulf of Bothnia) 深处,靠近北极圈。宪兵们并非专为我而来:哈帕兰达是所有因战争离开芬兰且不愿或不能乘船或飞机旅行者的主要中转站。瑞典人派出了军队和宪兵巡逻边境。
我不得不再次讲述我的故事。在赫尔辛基,我已经恢复并改进了我在米塔-列夫勒家学到的基础瑞典语;必要时借助德语和英语,我毫不费力地让人明白我的意思。审问我的军官似乎觉得我的情况很简单,直到他问我芬兰警察是否虐待过我。我向他保证他们一直行为相当得体。我看到,这个回答让瑞典军官感到困惑。许多瑞典人倾向于将芬兰人视为野蛮人。
我几乎身无分文:我的“战争基金”,连同我所有的行李,还留在赫尔辛基的房间里;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幸运的是,这些是我的冬装,是我去年夏天带来的,当时以为我在芬兰的逗留可能会很长。起初警察支付了我在一户私人住宅的食宿费;几天后,他们不无歉意地把我转移到当地警察局,那里配备了三个大牢房,通常只用作当地醉汉的夜间避难所。我处于监视下的自由状态,这意味着我可以去离我睡觉地方十分钟路程的一家顾客盈门的小餐馆吃饭,甚至可以沿着预定路线散步。看到我没戴帽子,一位好心的宪兵给了我一顶羊毛帽。气温不高于零下20摄氏度,但因为是干冷,而且空气通常很静止,所以可以忍受,甚至令人精神振奋。在这个季节,太阳每天在地平线上的时间只有宝贵的几个小时,但延长的黄昏使白天延长了好几个小时。尽管警察局的便利设施相当缺乏,我在那里的逗留并非不愉快。有一次,宪兵们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他们让我替他们接电话。
我在我的避难所里没待多久就有了伴。几天后,一个与我年龄相仿、英语说得极好的芬兰人加入了我的牢房。稍晚一点,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被安排在隔壁牢房。他是一位芬兰共产党代表,库西宁 (Kuusinen) 傀儡政府的成员,据说如果战争开始时引发了支持共产党人的全面起义,这个政府本应在芬兰掌权:显然,这是芬兰共产党向斯大林预测的结果。如果他相信了这一点,那表明他对芬兰的情况了解得和希特勒上台时他对德国的情况一样糟糕。还有一个牢房留给醉汉,他们偶尔的存在并不打扰我们。我们的共产党人只说芬兰语,即使说芬兰语也相当沉默寡言。我唯一能交谈的人就是我的狱友,他结果是个愉快友好的人。战争爆发时,他是赫尔辛基财政部的货币兑换部门负责人。宣战时作为军官被动员,他身体上无法忍受俄国人在战斗初期将其部队送去屠杀的景象:据各方描述,那是一场可怕的屠杀场面。有理由认为俄国人派了他们最差的部队去芬兰——无论是 K 因为他们指望得到芬兰民众起义的支持;还是因为他们大大低估了芬兰军队的勇气或爱国主义;或者,正如一些人声称的那样,是斯大林方面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算计。
在我的狱友建议下,我写信给法国公使馆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当局,试图找回我的物品。这个请求唯一的结果是我的箱子最终被送到了法国公使馆,并于1946年从那里转寄到巴西给我。在那里我确实很高兴地在里面找到了我1528年版的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著作,西蒙·德·科利纳 (Simon de Colines) 的排版杰作,它对我非常珍贵,我早已以为丢失了。通过和以前一样的渠道,我向我在巴黎的家人传递了消息。我也与一些数学家通信,希望能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挪威 (Norway) 的维果·布伦 (Viggo Brun) 赶紧给我寄了钱,战后我很高兴能够偿还。虽然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但现在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不同意启发我行为的原则;尽管如此,他向我保证他愿意帮助我。对他来说,希特勒也代表了绝对的邪恶,与希特勒的斗争优先于一切。他费尽周折为我争取挪威签证;他没有成功是我的幸运,因为在那里几个月后我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德国人手中。
十二月,警察收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命令,大意是我不能留在瑞典。要么我让法国大使馆把我送回法国,要么我将被送回芬兰。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签证去任何国家,但我必须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联系了法国大使馆,大使馆无疑就如何处理我咨询了巴黎。一月份,我收到了一张去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票。我享受了几天暂时的自由,期间我遇到了数学家克拉梅尔 (Cramér)。他也表现出理解和慷慨,带我去城里一家比较好的餐馆吃饭。我回到了斯坎森 (Skansen),那个可爱的动物园和露天民族博物馆,几个月前埃夫琳和我在那里曾如此愉快地参观过。我回忆起她和尼尔斯·霍尔格森 (Nils Holgersson),后者在我童年时曾让我着迷。在大使馆,一位公使馆官员很友好,并试图就等待我的命运安抚我。作为交换我的护照,他给了我一份合适的旅行证件,以及一张去卑尔根 (Bergen) 的火车票和一张从卑尔根到纽卡斯尔 (Newcastle) 的船票。
身陷囹圄
(Under Lock and Key)
于是,一月底,我从卑尔根启航,乘坐一艘六百吨的老旧破船。灾难的阴影笼罩着这次航行:广播里播报着在我们前后沉没船只的消息。毫无疑问,它们撞上了漂浮的水雷。有指示要求日夜穿着救生衣。我可能是船上唯一从未穿过的人——并非出于某种愚蠢的虚张声势,而是因为海难生还的机会在我看来几乎为零:北海 (North Sea) 在一月份并不以仁慈著称。事实上,航行非常颠簸,我昏睡了36个小时,没吃一口东西。当我们接近苏格兰 (Scotland) 时,天气变得平静了。到达那里后,我们不得不等待三天,等待海军部 (Admiralty) 的靠岸命令,我们目睹了异常的景象:一大群船只抛锚停泊,都被战争状态 immobilize 了。
我不确切记得我期望旅程的其余部分会如何进行:也许我以为,感谢维果·布伦和克拉梅尔的慷慨,我有足够的钱自己去法国,在那里向当局自首。我确实记得我曾希望途中去剑桥拜访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幻想在船一靠岸就被打消了:警察正等着我。我此前从未怀疑过法国和英国警察已经密切合作。英国警察究竟是如何被告知我在这艘船上的?当时我没有多想这个问题,也从未弄清楚。
甚至在下船前就被拘留,我被一位带着牛津派头的年轻督察(如果那确实是他的级别的话)审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检查并没收了我随身携带的各种文件。其中一份提到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对我的案子表示了兴趣。督察问我:“是罗素勋爵吗?” 确实是他:几年前他继承了这个头衔。审问变成了一场关于良心反战利弊的讨论。中断之后,我的提问者回到我面前说:“我们现在还能争论什么呢?” 总之,我被带上火车,手腕上系着一根皮带——“像条狗,”我被系着的那个警察笑着说。就这样,我乘坐夜班火车从纽卡斯尔到了伦敦。到达并在火车站吃过早餐后,我被带到我的新宿舍,一个当地警察局,接受又一次审讯。这里的规定要求每个囚犯每天散步一小时。所以值班警察带我穿过伦敦的街道,并在我的建议下,去了泰晤士河 (Thames) 沿岸的码头。他似乎很高兴被指派做我的护送。他有生以来最引以为豪的是护送列昂·布鲁姆 (Léon Blum) 作为总理正式访问伦敦。这位警察还有另一种轶事,比如一次夜间巡逻时,他走近一辆停在黑暗小巷里所有灯都熄灭的汽车。当他的手电筒照亮一对处于严重脱衣状态狂欢的情侣时,他并不惊讶;但当那个男人喊道:“走开,你让我女朋友难堪了。”时,他有点吃惊。
从伦敦,我被带到——仍然在护送下,但这次手腕没被绑着——乘火车去南安普敦 (Southampton),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同胞。虽然他似乎与他的英国同事沟通有困难,但他忽略了我提出为他翻译的提议。我们一独处,他就解释说:“我完全懂英语;但在我这行,最好装作不懂你最懂的语言。” 他是法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在带我登上将载我们去勒阿弗尔的船时,他询问了我的情况,然后问道:“但是面对所有这些难题,你难道没想过自杀吗?” 我告诉他这个念头甚至从未出现过。“好吧,”他说,“我只是不想惹麻烦。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我现在就把你铐起来。” 我向他保证没必要。这时我们已经在一个有两张铺位的舒适船舱里了。他说:“我在船上有工作要做。我要把你锁在这里。我明天早上回来。”
正如承诺的那样,他早上放了我出来,并带我到一等舱餐厅,那里正在供应早餐。邻桌坐着保尔·朗之万 (Paul Langevin)、莫里斯·弗雷歇 (Maurice Fréchet) 和物理学家萨德龙 (Sadron),我的斯特拉斯堡同事兼朋友。我问我的同伴:“你想让我把你介绍给一位科学院院士吗?”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受宠若惊。
当我在高等师范学校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尊重朗之万有几个原因,其中包括他从未屈尊成为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战前一段时间,他终于下定决心这样做,据说是在共产党的要求下:那样共产党就可以宣传“科学院院士保罗·朗之万出席”的会议了。甚至有一次,党的宣传海报宣布“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朗之万”。朗之万可能和任何人一样值得获得诺贝尔奖,但事实是他从未被授予。令他的朋友保罗·里维 (Paul Rivet) 非常懊恼的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人任由自己被利用而毫无怨言。
因此我把我的护送介绍给了朗之万。我们本应在早餐后直接下船,但由于浓雾,我们在船上待了大半天。弗雷歇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如下的话:“在伦敦,人们说你在芬兰当间谍时被抓了个现行。但我不相信。如果是那样的话,芬兰人会枪毙你。他们没有,所以你不可能是一个。” 他的公理式推理无可挑剔。
萨德龙向我解释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刚从伦敦执行一次科学任务回来。我们感叹着这可怕的时代。我又和我的护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你们犹太人真是了不起。1914-18年战争期间,我在军队里遇到过一位犹太律师。我们的团正在敌占区行军。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个自由人。如果我想离开,我就可以离开。’ 然后他就走了。他第二天回来了。我问他:‘你昨天到现在都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想了很多。’”
在离开我之前,这位特工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在勒阿弗尔,我要把你交给宪兵。他们不像我这么思想开明。你最好通知你的家人你到了。写封信给我;我会亲自寄出去。” 于是我给埃夫琳写了一封短信,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说最紧迫的问题是给我找个律师。我请萨德龙口头转达同样的信息,并补充说:“确保律师不姓莱维 (Levy) 或科恩 (Cohen)。” 我不知道信息是否被转达了,但一段时间后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我的“辩护人”("defender") 名叫埃德蒙·布洛赫律师 (Maître Edmond Bloch)。
我们靠岸后,宪兵把我带到了勒阿弗尔的监狱。与我在芬兰、瑞典和英国参观过的设施相比,这座法国监狱显得相当肮脏,维护得很差。被彻底搜身后,口袋里剩下的一点东西也被没收了,我被关进一个明亮宽敞的牢房,设计用于关押数人,但除了我空无一人。我唯一的消遣是辨认装饰在粉刷墙壁上的铭文和笨拙的淫秽图画。第二天,当我被告知律师的名字后,我给他写了信,说明我的士气无法长期承受单独监禁。我想,既然我的信不可避免地要被监狱管理部门阅读,我的待遇可能会有所改善,如果需要,我的律师和家人也会利用这封信达到目的。后来我发现我的父母和妹妹认真对待了我的抱怨,非常担心。无论如何,它对我的看守者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被转移到隔壁牢房,那里已经关押着两名囚犯。一个是职业偷猎者,他讲述着村庄巫术的故事,并准备发誓说那是真的。在审判时,他对预审法官说:“法官大人,禁猎期您吃野鸡的时候,您觉得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我这里。” 这番话并没有使他免于被判六个月,他当时正在勒阿弗尔服刑。如果不是缺乏女性陪伴,他本可以轻易地安于自己的命运。但他已经煞费苦心地在出狱的那一刻就安排好了补救措施:他的妻子会来等他,街对面旅馆的房间已经预订好了。
根据规定,囚犯应该被允许在户外散步并使用图书馆。在勒阿弗尔,没有户外散步的可能性,也没有图书馆。在我一再要求下,有人设法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半打英文书,是某个早期囚犯留下的。就这样,我读了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精彩的小说《死神来迎接大主教》(Death Comes to the Archbishop),以及一本我此后再也没遇到过的引人入胜的书:一位捷克 (Czech) 锁匠的回忆录,他因漫游癖而穿越俄国,然后是西伯利亚,到达遥远的北方。在那里,他曾为一个主要由爱斯基摩人 (Eskimos) 居住、白人极少的广阔地域担任锁匠、工程师、牙医,甚至民选法官。作为法官,他的职责是执行唯一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向爱斯基摩人出售酒精处以死刑,并记录处决情况。他描述了春天的来临,在极夜结束前不久,成群向北迁徙的鸟儿预示着春天的到来:高高飞翔的鸟儿已经被太阳照亮,而地面上仍然是黑夜。
负责监狱的典狱长以残暴著称。我并不太为自己担心。一方面,我被登记为“韦伊中尉”("Lieutenant Weil"),我的军衔对狱警提供了一些保护。尽管如此,当被告知我将被转移到鲁昂 (Rouen) 时,我还是很高兴,在那里,在两名宪兵的陪同下,我和另一名囚犯被火车带走。当一名宪兵拿着手铐走近另一名囚犯时,他本能地退缩了。“来吧,”宪兵对他说,“这没什么可耻的。”
就这样,在二月中旬,我开始了在鲁昂军事监狱的逗留,讽刺的是,它以其所在街区的名字被称为“好消息”("Bonne-Nouvelle")。我在那里待了将近三个月。这座监狱相当拥挤,主要关押着因发表“失败主义言论”而被捕的人,比如“宁做活着的德国佬,不做死了的法国人”之类的话。达拉第政权、假战 (phoney war)、官方口号(“我们将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的明显愚蠢,引发了一股士气低落的浪潮,军事司法徒劳地试图阻止。
最初几天我有一个狱友,但埃夫琳、我的父母和妹妹开始定期探望并给我带书后,我设法说服了思想开明的监狱长把我安排到一个单人牢房,在那里我不仅可以保留家人每周带来的书,还可以保留笔、墨水和纸张。牢房狭长,由一扇高窗采光,透过铁栏杆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家具包括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小写字台,上面有一个架子、一个水槽和一个抽水马桶。门像保险柜门一样,但开有通常的窥视孔,打开时钥匙哗啦作响,铰链吱嘎作响——恰当地诠释了“像监狱大门一样优雅”("as graceful as a prison gate") 这句表达。我随身带着《薄伽梵歌》、《唱赞奥义书》、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及在我妹妹热情推荐下,雷斯枢机主教 (Retz) 的回忆录。我也有恢复数学工作所需的东西。很快我收到了大量邮件,这些邮件必须先由监狱官员和预审法官阅读;有时会有被审查删节的段落。几乎所有我视为朋友的人都在这个时候给我写信。如果某些人在那时让我失望了,我并不为发现他们友谊的真正价值而感到不快。在我刚到鲁昂时,信件大多围绕以下主题变化:“我足够了解你,相信你会尊严地承受这场磨难……”(有时前面会加上主题:“你知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但没过多久,语气就变了。两个月后,嘉当写道:“我们并非都像你一样幸运,能坐着不受打扰地工作……”
我又学会了用手写长文。我回到了在芬兰中断的关于积分的布尔巴基报告。弗雷曼,展现了真正的友谊,急于弥补我1937年交给他关于群上积分的手稿出版方面无法解释的延迟;他把校样寄到鲁昂让我校对。这项工作是题献给埃利·嘉当的,我也是在鲁昂写的献词。有一天,我的父母,像往常一样来鲁昂进行每周探视,在进门路上停下来和监狱长打招呼。他对他们说:“你儿子做得很好。他终于完成了一篇花费了他很大力气的引言,但现在他对此很满意。” 监狱长通过阅读我的邮件对我所有的工作了如指掌。
按照规定,我每天有半小时的散步时间。这并不完全像梵高 (Van Gogh) 画作中描绘的囚犯散步。每个囚犯被分配到一个大圆的一个扇区,圆心是看守塔。走快点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在我的牢房里,我每天也会做些锻炼。散步区长着几棵树。春天它们的叶子开始长出来时,我常常对自己背诵《梵歌》中的诗句:“Patram pushpam phalam toyam...” (“一片叶,一朵花,一枚果,一捧水……”——“一片叶,一朵花,一枚果,水,只要是纯净之心奉献,皆可为供品”)。只有一次,偶然地,我和一个狱友共享了我的散步区,他因监禁的致命无聊而痛苦不堪。他不知道在等待审判期间他有权让人给他带书;他告诉我他喜欢阅读。如果每个被拘留者都被告知他的权利,许多无谓的痛苦就能避免。生活是由琐碎细节组成的:也许在监狱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清楚这一点。西方国家的规定通常远非不人道;但对那些生活因此而被决定的人来说,这些规定是以残酷还是仁慈,或者仅仅是以封闭还是开放的心态来执行,可能会造成天壤之别——苦难与尚可忍受生存之间的区别。
最肯定的是,我从未经历过监禁中最严酷的方面。典狱长们,大多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绝非虐待狂;毫无疑问他们的座右铭是“避免麻烦”。经验教会了他们足够多的实用心理学基本概念,能够识别出哪些被监管者可以信任,哪些不能。例如,对我来说,每周一次的牢房搜查,寻找剃须刀片、锉刀或其他逃跑工具,仅仅是走形式。然而,有一次情况不同。门开了,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巨大噪音。规定要求牢房门打开时,囚犯要冲到牢房尽头立正站好。于是我“冲”了过去,我想是相当懒洋洋地,并摆出一个模糊类似“立正”的姿势。值班的狱警,我认识他,是个矮小、有点易怒的人。他开始仔细摸遍床垫的每一寸,然后是桌子底下。毫无疑问,他看到我嘴唇上露出一丝讽刺的微笑。他挺直了身子,说:“我的手艺是从老狱警那里学来的。我按照他们教我的方式履行我的职责。” 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狱警;他是一位传统的守护者。
与此同时,对我的“案子”的调查仍在继续。可以推断,它实际上相当简单。预审法官名叫勒莱姆 (Le Lem)。我相信,他是一位文职法官,在战争期间穿上了军装。在我看来,他被要求在职责范围内做的事情——主要包括起诉“失败主义言论”——在他看来似乎很愚蠢。有一天,他传唤了埃夫琳,当她谈到我们在芬兰一个岛上逗留时,他用带着怀旧意味的声音对她说:“你们在那个岛上做了什么?你们去钓鱼了吗?”
我也见过几次我的辩护律师布洛赫先生。我们第一次谈话后,关于我的案子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闲聊,他让我了解世界大事。当他告诉我芬兰战争是如何结束时,我深感悲痛。然而,并非从他那里我得知了纳尔维克远征 (Narvik expedition):我是在去洗澡的路上从一个狱友那里听说的,他凑到我耳边低语:“挪威那边打得一团糟。”⁵ (Ça chie en Norvège.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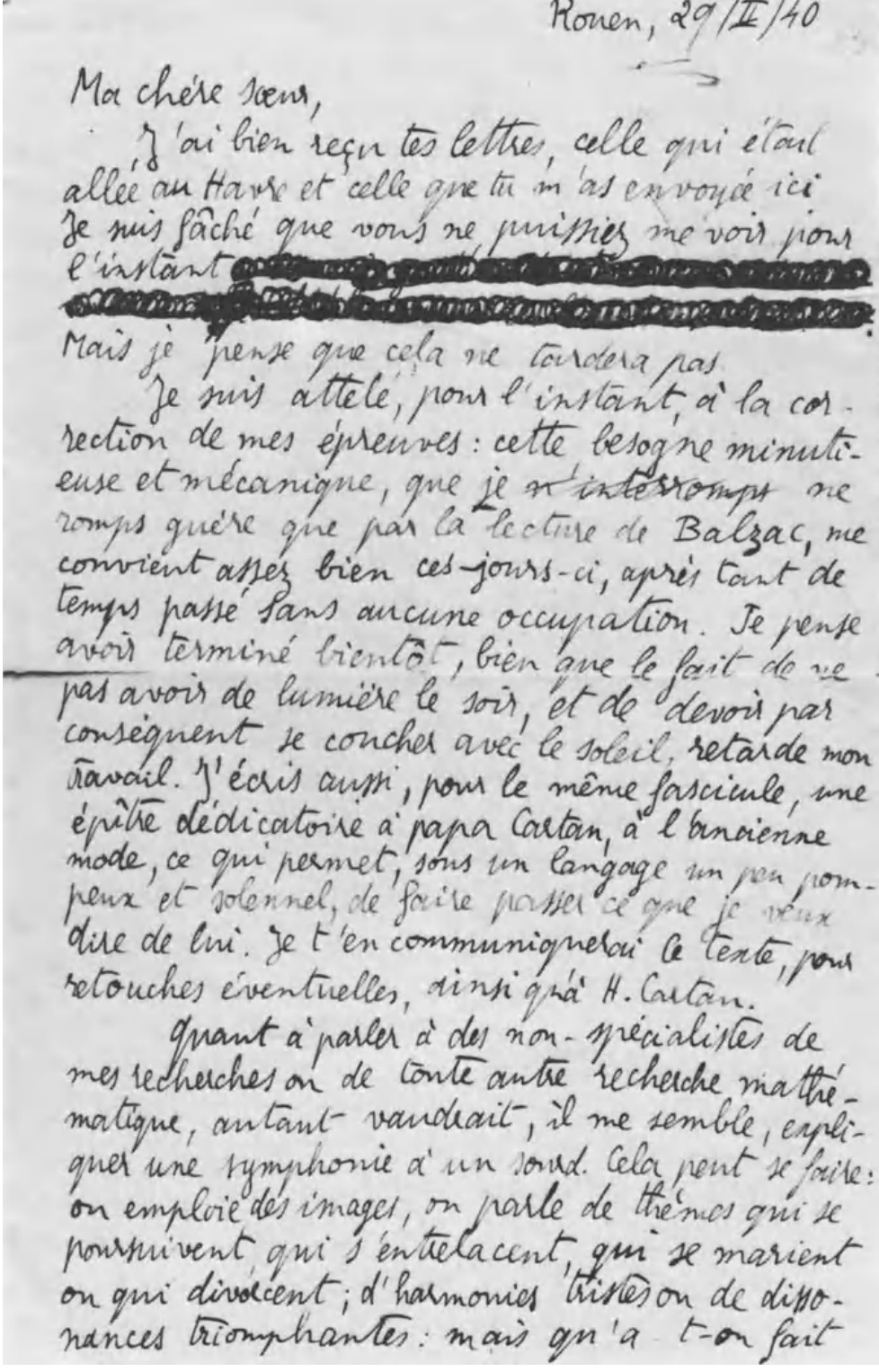 [图片未提供描述]
[图片未提供描述]
四月,我在代数曲线之间的对应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algebraic curves) 方面取得了自认为重大的进展。还有相当多的空白需要填补;特别是,我仍在寻找某个难以捉摸的引理 (lemma) 的证明。我妹妹坚持认为我未能找到这个证明是勒莱姆上尉诅咒的结果,我注定永远找不到它。在正常时期,我会在发表任何东西之前等待。这次,未来在我看来如此摇摇欲坠,以至于我认为在《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一个简短的结果概要是恰当的;是埃利·嘉当提交了这篇注释。
所有这些都记录在我两次探视之间寄给埃夫琳的信中。大部分时间她和她的母亲以及当时八岁的儿子阿兰在索莱姆附近的帕尔塞。以下是这些信件的大部分内容:
(3月4日)[...] 关于我自己我能说什么呢?我像蜗牛一样,缩回了我的壳里;几乎没有什么能穿透它,无论是进是出。我想我这样做不是很勇敢,但最重要的是保持自身的完整。别担心:在这个壳里我还是原来的我,还是你的;总有一天我会出来的,我们会再次找到彼此。努力保持快乐和勇敢 [...]
(3月30日)[...] 我真希望能有关于索莱姆圣周六仪式的描述——牺牲羔羊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明白,希望能有细节。我希望能看到乡间初发的嫩芽。在这里,散步时,如果我伸长脖子,可以看到一些树的上部枝条,确实,它们开始发芽了,但是,唉……我想这得等到明年了。 [...]
实际上,自从见到你之后,我的算术-代数研究进展顺利。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以至于我希望能在这里有更多时间,在平静安宁中完成我开始的工作。我开始觉得没有什么比监狱更有利于抽象科学了。我的印度朋友维杰亚拉加万常说,如果他在监狱里待上六个月或一年,他肯定能证明黎曼猜想 (Riemann hypothesis)。这也许是真的,但他从未得到机会。[...] 所有这些,加上我的阅读,让我很忙碌。我的巴尔扎克读完了,但我不时重读片段;读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如果我口述给你听我们会多么开心;想起所有那些会让我们一起笑的事情。
这些也是不得不推迟一段时间的乐趣。我还在读雷斯的回忆录⁷,但当我停下一两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后,我很难再捡起来:我总是迷失在他三重、四重纠缠的阴谋线索中,完全迷失方向。人对他很有同情心,但如此迂回的心智永远无法成就伟大的事业。当我问妹妹他是不是那不勒斯人 (Neapolitan) 时,她 horrified。看来贡迪 (Gondi) 家族来自佛罗伦萨 (Florence)。但他没有佛罗伦萨心智的宏大简洁。我仍然确信他血管里一定流淌着南方血液(当然是南意大利)。
然后总是有我的梵语书。我在读《梵歌》,小剂量地读,就像应该读这本书一样。吸收的细节越多,就越钦佩它。我很好奇想知道它会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然后还有我和妹妹的通信;此刻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因为它只涉及最抽象的主题。例如,希腊数学:她对此有一些想法。前几天,她和母亲在探视室来看我,我因为说了三个希腊词而被值班看守严厉训斥了。当然,我们不允许说除法语外的任何语言。笼统地反思了我的工作后,我还写了一篇非常冗长的论述,以写给她信的形式,因为她一直缠着我这样做——但我警告她,她甚至不能试图去理解,否则就会流于肤浅。恐怕她不会理会我的警告。[...]
(4月7日)我的数学工作进展超出了我最疯狂的希望,我甚至有点担心——如果只有在监狱里我才工作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得安排每年被关两三个月?与此同时,我正在考虑给有关当局写一份报告,如下:“致科学研究主任:最近有幸通过亲身经历发现监狱系统设施为纯粹和无私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我冒昧地,等等等等。” [...]
至于我的工作,进展如此顺利,以至于今天我正在给老爹嘉当寄一封给《科学院院刊》的注释。我从未写过,也许从未见过,《科学院院刊》上有注释能在如此小的空间里压缩如此多的结果。我对此非常满意,特别是因为它写就的地点(这在数学史上必定是第一次),也因为它是一种让全世界所有数学朋友知道我存在的好方式。我为我定理的美而激动不已,但这当然很难传达给你。但我在想,当你回到巴黎时,你会看到我写给我妹妹的那封14页的信;当然不要读数学部分(我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我可怜的妹妹试图读它时头痛得厉害),但里面有几个比喻可能会让你觉得有趣。[...]
尽管有数学,我也不介意把我的定理捕捞与在萨尔特河 (Sarthe River) 钓鱼(当然是在你的监督下,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交替进行,或者与骑自行车交替进行。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的。这里有几行我非常喜欢的《梵歌》诗句:“一片叶,一朵花,一枚果,一些水,无论谁以爱奉献,这份爱的供品我以他灵魂的虔诚接受。”
说话的是克里希那神。在泰米尔语中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吃的面包,我们喝的水,我们嚼的槟榔,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克里希那。” 几乎不可能翻译所有这些——在所有与神有关的事情上,我们的语言都偏向于人格神的观念,这与印度人的观念完全不同。
我还通过翻译我另一本梵语书的一章来取乐;这正是浮士德 (Faust) 在他著名的开场独白中所说的:
“请教我,尊敬的长者!”:纳拉达 (Narada) 带着这些话来到萨纳特库马拉 (Sanatkumāra) 面前。他回答他:“把你所知道的带来给我;然后我会进一步教你。” 他告诉他:“尊敬的长者,我知道《梨俱吠陀》(Rig-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娑摩吠陀》(Sama-Veda),第四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第五部传说集 (Legendary Lore),《吠陀之吠陀》(Veda of the Vedas),我知道仪式、数学、逻辑、道德、神学、梵学 (brahmanology)、鬼神学 (demonology)、占星术 (astrology)、爬虫学 (herpetology)。这些我知道,尊敬的长者。我就是这样,尊敬的长者,知道书本的科学,但不知道存在的科学。我曾听像您这样的人说过,尊敬的长者,了知存在科学者能渡过悲伤。我,尊敬的长者,正在悲伤。我请求您,尊敬的长者,教我渡到悲伤的彼岸。”他告诉他:“你所命名的所有这些都只是言语。它们只是言语,《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第四部《阿闼婆吠陀》……”(整个列表又被枚举了一遍)。²
之后他教授了存在的科学。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但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被破坏了。当这段文本写成时(它非常古老——大约公元前6世纪,我想)它拥有冥想所需的一切。印度哲学家们,他们无休止地研究和评论这些文本,也在其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但这,我认为,有时是因为他们把东西放进去了……即使在今天,在许多高等种姓中,一个印度教徒生来就属于某个哲学流派;这并不妨碍他相信任何他想相信的东西,但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印度教徒,他总是会声称他只是在解释他流派的原则,并且没有矛盾。
如果我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我一年也说不完,而且你可能不会觉得非常有趣——但我几乎无法通过描述我牢房的墙壁来取悦你,这是我眼前唯一的风景;而在《梵歌》的所有事物中,我能献给克里希那的只有水,偶尔还有水果——他们给我当甜点的一个橙子或香蕉;有时,最近几天,一片年轻的叶子,还皱巴巴的,被风吹到散步道上——但没有花(不过现在还不是季节;也许你那里也没有)。我很乐意献上一个芒果,但在这里很难找到。[...] 附言:我父亲担心我会得书写痉挛。
(4月16日)我的埃夫琳,几天前我收到了你4月6日的信,信中充满了我的牢房急需的花朵(我为什么会想象你那里还没有花呢?)以及青草甚至蜗牛的花园气息。每当我从数学中停下来时,所有黄水仙的花瓣都赏心悦目——我确实还不时停下来。但你变得对我来说太博学了:我丝毫不知道给豌豆搭架子是什么意思;你将不得不教我,暂时是理论上,也许某天实践中。我妹妹说我离开这里后应该当和尚,因为这种制度对我的工作如此有利。我将加入索莱姆的本笃会,我将学习格里高利圣歌 (Gregorian chant),我会偷偷溜出来到你的花园里看你。但是当帕尔塞的好人们看到一个和尚如此频繁地藏在你家院子里时会怎么说呢?也许他们会向院长 (Father Superior) 举报我?
这里没有花;我早上看到的树木一天比一天绿,今天早上散步时空气中带着淡淡的春意;但唉,它并不能真正到达牢房,我不得不满足于一天快结束时一小缕阳光。现在数学方面的事情平静了一些;是时候推敲证明的细节了,这从来没什么乐趣。我没什么新书可读。不久前读完了雷斯的回忆录,我现在正在重读,第二次读有所改善:既然熟悉了事件(叙述得相当笨拙),我不再需要绞尽脑汁去追踪这些阴谋的线索,我可以更注意他的描述性段落和他的普遍反思,这些都很有趣。你觉得舍夫勒斯小姐 (Mademoiselle de Chevreuse) 怎么样,她对待情人就像对待她的裙子——“她想上床就带他们上床,两天后就纯粹出于恶意把他们烧掉。” 蒙巴宗夫人 (Madame de Montbazon) 谈论的就是这位年轻女士,当时她告诉雷斯“她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同时被一个比魔鬼还坏的老妇人和一个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蠢的年轻女人所取乐”(那个老妇人是盖梅内夫人 (Madame de Guéméné))。谈话继续如下:“我对她的话习以为常,但由于不习惯她的甜蜜,我觉得很有趣,尽管考虑到背景,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她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倾向于放过这样的机会;我让步了很多;我的眼睛没有被挖出来;我建议我们进她的私人房间,但有人建议我们首先去佩罗讷 (Péronne);我们的恋情就这样结束了。”
我继续,和以往一样享受地,阅读《梵歌》。我曾经常重读某些段落,但我从头到尾通读它只有一次,在1923年或1924年。我对自己梵语记得足够好能读懂这样的文本感到满意——当然,不断借助翻译。署名西尔万·莱维的那本,经检验,相当不均衡:有些部分完全配得上他(这就说明了一切),而另一些部分翻译甚至似乎都不准确。由于这项工作并非他本人完成,而是由一名学生在他的监督和参与下完成的,也许他只在他最喜欢的部分动了手,或者当他的学生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时。此外,他总是说,只要只给出一行梵语的一种翻译,就总有至少一处误译。
我们重新开始了我们的布尔巴基通信,以期准备再出版几期分册。我还向迪厄多内建议我们重新启动我们的《公报》(Bulletin),刚刚收到几页题为“部落:普世的、非周期的、布尔巴基式的公报”("The Tribe: An Ecumenical, Aperiodical, and Bourbacchic Bulletin") 的东西,开头是一封信,始于“致我们所有在布尔巴基的兄弟们,致敬与祝福”,结尾如下:“让大脑除锈!让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让打字机的嗒嗒声和印刷机的嗡嗡声将布尔巴基的名字传遍全球!阿门。” 信的其余部分风格相同,只是更好。
如你所见,我不得不求助于雷斯、迪厄多内和诸如此类 (tutti quanti) 来帮助我步履蹒跚的想象力;今天最好就此打住。这几周紧张的工作让我相当晕眩。在其他时候,这本该是休个小假的时候——去看看郁金香田,或者壁画,或者只是盛开的樱桃树。现在我这些都没有——除了你信中的花(而这些远非一无所有)。复活节羔羊以及本笃会僧侣和修女的故事也很有趣。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修女。她们也唱格里高利圣歌吗?(在她们中间,对僧侣来说,是否有“十五六岁的年轻修女”?)⁹ [...]
附言:不要太担心给阿兰解释分数。一段时间以来,初等教育过于强调它们了;它们其实没那么重要。我猜想,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学会机械地操作它们,而不试图去理解——尤其是乘法和除法。另一方面,既然你提到语法分析,确保他做得绝对完美,因为它对于学习拉丁语(他最好毫不迟延地开始学)至关重要。即使在词序复杂的句子中,能够识别主语、直接或间接宾语等也至关重要。对于以后的学习来说,不放过这方面任何一个最小的错误非常重要。(所谓的“逻辑”分析也很重要,但我猜他现在还没做任何这方面的工作。)
(4月22日)[...] 我的数学狂热已经消退;我的良心告诉我,在我能更进一步之前,我有责任推敲证明的细节,这件事我发现如此枯燥乏味,以至于即使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上面,也几乎没什么进展。我刚刚重读完雷斯;我也读完了《梵歌》,这确实是那些可以无限重读的文本之一。我很久以前就读完了我所有的巴尔扎克,并把书还给了家人。布尔巴基无所事事。我完成了关于我们拓扑学后续工作的观察笔记,写给嘉当和迪厄多内,并告诉后者我不会继续回复他一直用来淹没我的关于积分的论文。上周我重写了给《粉红杂志》(Revue Rose) 的文章并寄出,完全重写,比以前长了三倍;我请我妹妹校对校样,前段时间我还请她和弗雷曼谈谈,解决关于我的书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不想再讨论了。可以说,我现在或多或少在度假。这个地方不像适合工作那样适合度假;在这种温和的天气里,我宁愿坐在那个被常春藤环绕的长凳上,靠近散发着蜂蜜香味的黄花,在那里我会和你谈论克里希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你没有在阅读,而是在忙着观察树木和植物春天的变化,我对此毫不惊讶。我很高兴你在这个季节待在乡下,而且是在春天真正是春天的地区——想想斯特拉斯堡,那里尽管有花,却立刻就是夏天了。“所有季节中,”克里希那说,“我是花季。” 但他没告诉我们是哪些花,而在印度,森林花卉和山地花卉之间有巨大差异(在克什米尔,我曾在索纳马尔格,“金色草甸”的山谷露营,四月份那里黄花盛开得如此茂密),或者还有平原的花——这些很少,但有一种开着绚烂花朵的大树,我忘了它的名字。这些大花朵远在叶子出现之前就开放了,树看起来像是在阳光下着了火,春天阳光已经很热,很快就变得灼热。还有绿色的小长尾小鹦鹉,它们像会移动甚至会啁啾的花——但它们没有季节。还有花园花卉,但这些需要水罐夫和园丁许多天的劳动……我是否告诉过你,在孟买,没有花园的人常常有园丁,他的工作是通过与确实有花园的园丁建立良好关系来保持主人的公寓鲜花盛开?还有花,很多花,在重要客人到达和离开时也是必需的,他们的脖子上挂着芬芳的花环:通常只有两三串花环,但在特殊场合,多到受害者能承受并且还能站立的数量。我见过有人在这些花环的重压下弯着腰。[...]
为国效力
(Serving the Colors)
我于1940年5月3日星期五被“审判”。那天早上,监狱理发师来给我打扮。他是囚犯之一,自从我到达鲁昂以来,每周来给我刮一两次胡子:自然,作为囚犯,我自己是不允许使用剃须刀的。这个人教了我一句理发师的谚语,“刮好泡沫等于刮好一半”,此后我常常对自己重复这句话。这位理发师是意大利人,在鲁昂拥有一家妓院。他说,他的老鸨告发了他,希望他在服刑期满后被驱逐出境,这样她就能成为妓院的独家老板。
审判是一场演得很糟糕的喜剧。法官们都是军官,穿着制服,军事检察官也是。布洛赫律师穿着黑色长袍,庄严肃穆,荣誉军团勋章 (Legion of Honor) 的红色绶带在其上格外醒目。我的家人在场。埃利·嘉当以他特有的仁慈,同意来为我作证。从技术上讲,我被指控的是未按时报到,而不是逃兵,因为在我犯罪时我实际上并不在军队服役。布洛赫律师的长袍及其戏剧性的袖子给了他相对于检察官的优势。除了这个细节,起诉书和辩护词在我看来都同样平淡无奇。没有人注意埃利·嘉当,甚至没有请他坐下。在宣判(用囚犯的俚语说是“敲棒子”("clubbing"))之前,主审法官按照规定的仪式问我是否有话要说。现在不是虚张声势的时候。我说如果我必须穿上制服,我准备好做军队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但我无法让自己说出悔改的话。
此外,我可能说的任何话,实际上布洛赫律师或任何其他人可能说的任何话,都不会影响结果。接下来的冬天,我的朋友卡瓦耶斯 (Cavaillès) 将告诉我,在巴黎战争部 (Ministry of War) 的密码办公室,正是他亲自为将我的判决规定给法庭的电报编码。人们常常有理由怀疑普遍意义上的“司法”特别是“军事司法”的自主性,但像这样当场抓住它的机会并不多见。
因此,我被判处该罪行的最高刑期,即五年监禁,当然也被剥夺了军官军衔。听证会结束后,检察官立即会见了当天的罪犯(我们有三四个人),告知我们上诉的权利。然后,似乎特别针对我,他表示我们也可以请求缓刑,作为交换在战斗部队服役。他似乎暗示我的这种情况下的请求会得到支持。布洛赫律师建议对我的定罪提出上诉,这个想法在我看来很愚蠢。我利用了允许我考虑的24小时,提交了被派往战斗部队的请求。我几乎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多么明智——如果一个月后,当鲁昂监狱因德军推进而疏散时,看守们枪杀了那里的囚犯,而不是冒着用这额外的负担减慢他们逃跑速度的风险,这真的是真的话。至少,流传的谣言是这样的。
回到好消息监狱,我必须换下我一直穿着的自己的衣服,换上囚服。监督这次操作的看守对我说:“他们把人培养成科学家,然后看看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可怜的法国!” 除了衣服,我的日常作息保持不变。接下来的星期六,我被告知我请求缓刑并在部队服役的请求已被批准,并且从那一刻起我就自由了——并被传唤周一去瑟堡 (Cherbourg) 报到。
埃夫琳计划第二天来监狱探望我,我知道她那天晚上会到达鲁昂,在那里的一家膳宿公寓过夜。我设法找到了那个地方,用鲜花装满了房间,并在晚上在那里给了她一个惊喜。自十月份以来,我们只在好消息监狱探视室的双层铁栏杆后面见过面。第二天,我的父母和妹妹,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他们,来和我们团聚,我们在塞纳河畔郁郁葱葱的诺曼底乡村散步度过了一天:苹果树正在开花。德军的推进刚刚开始——我如此迅速地转变为一名士兵可能并非巧合。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我母亲描述她计划对奥古斯特·孔德街公寓进行的改进,“等你休假回家时”;对我来说,这些计划似乎有些不真实。
周一我和埃夫琳一起去了瑟堡,她决定陪我。她随身只带了在鲁昂过夜所需的东西,而我几乎不比她多。我们从未如此轻装旅行过!在途中的一个车站,有一个免费为士兵提供服务的食堂。拿着我的报到令,我现在是一名士兵了,我作为士兵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为我和妻子点了咖啡。
在瑟堡,我被打扮成士兵。除了颜色,我几乎看不出这身蓝色制服和我刚在鲁昂脱下的囚服有什么区别。我将要服役的连队的连长在平民生活中是一位新教牧师 (Protestant pastor)。他已经熟悉了我的案子,给我做了一番道德说教,劝诫我赎清过去的错误,勇敢地履行职责,并告诉我德国人刚刚在阿登地区 (Ardennes) 取得了突破。
我在诺曼底的整个经历中,只有几段清晰的记忆仍然漂浮在我的脑海里。在瑟堡,我的连队专门负责每天去火车站将炮弹装上开往北方的火车。我对战友们说:“别把自己累坏了。这些炮弹反正最终会打到你们伙伴的脸上。” 我的推理只有一个细节错了:德国人装备太好了,而且也太匆忙了,不会有兴趣使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炮和弹药。
埃夫琳的旅馆就在我连队每天经过的路线上。有一次,和我的战友们安排好后(他们对这次冒险兴奋不已),我溜走在埃夫琳的房间里待了一天,在返回行军中重新归队。另一天(我想是星期天),我们俩在一个俯瞰海军基地的小山上享用了冷龙虾和一瓶墨丘利 (Mercurey) 葡萄酒的野餐。我从未觉得墨丘利葡萄酒如此美味。
很快埃夫琳又该离开了。随着德国人的逼近,瑟堡正变成一个军事禁区;没有特别授权,任何人都不能乘火车。火车和道路上充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埃夫琳必须回到她在帕尔塞的母亲和阿兰身边,经过漫长而不适的旅程后她才到达那里,包括在勒芒 (Le Mans) 火车站度过的一整夜。
六月初,我被调到科唐坦半岛 (Cotentin peninsula) 海岸的圣瓦斯特-拉乌盖 (Saint-Vaast-la-Hougue)。我被分配到一个机枪连。一些武器被部署用于防空。不时地,当看到,或以为看到,一架德国飞机时,就会开几枪。有一次机枪手声称击中了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实际流血事件:我曾帮忙搬运弹药箱。
这些无害的任务让我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我在一条小溪边晒日光浴,在那里我会读莱夫谢茨关于位置分析和代数几何的书——霍奇 (Hodge) 曾说这本书所有重要的陈述都是正确的,所有其他的都是错误的。
那时经常听到关于德国伞兵 (paratroops) 的疯狂谣言。关于伪装成修女、裙子下藏着摩托车的伞兵的故事至今仍被提及。还有人说伞兵穿着带弹簧底的靴子,据说是为了吸收着陆的冲击力。有一天,一个村民来向我连队的上尉报告说,他看到一个伞兵降落在本堂神父的花园里。当他用带弹簧底的靴子着陆时,他又弹了起来,升上了天空。
几天里,我们看到英国增援部队登陆并通过村庄前往战斗区域。那时天气已经很热了,村里的妇女们给英国士兵递水。我看到一个中士退缩着把水泼在地上。他可能曾在殖民地服役过,并形成了所有“土著”("native") 水都危险不能饮用的观念。
除了法国广播电台 sketchy 的报道外,我们几乎没有得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信息,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正在迅速恶化。有一天,一个准备和家人一起去波尔多 (Bordeaux) 地区的村民问我,他认为他们在那里是否安全。我毫不犹豫地肯定地回答了。很难摆脱这样的想法——1914年的遗留观念——即前线必须在某个地方稳定下来,很可能是在卢瓦尔河 (Loire river)。
有一天,我们看到天空中浓密的黑云。也许它们没什么特别的,但很快就有谣言说鲁昂正在燃烧,这些黑云来自燃烧的油轮。我从未弄清楚这个谣言是否有任何真相,也不知道它是如何传到我们这里的。
6月17日,该团转移到水边的一个军事设施,在一个有着十七世纪沃邦式 (à la Vauban) 防御工事的旧围墙内。据说德国人正在逼近。扩音器广播了贝当 (Pétain) 宣布他已请求停战的讲话。我一点也不难过;从我所能观察到的普遍无能和士气低落,以及我所看到和听到的难民潮来看,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唯一可能的出路。此外,我对英国人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尽管我很难解释清楚。该团采取了防御阵地;有那么一刻我印象中,出于某种错位的职业责任感,我们的军官正带领我们走向一场“光荣”但完全无意义的死亡。我可能错了,但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几个战友。我们的牧师中尉,总是爱管闲事,听到了我说的话,立刻把我关进了一个类似棚屋的地方。
我正在研究可能的逃跑方式时,门开了。我的一个战友解释说刚刚下达了撤离命令;中尉准备抛弃我,但士兵们抗议了。于是我重新加入了我的连队。
于是下达了命令,部署一个机枪班在一名中士的指挥下行动,用猛烈的火力掩护撤退。德国坦克尚未出现,但我们知道它们不远了;德国飞机在天空中到处飞翔,完全没有遇到抵抗。我问那位中士——一位预备役军人,不是职业军人——:“那么我们就是牺牲品了?”他向我保证他无意让我们送死。就在这时,传来了放弃机枪并在海滩上与团部会合的命令。后来我被告知,严格从我们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命令是我们军官方面的一个 egregious error:机枪火力可以阻止敌机过于靠近。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自己在海滩上。一架飞得很低的德国飞机在我们大约300码外投下了一枚炸弹,显然无意伤害我们。我们被登上一艘似乎在等我们的小轮船,它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出海了。我和我的战友们对我们的目的地一无所知;我们的军官们可能了解得也不比我们多。有人谈论布雷斯特 (Brest),但第二天早上我们下船时,我们是在普利茅斯 (Plymouth)。
离开瑟堡后,我就没刮胡子了。在英国登陆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一旦可以洗漱,就是刮掉我刚长出来的胡子——但我保留了我刚萌芽的小胡子。一位英国平民问我战争是否失败了,我向他保证我对英国充满信心。我们被登上一列火车;旅途持续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到达时,我们的团被编入一个已经挤满了法国军队的营地。这个营地设在英格兰中部,离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Stoke-on-Trent) 不远,主要目的是安置从挪威回来的部队。我以为它是由佩图瓦尔将军 (General Pétoire) 指挥的,这个名字在我看来不知何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是某位贝图阿尔将军 (General Béthouart)。
这恰好在6月18日之后,也就是戴高乐向法国人发出号召的时候。营地里的军官甚至士兵都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加入戴高乐派 (Gaullists) 的力量。有传言说,加入戴高乐事业的军官很有可能迅速晋升,特别是如果他能带上他的部队。一个摩洛哥连队的指挥官把他的部下召集到充当他“办公室”的帐篷里,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一个中士面前,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签名。之后,他们被告知他们刚刚加入了戴高乐军队。我没有效仿的冲动。尽管如此,情况自去年以来已大为改变。我写信给剑桥的同事们说,如果我不能完全致力于数学,我并不反对将我的科学知识用于为英国服务,如果我能以任何方式有所帮助的话。
我们在这个营地里无所事事。在特定时间内,我们被允许进城,在那里我们喝啤酒,与英国人(平民和军人)聊天,以及——就我而言——买《泰晤士报》(Times)。我和一些战友通过翻墙延长了这些时间。我被抓住了。为了惩罚这种不当行为,我的牧师中尉判了我几天“监禁”:当然是军事意义上的监禁,在驻地意味着在纪律设施里待一段时间。在营地里,人被限制在一些被铁丝网包围的帐篷里,由一队机动宪兵 (Gardes Mobiles)² 看守。
然后传来了离开营地的命令。整个营地,也就是所有没有加入戴高乐的人,将在布里斯托尔 (Bristol) 登船,前往摩洛哥 (Morocco)。
我仍然被机动宪兵拘留着,他们由于我未知的原因在路上耽搁了。当他们到达码头时,他们本应登上的船只刚刚离岸。我和机动宪兵一起留在了布里斯托尔。我的第一反应是,愚蠢地,感到恼火。事实上,结果证明这是幸运之举:从此我与我的操行记录彻底分开了。谁知道如果我和我的连队一起登船会遭遇什么命运,特别是因为去英国前一天发生的事件——我的牧师中尉假装忘记了——很可能在未来再次出现?接下来的冬天,当我回到法国时,我听说有谣言说我在塔陶因 (Tataouine) 的一个采石场砸石头。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
英国人把机动宪兵安置在布里斯托尔附近一个漂亮村庄旁的木制营房里。不再是他们看守下的囚犯,我被提升为连队翻译,这个角色我发现很合意。除了机动宪兵,还有一个由前西班牙共和军士兵组成的连队,法国人把他们征召进了外籍军团 (Foreign Legion)。英国人完全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一位英国指挥官负责我们所有人。我非常乐意为西班牙人提供我的翻译服务,他们相当郁闷地生活在他们的营房和一个他们用来锻炼的荒地之间。他们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村庄足球场。在他们的建议下,我请求指挥官让他们使用它,他同意了。几天后,当地球队认为应该提议一场比赛,西班牙人轻松获胜。自尊心受损的村民们召集了他们最强的球队——结果再次被西班牙人击败。从那时起,西班牙人,此前一直受到不信任,变得相当受欢迎。他们现在可以在村庄及附近自由活动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个派对,明星是一位有才华的弗拉门戈 (flamenco) 歌手,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已经当了四年兵。此后不久,西班牙人接待了工党议员迈克尔·富特 (Michael Foot) 的访问。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至于我的机动宪兵,西班牙人的存在让他们有机会回忆起,伴随着哄堂大笑,他们曾被派去守卫比利牛斯山脉 (Pyrenees) 一个西班牙共和派难民营的时光。他们的谈话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们对这些不幸者施加的粗暴甚至残忍的待遇。当机动宪兵要求我提供服务时,有时是为了相当奇怪的目的。有一天,他们想明确无误地表明,作为士官,他们免除了整理床铺和打扫营房的义务。他们坚持让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英国指挥官。他的回答是,如果他们不打扫房间,他们的房间就不会被打扫。
幸运的是,我的职责让我大部分时间都很自由。我定期去公共图书馆,并在该地区进行了许多散步;我甚至可以自由地去布里斯托尔,在那里我与大学的同事们取得了联系。一位即将被动员到空军的物理学家绝望地告诉我:“我肯定会被命令轰炸沙特尔大教堂,而且我肯定会炸偏。”
一天早上,英国广播电台宣布了血腥的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Mers-el-Kébir affair),英国舰队认为有必要使在奥兰 (Oran) 附近寻求避难的法国舰队失去能力,结果遭受了严重损失。起初我认为在街上不展示我的法国士兵制服是明智的;然后好奇心战胜了我。我从未像那天那样对英国人充满敬佩。我只听到理解甚至同情的表示。只有一次,一个明显受酒精影响的人对我进行了言语攻击;他的同伴让他闭嘴,告诉他,就像我自己本可以做的那样,法国海军向英国人开火时认为他们在履行职责,无论如何我对此毫无责任。
七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被告知收拾行李——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因为我只有一个帆布背包。旅程结束时,我发现自己被铁丝网包围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法国士兵在一起。他们中有些是曾在挪威纳尔维克战斗过的外籍军团士兵。我们被安置在以前用来关押被俘德国军官的建筑物里。甚至还有淋浴供我们使用。
晚点名时,我们排成队,接受一位年轻中尉的检阅,他由一名看起来像狱警(平民生活中可能确实是)的士官护送。轮到我时,我没有立正。我相信这纯粹是我的疏忽;但当中士对我咆哮敬礼时,我一动不动,他扑向了我。我想他和军官认为这是叛乱的萌芽。我被带到一个小棚屋里锁了起来。稍晚一点,当清楚我将在那里过夜时,一些战友给我送来了毯子——那里的夜晚很冷。
毫无疑问,如果我打交道的是英国人以外的任何人,我不会这样行事,但我以为我了解这些人,结果证明我没有错。早上,我被带到营地指挥官,一位英国上校面前,并被邀请为自己辩护。我说据我所知,我们作为法国士兵仍然有权被英国人视为盟军士兵对待;向盟军军官敬礼只是出于礼貌,但不能作为军事纪律强制执行。我准备出于礼貌向英国军官敬礼,但不是在命令下。如果相反,英国人认为我们是战俘,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说,这正是我和我的战友们希望澄清的一点。此外,我相当真实地向他保证了我的亲英情绪。我的讲话再成功不过了。上校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最希望的就是尽快澄清这一点。他把我送回我的战友们那里,劝诫我鼓励他们合作。
我在这座营地的逗留持续了大约两周。我们组织了一个适度的互教计划,包括由我提供的英语课程。我的方法在于想象我们其中一人可能与营地外遇到的一位年轻英国女士进行的对话。我逐句分析对话,逐渐引入最常用的动词及其变位。在我看来,我的学生们在两周内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身无分文,通过在营地小卖部给我买巧克力棒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的一个战友,一个矮小的电气工程师,是波兰裔犹太人,曾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逃离希特勒后,他移民到巴黎,在那里成了一名普通工人。他告诉我,战争前一两年,法国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曾试图招募他去德国“工作”。一切都为他安排好了:工程师职位、住房、严格的“雅利安”(Aryan) 身份证明;他只需要不时地——每次是不同的人——告诉来访者他在工厂里看到的情况。据那位军官说,这绝对没有风险。我的朋友反对说他的长相和口音会立刻暴露他是波兰犹太人。军官坚持说会提供给他完美伪造的证件,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经过这段徒劳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时间,军官似乎仍然不明白。战争爆发时,我的朋友被征召入外籍军团,并在纳尔维克远征期间担任翻译。必定是从他那里(除非是来自特伦特河畔斯托克附近营地的某人),我得到了1940年法国军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为数不多的战利品之一:一件从纳尔维克带回来的德国军用毯子。他断言法国军队在纳尔维克远征中取得的(尽管是局部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西班牙外籍军团士兵。
七月底,我并非没有遗憾地离开了我的朋友和学生们,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其他国籍的人,搬到了伦敦的白城营地 (White City camp)。这是一个赛狗场,英国人在那里安置了大约2000名法国士兵,几乎全部是最近从英国医院出院的。他们大多是挪威战役或敦刻尔克 (Dunkirk) 的幸存者。在英国接受了伤病治疗后,他们现在要么痊愈了,要么正在康复中。在这里我得到了一张床垫和一条毯子。我的新战友们大多散落在体育场层叠看台下的各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选择在看台顶部找个地方:这里我们可以躲避风雨和爆炸的高射炮弹,但仍然在露天。这种安排唯一的问题是每周六都有赛狗比赛,我们必须为观众腾出地方。确实,有一个区域是为我们保留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观看比赛。当炸弹落在伦敦郊区的另一个体育场,造成伤亡——不仅是观众(英国人本可以轻易接受),还有赛狗:这就太过分了——之后,这些比赛就停止了。
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整个下午在伦敦漫步。事实上,我们甚至晚上也自由,因为翻墙再容易不过了,英国人对这样做的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高射炮火的频繁,尤其是在晚上,使得戴上头盔是明智的。有一次,英国人认为装备防毒面具是谨慎的。我的一些同伴因为没有发给他们而担心,请我代表他们向当局请愿。营地指挥官告诉我:“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拿我的。”
英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确实关心我们的命运。有一天,我们列队接受女王和丘吉尔夫人 (Mrs. Churchill) 的检阅,她们和许多人握了手。一位相当年长的亲法派人士分批邀请我们出去,以提振我们的士气。有一天,他带我去了茶室,还有其他几个士兵,都是善良的法国乡下小伙子,他们无疑宁愿喝开胃酒 (apéritif) 也不愿喝茶。他们已经被环境弄得够拘谨了;更糟的是,我的英国朋友问他们:“中国茶还是锡兰茶?” (China or Ceylon?),并努力让他们相信这两者就像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一样不同。据我所知,这次邀请没有重复。
关于我们将何去何从,各种谣言纷飞。七月,一艘来接伤病员的法国医疗船,由于英德指挥部之间的混乱而在英吉利海峡 (English Channel) 沉没。尽管一些法国人建议最好忘记这件事,但英国广播电台的法语广播却不断提及这次令人惋惜的不幸事件,试图将责任从英国人身上推开。至于我们,不时有传言说我们很快将被遣返,但这些谣言似乎毫无结果。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测量一下这类谣言传播的速度。我只需要在体育场的一端散布一个谣言——越荒谬越好——然后赶紧跑到另一端等待结果。不幸的是,在我有机会进行这项复杂的社会学实验之前,我就离开了伦敦。
戴高乐派的宣传部门试图利用我们模棱两可的处境,试图从我们队伍中招募人员。他们收效甚微;我的同伴们,主要是乡下小伙子,只想一件事:尽快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戴高乐派宣传的杰作是有一天让我们在体育场内集合,然后通过扩音器,用一种强装悲伤的语气宣布,我们回到法国后都将被枪毙。这一说法背后的些微真相是贝当的法令,规定所有自愿移民到英国加入戴高乐派的人都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即使是我们中最愚昧的乡下小伙子也不会不明白,如果贝当派船来接他们回家,那就不是为了在他们抵达时枪毙他们。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后来斯大林确实这样做了;但贝当不是斯大林。我还听到了关于戴高乐派招募方法的其他传闻,所有这些都让我对这个运动,甚至对鼓励或纵容这些策略的那个人,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我可能是当时在英国唯一既亲英又反戴高乐派的法国人。
一到伦敦,我就试图联系朋友。一个德国家庭,我父母的老朋友,借给了我一些钱。虽然所有寄往被占领法国的邮件服务都暂停了,但可以与所谓的“自由”区通信,最好是通过电报。通过亨利·嘉当,他留在了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我得以与我的父母和妹妹联系,并获得了他们在维希 (Vichy) 的地址。在伦敦本地,我找到了我在剑桥的朋友弗兰克·史密斯 (Frank Smithies),他在一个技术部门工作,以及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朋友兼同事,化学家盖龙 (Guéron),他加入了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将在加拿大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的家人留在了法国,但几年后得以与他团聚。我还去拜访了布拉姆 (Brahams) 夫妇,我在剑桥认识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被动员担任飞行员,刚刚被报失踪。他的父母,对再次见到儿子不抱任何希望,勇敢地承受着悲痛;他们欢迎我的热情难以言表。我第一次拜访时,他们问我能为我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允许我洗个澡。” 然后他们请我吃了晚饭。他们住在一套公寓里,位于切尔西 (Chelsea) 一片带有露台屋顶的新建筑群中。在我与他们共度的一个晚上,晚餐快结束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们下到地下室,我请求上到屋顶。他们没有表示反对;只有布拉姆先生在我离开他们时对我说:“如果需要的话,你愿意被土葬还是火葬?” 那次我没有后悔我的好奇心。整个伦敦及其郊区上演了一场令人惊叹的高射炮火齐射。曳光弹在各个方向流窜;四面八方,探照灯扫过天空,试图将敌机捕捉在它们的光束网中。借着它们的光,系留气球闪耀着锐利的金属光泽,在城市周围形成一个明亮的环。没有任何烟火表演能与这样的景象相比,我后来发现圣埃克絮佩里 (Saint-Exupéry) 在《飞往阿拉斯》(Flight to Arras) 中描述过它。正如他的导航员所评论的那样:“你在平民生活中是看不到那个的。”
 伦敦 (1940年8月):A.W.,左起第七人(留着小胡子)
伦敦 (1940年8月):A.W.,左起第七人(留着小胡子)
八月份,德国飞机几乎每晚都来访。这些飞机有两个发动机,由于我未知的原因,它们不同步,产生的脉动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嗡嗡声效果。我确信当时听到过它的人都无法忘记。尽管高射炮火声很大,我已经习惯了,它并没有妨碍我睡觉。尤其是一个晚上,当我已经上床睡觉时,我听到空袭警报,然后是一架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很快就被高射炮火的雷鸣声淹没了。后者会暂时停止,使得嗡嗡声间歇可闻。我想起了理查·施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的《蒂尔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其中轻松、嘲弄的蒂尔主题在反对他的力量喧嚣中反复出现。我对那架德国轰炸机的命运产生了兴趣。每次它的存在再次可闻时,我都感到激动:在我看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胜利。
我在伦敦各处走了很远很广。我再也没有机会在那里待这么长时间了。我参观了它许多可爱的大小公园。我也去了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有时去听从中午到一点举行的音乐会,以弥补晚间演出的缺乏。我不时去法国领事馆打探白城居民命运的线索。我受到了礼貌的接待,但一无所获;也许他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
如果我们的法国人不和女人发生点风流韵事,他们就几乎不配这个名字了。法国人在爱情方面的崇高声誉加上男性相对短缺,再加上穿制服男人的魅力,结果是猎艳并不困难。此外,它们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钱或根本没钱并非秘密。农家子弟,占了白城的大多数,通常很平和,一般几乎不离开营地,但寻找任何可能机会的城里小伙子并不缺乏。他们一离开营地,就有女人来接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摆出久经沙场的虚张声势:当警报响起,女人们想去避难所时,这些吹牛者会拒绝,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百次了。后来,当轰炸加剧时,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至少,根据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私房话)改变了腔调:这次,是他们想去避难,而女人们会说:“但是亲爱的,你已经教会我不害怕了!”
当然,这些接触并非总是没有风险的。我们中的一个,有一天去看医生,被告知:“好吧,老兄,你得了淋病。”“天哪,”他回答,“我从没想过英国女孩会这样。”
九月轰炸加剧了,首先是在贫困的东区 (East End) 街区。我和一个朋友去察看损失。虽然无限更糟的情况还在后面,但这已经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了。所谓的伦敦闪电战 (London Blitz) 发生时,我碰巧在里士满公园 (Richmond Park) 散步。那天下午,戈林 (Göring) 向伦敦上空 unleashing 了他的庞大舰队。多亏了英国的雷达 (radar),它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以至于他没有再试。后来发现,他大量的飞机在到达伦敦之前就被拦截了,但剩下的足以制造相当壮观的景象。懒洋洋地躺在公园的草地上,我看到整个天空充满了互相追逐的飞机。不时地,其中一架会盘旋着从空中坠落;有时我能看到一个伞兵跳伞。那天晚上,从里士满回城的公共汽车或船只都找不到了。我一路走回去,沿着泰晤士河岸。那是一个异常宁静祥和的夜晚。
对我们这些在白城的人来说,离开的谣言似乎越来越具体了。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说“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战斗……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 在收音机里听到他的话,我确信入侵已经开始了。我们被告知我们将离开伦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登船去法国?似乎同样可能的是我们将被送往集中营。尽管法国和英国朋友们坚持建议,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我的同伴们被遣返,我将和他们一起走。我计划一到法国就派人去接埃夫琳和阿兰,然后和他们一起去美国。除非我加入戴高乐的部队,否则我看不到留在英国的任何方法。即使我能够接受这个想法,我也几乎无法指望在这种情况下让埃夫琳来找我,甚至无法有效地与她沟通:作为被占领区,帕尔塞与英国的所有通信都被切断了。此外,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了。在英国,我们对法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仿佛我们在另一个星球上。无论是读报纸还是与朋友交谈都无法阐明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我渴望看看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为了为可能的离开做好准备,我让营地办公室的一个战友用我的真名准备了一张卡片,证明我刚刚从肺炎中恢复过来,并注明了我接受治疗的医院名称。有了这张卡片,当离开的时候到来时,我毫不费力地登上了去利物浦 (Liverpool) 的火车。在利物浦有两艘漂亮的医疗船,“斯芬克斯号”(Sphinx) 和“加拿大号”(Canada),是贝当派来接我们的。发现自己与我在白城交到的最好朋友分开了,我真的很难过。
这是我一生中最接近邮轮旅行的一次经历。船舱是为军官和重伤或重病者预留的;但我毫不费力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通风的地方。食物充足。因为我所谓的肺炎,我被拍了X光片;没有发现病灶。
“加拿大号”,所有灯都亮着,顶层甲板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沿着一条由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商定的精心策划的航线航行。我们首先向北行驶。在爱尔兰 (Ireland) 海岸附近,我们目睹了两名飞机被击落、漂浮在救生筏上的英国飞行员获救。我相信他们伤得不重,但尽管如此,能得到真正医生照料的前景还是让他们很高兴。完全绕过爱尔兰后,船只沿着葡萄牙 (Portuguese) 然后是西班牙水域向南航行,一直到直布罗陀 (Gibraltar),那两名英国人在那里下了船。在奥兰短暂停靠后,船只再次驶向西班牙水域,最后驶向马赛,我们在船上待了两周后在那里靠岸。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晒日光浴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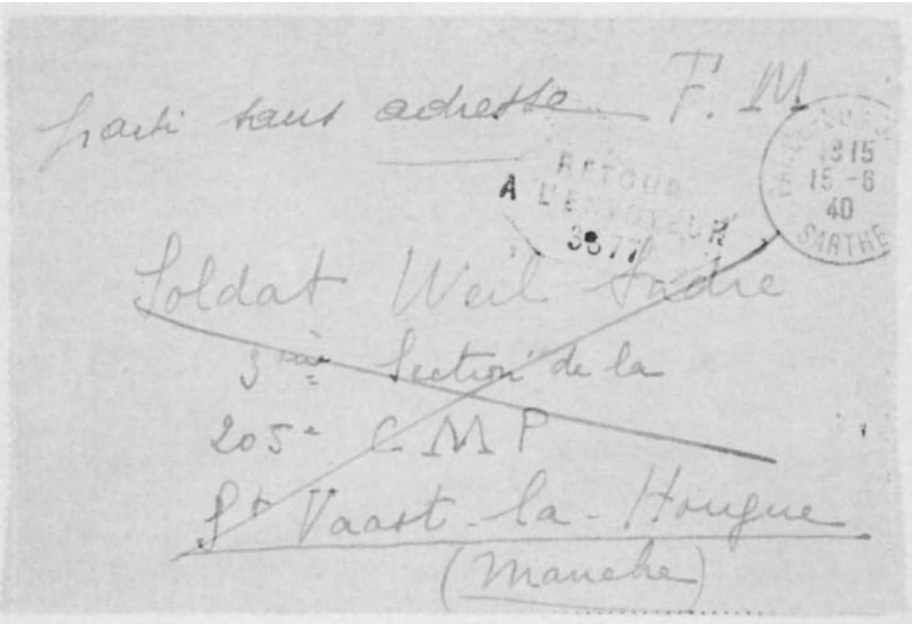 埃夫琳·韦伊写给A.W.的最后一封战时信件(1940年6月)
埃夫琳·韦伊写给A.W.的最后一封战时信件(1940年6月)
我以为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图卢兹 (Toulouse),他们在维希待了一段时间后确实去了那里。在伦敦,以及后来在奥兰,我曾试图联系他们,告知我将乘坐“加拿大号”抵达。船靠岸时,我惊讶地看到他们正等着我。他们对我喊道:“奥斯卡在这里等你。”“奥斯卡”是我们对警察的代号。
后来我得以重构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的母亲,一如既往地担心,一直缠着许多人打听我是否真的在船上。当然她什么也没打听到,但在码头上等待时,她听到某个军官、警察或官僚说:“我们也在找一个叫安德烈·韦伊的人。” 她没有意识到他是为了她而在打听我,误以为他是“奥斯卡”。在她的警告下,我回到我 modest 的行李旁,赶紧销毁了一位朋友托我转交给他家人的信。我不知道这条信息对他有多重要;他从未弄清楚为什么他的家人没有收到它。
什么也没发生。我们被带到营房,并获得了几个小时的自由,我和家人一起度过。第二天,出示了在伦敦伪造的卡片后,我被正式遣散了。像我所有的同伴一样,我领到了一套用粗糙蓝色军用布料做的西装,这是每个退伍士兵都有权获得的。它被称为“贝当装”("Pétain")。我必须说明我的职业。早在去年冬天,甚至在我回到法国之前,甚至在我任何确切信息可能传到法国之前,我就已经被解除了我在斯特拉斯堡的职位——据我后来被告知,是根据达拉第的个人命令。尽管如此,我说“教授”,这似乎暗示我是国家雇员。反犹法律,凭借它我无论如何很快也会被解雇,当时尚未宣布。结果,我无权获得授予每个退伍士兵以帮助其回归平民生活的小笔款项。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当主持仪式的老军官把“贝当装”递给我时,他对我说:“你可以用它去钓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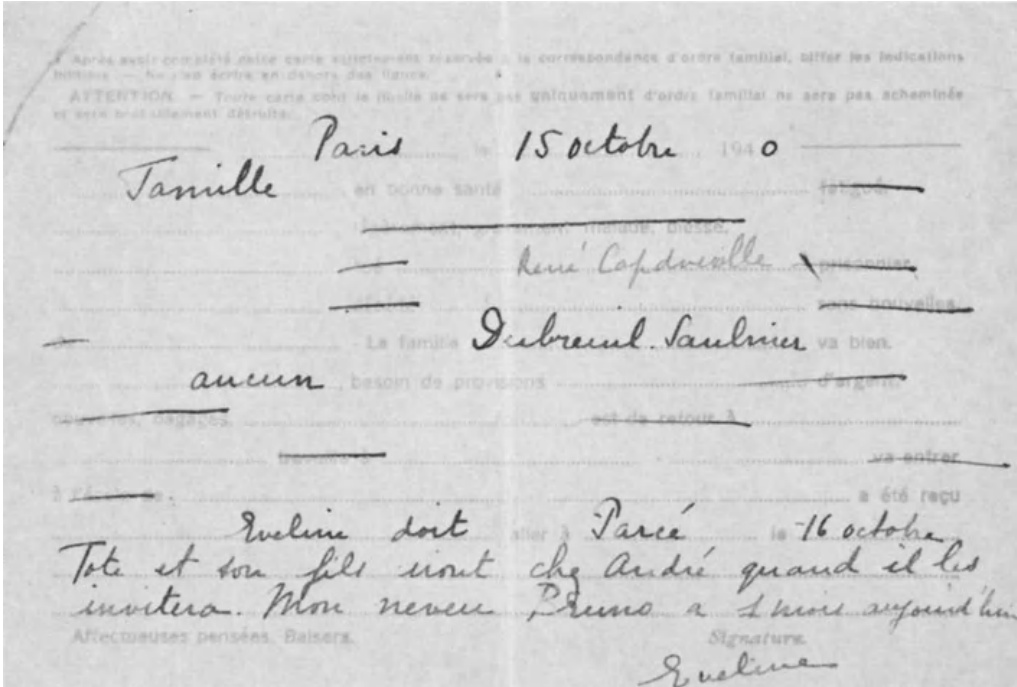 埃夫琳·韦伊寄给西蒙娜·韦伊的区间明信片(“德国佬明信片” - carte bochtale)(1940年10月)
埃夫琳·韦伊寄给西蒙娜·韦伊的区间明信片(“德国佬明信片” - carte bochtale)(1940年10月)
告别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我又成了平民,而且是失业者。我的父母承担了我的经济问题。他们不习惯和我讨论他们的财务状况;我接受了他们的帮助,没有问问题,当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偿还他们。
自六月以来,我一直没有埃夫琳的消息。她那个月写的最后一封信,用了我正确的军事地址,七月份被盖上“已迁,无转寄地址”的戳退回给她了。事实上,整个法国军队都已迁走,没有留下地址。我至今仍保留着这份象征性的文件,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保存着。埃夫琳不知怎么得知了我在英国。九月,布吕隆 (Brûlon) 当地一位寻找水源者 (water diviner),同时也是邮递员,证实了这一事实并预言了我的归来——甚至,显然,大致描述了我将要走的路线。他配备了一张欧洲地图和他的探矿杖 (divining-rod),利用一张照片和个人最后已知位置来定位失踪人员。埃夫琳只提到了瑟堡,但显然探矿杖追踪了我的路径穿过英国,然后到达地中海。这有多少可信度呢?不幸的是,这次咨询没有任何记录存在。
十月初,"自由法国" 和 "被占领法国" 之间的通信刚刚被授权,但仅限于 "区间家庭卡" (interzonal family cards),亨利·嘉当称之为 "德国佬明信片"¹³ (cartes bochtales¹³)。这些是预先印制的卡片,提供与法国生活相关的程式化信息选择:从“——身体健康/已阵亡/受伤/被俘”到“——已通过/未通过——考试”,后面是两行“个人通信”("personal correspondence"),然后是两种结束语选择,“爱与亲吻/深情地”("Love and kisses/Affectionately")。这些卡片刚刚分发不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张到达目的地。
除了与埃夫琳沟通的问题,我还专注于寻找去美国的方法——如果可能的话,合法地去。似乎没有什么是容易的:护照、签证、交通。战争一开始,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迁到了克莱蒙。虽然我不再与它有任何官方联系,但我的同事们在那里;此外,克莱蒙靠近维希,因此离法国自由区和被占领区的分界线不远。无论如何,埃夫琳都必须越过这条线才能与我团聚,如果需要,我自己也准备好越过它,尽管这会带来明显的风险。我给亨利·嘉当发了电报,并乘火车去了克莱蒙。
我不认为“奥斯卡”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如此,我妹妹未能准确确定我获得的缓刑的确切含义。我仍然需要“服刑”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一次告发可能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我一在克莱蒙下火车,嘉当就说:“小心,你可能会被发现。” 我向他解释了我的策略:我决定让自己处处散发出极度安全感的样子。如果我显得在躲藏,那可能会给某个乐善好施的潜在告密者提供一个谨慎告发的想法。这是我不想冒的风险。我去拜访了所有朋友。虽然丹容院长不再是“我的”院长,但他向我保证了他的支持,并信守诺言:他亲自陪我去了维希的教育部。
这时,甚至冬天来临后更是如此,维希是一番奇特的景象。主要酒店被改造成政府办公室,床被移走了,但洗脸盆和坐浴盆 (bidets) 完好无损。由于中央供暖不工作,安装了炉子,其排气管穿过专门切割出来以容纳它们的窗玻璃。所有这些伸出来的管道使得外墙看起来怪异而多刺。
毫无疑问,感谢丹容,我在教育部受到了很好的接待。维希的人大多是善意的人,有时甚至是戴高乐派。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反对通过将像我这样的案子出口到美国来处理它们。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教育部秘书长的泰拉歇 (Terracher) 提供了帮助和鼓励。我也见到了贝兰 (Belin),毫无疑问是在我妹妹的推荐下,她在战前与他通信了一段时间。她很看重这位工会活动家 (trade-unionist),一个诚实且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唯一的错误在于认为他作为贝当内阁的一员能够做些好事。贝兰这样向他的一位同事介绍我:“这是某某某,一位和平主义者;这是安德烈·韦伊,良心反战者。” 他承诺支持我的护照申请。我不知道他是否曾有机会为我出面干预。
埃夫琳的哥哥勒内·吉莱 (René Gillet) 当时和他妻子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布鲁诺 (Bruno) 在维希。维希不大;我在公园里偶然遇到了勒内。他是一名现役中尉,不久后将前往叙利亚。稍晚一点,我收到了父母的电报:“外甥布鲁诺一个月了。” 他们刚刚收到埃夫琳的第一张区间明信片。不知道在“个人信息”栏该写什么,她写了:“我的外甥布鲁诺一个月了”;我的父母确信这是一条紧急的密码信息,毫不耽搁地把它转给了我。
除了我的个人问题,还有布尔巴基的生存需要考虑。自1938年9月迪耶勒菲大会以来,就没有开过会了。我们内部公报《部落》的第一期由迪厄多内于1940年3月编纂并分发,至今没有后续期刊出现。我们伟大著作的第一分册已经由弗雷曼出版了。充分意识到我们期望它扮演的角色,并为了纪念欧几里得 (Euclid),我们称之为《数学原本》(Éléments de Mathématique)。第二部分刚刚出版,或者即将出版。1940年秋天,我们需要盘点情况并召集我们的小组,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以期继续我们的工作。幸运的是,我们中有几个人当时在克莱蒙。德尔萨特,不被允许返回南锡(那里在“禁区”("forbidden zone")),在格勒诺布尔 (Grenoble) 代替战俘法瓦尔 (Favard)。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大会,将居住在该地区的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洛朗·施瓦茨 (Laurent Schwartz) 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个计划几乎落空,因为德尔萨特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说“同意在克莱蒙开会”。“大会”(congress) 这个词,带有政治内涵,在维希法国是禁忌。我被传唤到地区军事指挥部,我去的时候以为是关于我的护照申请的事情,当时护照申请必须得到军事当局的批准。一位军官问我:“你认识一个叫德尔萨特的人吗?” 当我肯定地回答后,他要求我解释那封电报。芬兰的记忆回到了我的脑海。尽管如此,在我回答并请丹容为我担保后,我被礼貌地打发走了,我们的“大会”按计划举行了。
然而,我最紧迫的担忧是与埃夫琳沟通。区间明信片远远不够用,其他沟通方式缓慢且不可靠。我去了维耶尔宗 (Vierzon),它横跨分界线。检查站是一座由德国士兵守卫的桥梁。桥上交通繁忙,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在自由区这边,我遇到了市长,他向我保证我的问题很简单。他主动提出带一封信给埃夫琳,承诺在另一边寄出。按照他的指示,我请埃夫琳去维耶尔宗一个特定地址报到,从那里她将被带到自由区。收到我的信后,埃夫琳去了巴黎,当然带上了阿兰,还有她的母亲,她想再见见她的儿子勒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著名的布鲁诺。在巴黎,他们得到了相互矛盾的建议,甚至被告知应该联系德军司令部 (Kommandantur)。从那里他们去了维耶尔宗。但那时我给她的地址已经没用了;边境向导一定被抓了。幸运的是,在维耶尔宗,这条线只由正规德国军队守卫:稍晚一点,党卫军 (SS) 接管了,控制严厉得多。任何非法越境的人都可能被枪杀,但更有可能被送往集中营,期限不定。这足以让人犹豫。然而,只要愿意支付现行价格,就不乏走私者 (smugglers)。在关键时刻,一个农家女孩吸引了值班士官的注意,埃夫琳、她的母亲和阿兰得以越过——即使并非毫无疑虑,至少也安然无恙。
我收到一封从伊苏丹 (Issoudun) 发来的电报,宣布埃夫琳抵达自由区。我去接她,在一个她必须换乘火车的火车站找到了她。自瑟堡以来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住在离克莱蒙不远的塞拉 (Ceyrat),在一家食物仍然充足的旅馆里——不像城里,食物已经很匮乏了。另一方面,那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唯一的暖气来自晚上必须熄灭的炉子。清晨我会强迫自己起床点燃我们的炉子。当我失败时(这种情况相当频繁),整个房间会充满烟雾,我们不得不等待更专业的服务员来解救我们。当然,我们在床上吃早餐,依偎在我们能找到的所有毛织品下。迪厄多内住在隔壁房间,清晨黑暗中他看起来样子古怪:裹着数量惊人的毛衣,他还戴着一顶厚羊毛织的睡帽,几乎遮住了他所有的部分,只露出眼睛、嘴巴和鼻子。但我们在离旅馆很近的雪林里散步,足以弥补这些微小的不适。
与此同时,我一回到法国就联系了各位美国同事。我收到一封电报,提供给我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一个教职,并建议我在最近的美国领事馆申请“非配额”("non-quota") 签证;那是在里昂 (Lyon)。我听说过新学院,知道它是一所自由派机构,成立不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我不认为那里教数学,但这 hardly a time to quibble。然而,在领事馆,我 неприятно 惊讶地得知,根据美国法律,除非申请人能证明目前持有教职,否则不能授予“非配额”签证。一月份我已被解除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职位。这位领事,对所有拼命寻求签证的大量犹太人显然缺乏同情心,以此为由——或者说借口——拒绝了我的申请。在此期间,埃夫琳来找我了,我们收到了我们的护照,经维希当局正式批准。在马赛,我的父母成功地为埃夫琳、阿兰和我预订了开往马提尼克 (Martinique) 轮船的船票。我给新学院发了电报,被指示前往马提尼克;与此同时,学校会看看能做些什么来获得美国签证,他们无疑会在华盛顿为此游说。于是我们动身去了马赛。
维希刚刚通过了第一批反犹法律,我已经在克莱蒙的大学里看到了它们的执行。所有法国大学的院长都被要求列出在他们机构任教的所有犹太教员,作为迫使他们辞职的第一步。许多院长通过要求所有同事表明自己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找到了出路。这是一种体面的做法;尽管如此,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位院长采取“我从未知道你们中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我也不想知道。我特此辞去院长职务;让别人来执行这项任务吧,如果他愿意的话”的立场,是对法国大学荣誉的一种悲哀反映。我不相信选择这条道路的院长会承担任何真正的风险。正如沙法列维奇 (Shafarevitch) 曾经说过的,在这样的政权下,有很多情况下,人可以,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要么稍微挺直腰板,要么稍微多弯腰。无论如何,在维希政权下,即使那些因种族原因失去教职的人,人身安全仍然是有保障的;这种情况将在1942年随着全面占领的到来而改变。与此同时,马赛已经挤满了潜在的移民,并非所有人都是犹太人或外国人。他们不仅挤满了美国领事馆的候见室,还有许多其他领事馆。稍晚一点,一位声誉卓著的马赛商人,碰巧是暹罗 (Siam) 的名誉领事,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出售(价格相当高)完全真实的暹罗签证。我至今仍保留着我父母盖有其中一张签证的护照,这签证和去月球的签证没什么两样。一些难民凑钱租了一栋别墅,他们将其命名为“望签别墅” (Chateau Espère-Visa)。
我也——虽然不抱太大希望——去了马赛的美国领事馆。这次我运气好多了。领事是罗斯福派来的人,其明确任务是拯救因战争而处于危险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在我第一次请求时,并且无疑是藐视所有规定,他授予了我“配额”(quota) 签证。
尽管几位朋友悲观预测,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这样完成了。我们的船票预订在“温尼伯号”(Winnipeg) 上,它和它的姐妹船“威斯康星号”(Wisconsin) 构成了骄傲的法国横渡大西洋总公司 (Compagnie Générale Transatlantique)(俗称“横渡公司” - "Transat") 的全部舰队。“温尼伯号”和“威斯康星号”是两艘往返马提尼克的客货两用“香蕉船”("banana boats")。埃夫琳用一张“德国佬明信片”向她母亲(她已经回到帕尔塞)宣布了她即将出发的消息:“阿兰要上海军学校了。” 作为回复,她收到一张卡片说:“安德烈的孩子们在亨利叔叔家。” 这些“孩子”是我的书。在去与我汇合的路上,埃夫琳在巴黎安排了将我的图书馆运到恩里克·弗雷曼家,得到了我父母忠实清洁女工的帮助。大约在同一时间,弗雷曼寄给我我关于拓扑群上积分的书的前两本样书,我因此得以将它们带到美国。
就这样,一月底,我们登上了“温尼伯号”,备齐了所有圣礼和一大桶果酱——实际上并非果酱。在我们逗留克莱蒙期间,食品短缺虽然不严重,但已经开始显现。每个人总是在寻找划算的交易。这时我的岳母正忙着给她巴黎的朋友们寄食品包裹,她会用“德国佬明信片”告诉我们:“科利丹-雷¹⁴一家 (Colidan-Rée¹⁴ family) 一切安好。” 有一天在克莱蒙,传出消息说著名的蜜饯工厂“塞维涅侯爵夫人”(Marquise de Sévigné) 正在出售二等蜜饯水果。我们排队等候(时间不算太长)得到了回报,得到了一桶美味的糖浆浸渍水果,这对我们持续数周的航行饮食是一个重要补充,因为船只遵守维希法律规定的定量配给——这意味着那些不那么有远见或不那么幸运的乘客早餐只能吃干面包。一位爱开玩笑的乘客评论说,“横渡公司”的新座右铭是:“自备食物。” ("Bring your own food.") 另一方面,这艘因环境所迫成为“横渡公司”舰队精华的船只,配备了该航运公司最顶尖的人员。在餐厅里,迎接我们的是“诺曼底号”(Normandie) 的首席餐厅领班。每天晚上,无论多么难以忍受的炎热,他都坚持晚餐时穿夹克打领带。毫无疑问,他因为不能坚持要求穿燕尾服 (tuxedos) 而痛苦。
这并非我们航行中唯一特殊之处。我们悬挂着停战委员会 (Armistice Commission) 的黄旗航行。(和平时期,黄旗表示“船上有瘟疫”。)这次,船上没有货物,而是有300名水手被派去接替“圣女贞德号”(Jeanne d'Arc) 的船员,这是罗贝尔海军上将 (Admiral Robert) 舰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个人使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 (Guadeloupe) 处于贝当的控制之下。对大多数乘客来说,马提尼克并非最终目的地。他们都有计划,许多人有秘密。法兰西学院的生理学家安德烈·马耶 (André Mayer),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同行,像我一样希望能再次在美国教书。来自利摩日 (Limoges) 的瓷器制造商布洛赫 (Bloch),指望商业联系能让他立足。一些人希望加入戴高乐的部队,要么一直去美国,要么通过马提尼克本身的渠道。科尼利翁-莫利尼耶 (Corniglion-Molinier) 就是这种情况,他后来将成为戴高乐的航空部长。一些人,毫无疑问,只是离开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一位极其沉默寡言的乘客戴着的单片眼镜足以引发广泛谣言,说他是希特勒的追随者。据说他抽的香烟上印有卐字 (swastika)。
乘客太多了,像我家这样的家庭无法独享一个船舱。船舱按性别分配,通过非正式安排使夫妇能够不时享受隐私。九岁的阿兰几乎所有时间都和水手们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很受欢迎;他们教他打绳结。
当我们通过直布罗陀海峡 (straits of Gibraltar) 时,水手们私下透露,他们中的一些人跳海了,希望被英国船只捞起,以便能加入戴高乐派海军。在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我们的船在港口停靠了三天。我们本想去参观梅克内斯 (Meknès) 或马拉喀什 (Marrakesh),但被告知我们在此港口的逗留可能会缩短,所以我们只好满足于参观拉巴特 (Rabat) 及其老城。阿兰从未忘记拉巴特的鹳鸟 (storks),它们喙部发出嘈杂的嗒嗒声。
“温尼伯号”不是一艘快船。花了两个多星期才到达法兰西堡 (Fort-de-France)。那时,这是一个美丽、地理位置极佳的城市,低矮的建筑环绕着一个广场,我们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潘趣酒 (punch)。我们对市场的参观着迷,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鱼、香蕉和各种颜色的水果。通过我妹妹的朋友贝尔歇医生 (Dr. Bercher),我得到了一封给德埃塔日 (Des Étages) 的介绍信,他在岛上因杀死了一个对父亲之死负有责任的总督而闻名。我不知道他为此不得不在监狱里待了多久。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们以最大的善意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去附近的海滩游泳和航行。在他妻子经营的一家小企业的掩护下,他组织了一个网络,将志愿者带到圣卢西亚 (Saint Lucia) 领土,从那里他们可以继续加入戴高乐的部队。德埃塔日最终被捕并被监禁,我相信条件很恶劣;解放后他担任马提尼克副代表 (Deputy from Martinique)。
像我们一样,“温尼伯号”上的许多乘客都在寻求前往美国的通道。这样的交通工具很难找到,昂贵且不舒适。幸运的是,几天后,罗贝尔海军上将注意到我们向他的臣民展示并非所有法国人都支持贝当,从而挫伤了他们的士气,于是命令我们毫不迟延地登上“温尼伯号”。在这方面,我们比下一艘船“威斯康星号”的乘客幸运,后者被海军上将送进集中营待了几个星期。我们接下来在瓜德罗普停靠了三天,这让我们有机会游览了该岛,然后我们被带到维尔京群岛 (Virgin Islands) 的美国领土圣托马斯 (Saint Thomas),二月底,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在那里告别了“温尼伯号”。
尽管圣托马斯直到相当近期还是丹麦属地,我们准备好在那里预尝可口可乐文化了。天气闷热难当,但可口可乐却很匮乏;也许美国海军 (American Navy) 把它们都喝光了——尽管绝非排除了其他更强劲的饮料。我能给阿兰的只是一点温热的百事可乐 (Pepsi-cola),在一个挤满了醉醺醺水手的酒吧里。令阿兰高兴的是,其中一个水手试图骑马进入酒吧。一艘美国小船“卡塔琳娜号”(Catarina) 把我们带到波多黎各 (Puerto Rico),正好赶上获得开往纽约的定期班轮上最后三个铺位。海面相当颠簸,埃夫琳几乎无法离开船舱。早上我带阿兰去吃早餐时,我们被领到一张丰盛地摆放着果酱罐的桌子旁,一位美国女士已经坐在那里了。阿兰,习惯了“温尼伯号”上的贫乏条件,瞪大眼睛盯着那些蜜饯,问我:“那些都属于那位女士吗?”
注释:
¹ Munich conference: 指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خ签订的协议,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试图以此避免战争,成为绥靖政策的象征。 ¹ Self: 在印度教哲学(尤其是《奥义书》和《梵歌》)中指终极的、真实的自我,即“梵” (Brahman) 或“阿特曼” (Atman),超越个体经验和肉体存在。了知 Self 即获得解脱。 ² 韦伊引用的《梵歌》诗节,强调神在正义衰败时会化身降世。 ³ Avenue Edouard Daladier: 爱德华·达拉第是签署慕尼خ协定时的法国总理。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在韦伊看来,象征着绥靖政策带来的不祥之兆。 ⁴ Se non è vero...: 意大利语,谚语 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 的缩略,意为“即使不是真的,也编得很好”。 ⁵ Ça chie en Norvège: 法国俚语,非常粗俗,大致意为“挪威那边情况糟透了/一团糟”。 ⁷ Retz's memoirs: 指法国红衣主教让-弗朗索瓦·保罗·德·贡迪·德·雷斯 (Jean-François Paul de Gondi, Cardinal de Retz) 的回忆录,记录了17世纪法国投石党运动时期的政治阴谋。 ⁹ 韦伊引用了法国诗人马拉美 (Mallarmé) 的诗句,原文是关于少女的,这里被戏谑地用于修女。 ¹³ cartes bochtales: 结合了法语 cartes postales (明信片) 和 Boches (对德国人的贬称,类似“德国佬”),是当时对这种受德国审查控制的区间通信卡的讽刺性称呼。 ¹⁴ Colidan-Rée: 可能是韦伊和家人用来指代食品包裹的暗语,结合了法语 colis (包裹) 和 denrée (食品)。
第七章 美洲;尾声
(Chapter VII The Americas; Epilogue)
我曾读到过,太平洋战争的一些幸存者在救生筏上漂流了许多星期,仅凭一张袖珍地图指引方向。他们最终漂流到一个岛上,距离他们以为所在的位置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说,他们生存的关键在于,尽管风浪颠簸,始终牢牢握住舵柄,并认为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这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是他们的救赎。
毫无疑问,我比这些航海家幸运得多,我已经到达了我在整个 peregrinations 过程中确定的确切目的地:纽约。一到那里,我以为我的未来有了保障。首要任务是弄清楚新学院为我准备了什么类型的职位。
船靠岸时,学校派了一位官员来接我。他的第一步是把我全家带到布雷沃特酒店 (Brevoort Hotel),这是一家设备齐全的老式酒店,一些年长的纽约人至今仍怀念它。它坐落在雄伟的第五大道 (Fifth Avenue) 上,离华盛顿广场 (Washington Square)、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以及新学院都不远。
我立刻发现我在新学院的职位是虚构的:它被发明出来的唯一目的是让我有资格获得“非配额”签证——这个目的甚至没有实现。事实上,我被承诺的薪水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作为一项旨在救助法国科学家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
确实有理由担心德国人在法国的行为会像他们入侵那个不幸国家波兰 (Poland) 时那样,他们在那里已经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系统性摧毁。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即使在犹太人中,许多知识分子也无需为了逃避动乱而移民。尽管如此,没有人能确切知道,风险也确实太真实了。这是路易·拉普金 (Louis Rapkine),一位来自加拿大 (Canada) 的才华横溢的年轻生物化学家,在关键时刻恰好在纽约,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主要论点。他起草并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法国科学家名单,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认为应该尽快将他们从法国解救出来。他一得知——我不知道是如何得知的——我在1940年10月回到了法国,就把我加入了他的名单,正是这样我才收到了新学院的邀请。我曾称他为圣路易·拉普金 (Saint Louis Rapkine)。至今每当想起他给予我的善意,我仍深受感动。解放后,他费了些周折才在巴斯德研究所 (Institut Pasteur) 找到一个职位,结果不久后就因肺癌去世。他的去世让我深感悲痛。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身在纽约,暂时没有任何义务。由于基金会付给我的年薪2500美元或多或少足够我们的生活开销,我暂时免除了经济上的担忧,但我仍然需要考虑为长远打算,找一个更稳定,如果可能的话,报酬更好的职位。我这一代的其他数学家,我不认为自己比他们差,已经成功找到了这样的职位。我对美国的情况如何运作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特别担心。
另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在法国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妹妹留在了马赛,我不认为他们长期在那里会安全。我父亲的一位堂妹,布兰奇·加利福尼亚·韦伊 (Blanche California Weill),住在纽约;她的父亲,我父亲的大堂兄,也是阿尔萨斯人,但比我父亲年长得多,已于十九世纪移民,并在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 (Bakersfield, California) 创建了后来成为当地最大百货商店的产业。他的女儿布兰奇是一位聪明、精力充沛的儿童心理学家,是本世纪初最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她慷慨地提出签署我父母和妹妹获得“配额”签证所需的担保文件:这些文件使她对他们在美国期间的所有经济需求负责。但即使这个必不可少的手续办妥之后,还有很长的等待期。此外,虽然我的父母出于对自己安全,甚至更多地是对我妹妹安全的担忧而渴望来美国与我团聚,但她另一方面却绝不分享他们的渴望。作为来的条件,她想要我的保证,一旦到了这里她可以实施她的计划——她错误地以为我对此了如指掌。这个建立前线护士团 (corps of front-line nurses) 的计划,是她在离开马赛前与诗人乔·布斯凯 (Joe Bousquet)¹ 详细讨论过的。后来当她的计划被提给戴高乐时,他的反应是:“她疯了!” 事实上,她构思这个计划主要是为了能在身体上分担战斗中男人们最深重的苦难。显然,我无法给予她想要的保证。
幸运的是,维希法国和美国之间的通信仍然被允许,但自然也受到审查以及长时间的延误。与被占领法国的通信不被允许,因此埃夫琳不得不依靠朋友们的帮助才能与她的母亲联系;即使如此,通信也很缓慢且不可靠。
在所有方面,我相信我的学徒生涯现在已经结束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想法是多么错误。我于1941年3月3日抵达纽约。就在同一个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收到了一封关于我的来自哈弗福德学院 (Haverford College) 的信。信中强调我缺乏美国教学方法的经验,以及这种缺乏将对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提出愿意通过任命我担任哈弗福德数学系为期一年的教职来为我提供必要的经验(免费!)。由于基金会付给我薪水,这个职位是无薪的。
美国意义上的“学院”("college")² 是在中学(通常平庸)提供的中学教育之后提供四年教学的机构。十九世纪,教友会(“贵格会” - "Quakers") 在费城 (Philadelphia) 市郊创建了三所这样的学院。这些学院以其所在的城镇命名。三者中最古老的是哈弗福德,另外两所分别在布林莫尔 (Bryn Mawr) 和斯沃斯莫尔 (Swarthmore)。正是这个宗教派别在十七世纪创建了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官方名称为“联邦” - "Commonwealth")。1941年,哈弗福德仍然是一所纯男校,布林莫尔只招收女生,而斯沃斯莫尔已经是男女同校了。这三所学院都享有极好的声誉。在哈弗福德,贵格会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大量教授和学生定期参加周日的宗教仪式,仪式包括静默冥想,只有某个参与者可能受到的灵感启示的话语才能打断它。事实上,我相信,这些聚会很少在没有灵感降临到在场某人身上的情况下结束;通常,发言的是哲学教授。
贵格会不仅以其道德美德闻名,也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著称——这一特质可能与他们在美国社会受到的高度尊重不无关系。哈弗福德的提议在我看来并不算特别慷慨,但新学院的人强烈建议我接受它。我毫不费力地下定了决心,并且没有后悔这个决定。我被告知这是熟悉美国大学体系的好方法。四月初我第一次访问哈弗福德时,我冒昧地提出增加薪水会受到欢迎,我的大胆得到了回报,在我的洛克菲勒年薪之外又增加了250美元。其余方面,他们对我很好,我这个欧洲人在这个学院历史悠久的传统中不能不感到自在。
因此,我计划在接下来的九月新学年开始时到达哈弗福德。与此同时,我和家人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在那里我认识大多数数学家。事实上,我近期的过去,以及由此引发的流言蜚语,导致一些同事对我相当冷淡。但我几乎无法用言语表达与我的朋友西格尔和谢瓦莱重逢的喜悦,自1939年以来我只得到过关于他们最间接的消息。西格尔于1940年春天离开了哥廷根。早已决心前往美国,他安排自己被邀请到挪威,在那里他登记为政治难民。他从卑尔根乘坐最后一班开往美国的船只——就在德军进入奥斯陆 (Oslo) 的同一天。想象一下如果德军抓住了他会发生什么,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至于谢瓦莱,自战争开始以来法国就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谣言,他按规定向法国领事馆报到,并被告知留在普林斯顿,莱夫谢茨在那里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我一见到谢瓦莱,他就提出与我共享他在法恩楼的办公室。日复一日,来到这个办公室,我会与他分享我思考的成果。就数学而言,我最主要的关注点是详细制定我在一年前好消息监狱里发现的结果的无可挑剔的证明。赫尔曼·外尔,以他一贯的仁慈欢迎了我,提出利用他的影响力让我再次入狱,因为我之前在那类场所的逗留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如此积极的影响。
1941年的春天和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谢瓦莱,尤其是他的妻子雅克琳,在帮我们在普林斯顿市中心(如今那所房子已不在)安家落户,以及引导我们熟悉在美国购物的奥秘方面,提供了巨大帮助。诚然,那时超市尚未出现——或者至少尚未进入普林斯顿。在此期间,阿兰上学了,不久之后他说的英语就比他母亲和我都好了。他在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方面甚至比我还幸运: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一份卖报纸和杂志的工作,他孩子气的法国魅力在这份工作上派上了用场。
秋天,我们去了哈弗福德,如果不是世界大事和我们对欧洲亲人的担忧给我们的日子蒙上不祥的阴影,我们的日子本会极其幸福。我的一位同事,来自一个古老的贵格会家庭,因此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刚从欧洲回来,他是负责评估局势的教友会代表团成员。他们一致的结论,预测美国不久将参战,可以概括为三个词:“拼命武装”("Arm like hell.")。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一道绚烂的北极光照亮了费城上空。这种自然现象在这样的纬度几乎闻所未闻:难道是某种预兆?那天晚上警察局接到了大量焦虑民众打来的电话,询问战争是否在这里开始了。
除了这些担忧,我们的生活相当平静。阿兰入学了;埃夫琳在布林莫尔上美国历史课。哈弗福德数学系总共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同事们很友好,我的教学职责并不需要我付出太多努力。系主任并不自诩为严肃的数学家,但他确实有一种美国人中罕见的幽默感。与他的同事卡尔·阿伦多费尔 (Carl Allendoerfer) 似乎即将展开富有成果的合作。斯沃斯莫尔的数学教授,一位迷人的年迈荷兰人名叫阿诺德·德累斯顿 (Arnold Dresden),邀请我去他的学院谈谈我最近的工作,酬金为500美元。这次邀请不仅为我微薄的收入提供了可观的补充,也是一次宝贵的信任投票。
1942年初,我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认为是好消息的事情: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正准备给我提供一个职位。当这个提议到来时,令人失望:只是一个讲师 (instructorship) 职位,而且薪水低得可怜——这种职位通常会提供给该领域的新手。此外,我的大部分薪水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付这一事实再次影响了提议的条款。要不是为了我的家人,我真想不顾后果地拒绝这个提议。至少有人向我解释说,美国大学的传统包括讨价还价。遵循这个建议为我赢得了“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的头衔和略高的薪水。我为获得更合适职位而进行的试探都毫无结果,而且埃夫琳怀孕了。稍晚一点,在我访问了中西部一所大学后,邀请我去的那位朋友写信说:“你不可能被这里聘用——并非你的讲座不受欢迎,而是因为通常的三个原因:你是犹太人,你是外国人,而且对这些人来说你太优秀了。”
1942-43学年即将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我繁忙的日程安排,包括那些我已经知道会令人沮丧的课程。我以写给阿廷的信的形式,记录了我关于代数几何研究的最新想法。与此同时,我父母前往美国的旅行计划已经成形:他们和我妹妹于5月14日从马赛启航。七月初,经过包括卡萨布兰卡和里斯本 (Lisbon) 在内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后,他们抵达纽约,我在那里接了他们。妹妹立刻用她的计划——当然是那个著名的护士团——轰炸我。她希望毫不耽搁地联系雅克·马里坦 (Jacques Maritain),她指望他把她介绍给罗斯福;罗斯福会批准这个项目,她将前往伦敦去执行它。当我告诉她事情没那么简单时,她非常失望,但仍然没有放弃她的计划。
与此同时,她和我父母在纽约安顿下来,住在一套位于河滨大道 (Riverside Drive)、位置优越但 modest 的公寓里,可以欣赏到哈德逊河 (Hudson) 的美景。我搬到了伯利恒 (Bethlehem),一个除了钢铁厂(幸运的是它们离市中心相当远)外相当无害的小城市。这里仍然有许多宾夕法尼亚荷兰人 (Pennsylvania Dutch) 的痕迹,即定居该地区的德国门诺派教徒 (German Mennonites);他们的方言在该地区仍然被使用。市中心有一个宁静的墓地,只有大石头作为墓碑,还有一个漂亮的玫瑰园增添了它的魅力。
我们的女儿西尔维 (Sylvie) 于9月12日出生,就在暑假结束前。令埃夫琳非常满意的是,她分娩的医院不在伯利恒市区,而是在邻近一个诗意地名为喷泉山 (Fountain Hill) 的村庄:一份写着“韦伊,生于伯利恒”的出生证明对她来说会显得有点显眼,特别是如果孩子是男孩的话。当她在医院时,谢瓦莱来帮我处理家务,阿兰看到我们一边没完没了地擦盘子,一边不停地讨论代数几何,感到非常 amused。埃夫琳回家后,我们迫切需要家政帮助。不幸的是,由于大多数男人被征召入伍,女人们正在工厂里顶替他们。我们费了些周折才设法留住了一位名叫玛丽 (Mary) 的好人,让她离开她在拿撒勒 (Nazareth) 的家,来帮埃夫琳一段时间处理最基本的家务。一段时间后,陈省身 (Chern) 来访,他刚从中国抵达普林斯顿。他的来访,一段持久友谊的开始,对我们俩都富有成果。我不相信他被强迫参与洗碗。
我的“教学”,如果能这么称呼的话,于九月底开始。我所属的机构(这个词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与雇主的关系)被赋予了“大学”("university") 的高贵头衔;但事实上,它只是附属于伯利恒钢铁公司 (Bethlehem Steel) 的一所二流工程学校。对我以及我的同事们——他们在数学方面完全无知——唯一的期望就是端出愚蠢教科书里预先消化好的公式,并保持这个文凭工厂的齿轮平稳运转。有时,忘了身在何处,我会忘乎所以地开始进行证明。之后,按照既定仪式,我总会问:“有问题吗?”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会有人问:“这个会考吗?” 我的回答是现成的:“你应该知道它,但它不是很重要。” 大家都高兴。
1942-43学年就这样过去了。至少我能够继续写作,虽然速度有所放缓,我的关于代数几何基础的书,这是我后来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我的父母,然后是我的妹妹,当然抓住了最早的机会来看望我们刚出生的孩子。我尤其被妹妹的情感所打动。她立刻提出了孩子洗礼 (baptism) 的问题,她出于我显然无法认同的原因而热切渴望。埃夫琳也有同样的愿望。离婚了,并且在天主教会眼中生活在罪恶中,她认为自己处于教会之外,我相信她对此毫无痛苦;但她仍然对她童年的宗教感到依恋,星期天她经常去弥撒 (mass),我有时会陪她去。洗礼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几滴水滴在婴儿头上,正如我妹妹指出的那样,还有其他针对个人的论据。我怎么可能反对呢?没费多少力气就说服了我。
与此同时,阿兰的宗教归属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所讨论的时期,在像伯利恒这样守旧的城市里,学校记录中填写的“无宗教信仰”("No religious affiliation") 标签很可能对孩子不利。阿兰是埃夫琳第一次婚姻的孩子,那次婚姻是在教堂举行的;宣布他是天主教徒似乎是很自然的。按照惯例,是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们当地的本堂神父,为他的第一次圣餐 (first communion) 做准备了。
美国大多数天主教神父是爱尔兰 (Irish) 或意大利 (Italian) 后裔,两者都不以思想开放著称。第二年圣枝主日 (Palm Sunday) 我们就对此有了一个例证。自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意大利旅行时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Saint Mark's) 参加过圣枝主日仪式以来,这一直是埃夫琳和我最喜欢的圣日之一。1943年,埃夫琳像往常一样去了教堂,而我则在家照顾西尔维。埃夫琳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布道大致如下:“今天的福音多么美好啊!”神父说;“我多么希望能详细地谈谈它!但我们有更紧迫的问题。上周日的奉献严重不足。我们有许多开销需要支付……” 从这一个场合就概括是不公平的;但那天早上埃夫琳的愤慨难以言表。
无论如何,我们在寻找别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妹妹刚在纽约遇到了一位法国最杰出的多明我会士 (Dominicans):库蒂里耶神父 (Father Couturier),他后来因策划建造阿西 (Assy) 的万恩圣母院 (Notre Dame de Toute Grâce) 而闻名。她向他解释了我们的情况,他同意亲自负责阿兰的第一次圣餐。为了解释我们的请求,我告诉他:“我听说了许多关于美国神职人员的坏话。” 他以教会的方式回答说:“人们夸大其词了。” 与我妹妹的期望相反,他觉得埃夫琳教阿兰教理问答 (catechism) 完全自然。经过简短的考察后,他在纽约的法国多明我会小教堂为阿兰举行了第一次圣餐弥撒。就在举行弥撒前,他还提出让埃夫琳也领圣餐。惊讶又感动的她还是谢绝了。正如后来他的日记出版所显示的,他深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Vatican II) 精神的熏陶。弥撒令人感动。我从未听过一位神父以如此深刻和显而易见的信仰说出“看,天主的羔羊”(Ecce Agnus Dei) 这句话。
在此期间,我妹妹继续尝试,即使不是实现她的计划(她差不多放弃了希望),至少也要加入英国的戴高乐组织。她确信从那里她最终能成功通过降落伞进入法国。她无法忍受别人受苦而自己却过着受庇护的生活。她确实设法见到了安德烈·菲利普 (André Philip),后者同意将她招募到他的内政专员公署 (Commissariat of the Interior)⁵。十一月她去了英国。我们再也没能见到她。
1943-44学年对我来说开端不祥。由于战争,许多学院和大学突然发现自己濒临破产。它们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学生的学费,而学生们已被军队吞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当部队在美国的营地等待运往欧洲,不久后又运往非洲时,他们注定要无所事事 (otium)。为了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同时也为了让本身也无所事事的教员们有事可做,许多部队被派往了学院。这些新兵绝大多数什么都不懂,也不想增加知识,但这个事实无关紧要。在陆军科学训练计划 (Army Science Training Program,简称 ASTP) 的主持下,他们被派去填补动员在学院宿舍和财政上造成的空缺。我最终不得不每周花十四个小时向这些可怜的男孩们 spoonfeeding 代数和解析几何的基础知识。他们穿着制服来上课,由一名士官整队。有一次,为了维持安静,我让他命令他们立正。有一天,其中一个有问题:“我不明白 是什么。” 这个问题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刻,但我没有试图解释原因。
我至少曾希望夏天能自由地度过一个应得的假期,我期望将其用于仍在进行中的书,但这次喘息被剥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即将到期,看不到其他解决方案。在拉普金的建议下,我给基金会董事之一沃伦·韦弗 (Warren Weaver) 写了一封长信,询问他是否能利用他的影响力至少为我在某个科学氛围更浓厚的其他大学争取一个职位。他立刻回了一封令人鼓舞的信,但这封信之后很快又来了另一封,建议我耐心等待,忍受不适。后来我发现,在这两封信之间他咨询了莱夫谢茨,后者显然把我给韦弗的信视为专门针对他的指责。莱夫谢茨被认为是那些为了避免任何偏袒同教者的指控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反犹行为的犹太人之一。不久之后我与他就此话题进行的一次谈话让我目瞪口呆。
至少就我的直系亲属而言,我的生活无忧无虑。埃夫琳身体健康,西尔维茁壮成长。她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医生指定的炼乳品牌,因为在这段时有短缺的时期,这种牛奶有时会从货架上消失好几天。我的妹妹,抵达英国后已经在为安德烈·菲利普服务,定期给我父母写信,偶尔也给我写信。我的父母,仍在纽约,抱着希望能和她团聚的希望生活着。当戴高乐组织在阿尔及利亚站稳脚跟后,他们指望不久的某天能在那里与她重逢。
事实上,正如我们后来发现的那样,西蒙娜——在拼命努力让自己被派往法国执行任务,几乎肯定会送死之后——不得不在四月份住进了米德尔塞克斯医院 (Middlesex Hospital)。从这里她被转移到肯特郡 (Kent) 的阿什福德疗养院 (Ashford Sanatorium),当时已奄奄一息,并于1943年8月24日在那里去世。她尽一切努力不让家人知道她的状况,她成功了。
因此,没有任何事情为我收到来自密友克洛松夫人 (Madame Closon) 的电报做准备;至今这封电报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西蒙娜昨天平静去世,她从不愿让你们知道。” 路易·克洛松 (Louis Closon),战争爆发时在美国,很早就加入了戴高乐组织。他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出色,被授予解放勋章 (Compagnon de la Libération)。我1941年在纽约认识了他。1943年,他和家人在伦敦,除非他在别处执行任务;他和他的妻子是西蒙娜小圈子密友中的一员。克洛松夫人的电报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我忍不住怀疑是否该相信它。我知道克洛松夫人早先曾患过神经衰弱。当然,电报内容千真万确。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悲伤?但我没有沉溺其中的奢侈;通知我的父母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幸运的是,我知道我妹妹的朋友贝尔歇医生当时在费城。他在揭露法国对印度支那殖民统治最黑暗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和妹妹都曾为一份独立的左派期刊《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撰稿。作为一名商船医生,他大半生都在海上度过:正是以此身份他了解了印度支那,也因此他现在恰好在费城。我成功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陪同我去向父母告知噩耗这个令人沮丧的任务。
当我们在纽约见面时,我们决定应该减轻即将给父母带来的打击。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自己也对这个消息极为悲痛,让他打电话给他们,就好像他刚听到关于我妹妹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的谣言。与此同时,我们前往我父母的公寓。他们想发封电报询问我妹妹的消息。我父亲下到大堂,那里是楼里唯一的公用电话。贝尔歇和我在那里跟着他,相当笨拙地告诉他:“没用了。” 他立刻明白了。也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他开始哭了。“我们可怜的小西蒙内特,”他说(这是她小时候他对她的称呼);“她那么爱我们。” 然后,想到我母亲,他说:“我们怎么告诉她呢?” 听到消息后,她谈到要自杀,他们俩一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1943年剩下的时间对我来说相当黯淡,对我父母来说甚至更黯淡。感谢埃夫琳,我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但这却是我唯一的快乐源泉。改善我工作状况的前景毫无希望。一月份我给赫尔曼·外尔发了一封求救信,写道:“卖淫在于为金钱原因将高价值之物用于卑鄙用途;这就是我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宣布决定辞去目前的职位,无论后果如何,并请求他帮助为我和家人谋生。他回复说他理解我的感受,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处于类似境地,但“有些人对有组织的愚蠢比其他人更敏感”,他会看看能为我做些什么,并抱最好的希望。他确实联系了古根海姆基金会 (Guggenheim Foundation) 的秘书莫博士 (Dr. Moe),后者几乎独自管理着该基金会。莫博士表示理解和同情。根据基金会的规定,申请当年的资助已经太晚了——但我很快就获得了一笔资助。
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纽约,我遇到了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为他解决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土著部落婚姻规则的组合数学问题。他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的人文学部教了几年书。1944年,他把我介绍给了该机构的院长,遗传学家德雷福斯 (Dreyfus),他当时正在美国进行研究旅行。圣保罗大学刚刚成立不久,起初选择法国学者教授人文学科,意大利学者教授科学学科。由于巴西和意大利之间宣战,意大利教授被迫遣返;因此有一个数学教席需要填补。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和德雷福斯想到了我来担任这个职位。我的正式任命很快就随之而来了。
但这仅仅在巴西方面被选中是不够的。由于战争状态,任何外国人未经移民局 (Immigration Service) 签发的出境签证都不得离开美国。因此我为自己和家人,包括不想留在纽约的父母,申请了签证。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德雷福斯代表我向国务院 (State Department) 干预,但无济于事。我和德雷福斯都从未被告知这次拒绝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是,美国驻巴西的文化参赞打算将这个职位留给一位同胞,并在华盛顿表达了他的意愿。
其他的担忧开始困扰我。埃夫琳,战前曾患过肺结核,但我们以为她终于痊愈了,出现了复发的迹象。在医生建议下,我带她去了一家疗养院。阿兰留在了普林斯顿的朋友家,西尔维留在了我父母家。我们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伯利恒。
与此同时,我的厄运期即将结束。为了获得签证方面的帮助,我找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艾德洛特 (Aydelotte)。我告诉他,把我违背意愿地留在一个没有我容身之地的国家是不恰当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向移民局提出了这个论点,移民局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思想狭隘著称。没关系:我的签证被批准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朋友扎里斯基夫妇也将在圣保罗。在我看来,如果我去不了巴西,我曾向德雷福斯院长建议过这个名字。这种安排是为了满足美国文化参赞而达成的妥协吗?我无从得知。我只能为能在巴西与这些朋友重逢而感到高兴。
在此期间,埃夫琳已从疗养院出院。我们准备年底离开。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足以满足我们出发前的需求。我问莫博士我是否应该在计划离开美国之日提交辞职。他熟悉南美,告诉我:“我将从那天起暂停你的支票,但在你到达巴西之前不要辞职。一旦你到了那里,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你就可以把辞职信寄给我。”
在等待出发期间,埃夫琳和我在斯沃斯莫尔与阿诺德·德累斯顿一起搬家,这位老荷兰人的友谊对我来说已经证明是宝贵的。他在斯沃斯莫尔的一位同事是著名的英国诗人 W.H. 奥登 (W. H. Auden),他欣然同意与我一起审阅我正在为我的代数几何书写的引言。就这样,在我们从新奥尔良启航的前一天,我得以将完整的手稿寄给美国数学会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期望他们会出版它。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在规定我从序言中删去一句略带苦涩的话之后⁶。事实上,我对此早有预料,并且毫无困难地照办了。除了这个细节,这本书被接受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巴西校对了校样。
这一次,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们(埃夫琳、阿兰、西尔维、我的父母和我)将乘坐“里奥图努扬号”(Rio Tunuyán),一艘小型阿根廷班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艘恰好在法国理论上与阿根廷处于战争状态的短暂时期停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的法国班轮。阿根廷利用这种情况夺取了这艘船,改了名字,并配备了阿根廷船员。一年后,阿根廷人被迫将船归还给法国。到里约 (Rio) 的航行平安无事,但极其漫长,因为仍在进行的战争使得我们不得不沿着海岸线走一条不寻常的路线。西尔维很快成为船员和乘客们的最爱;阿兰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表演了一场成功逗笑了一脸严肃船长的木偶戏之后。
船上一位年轻军官,喜欢和西尔维玩耍,向我们坦白了他对船在新奥尔良停泊时间短暂的失望。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阿根廷,他对此期待已久。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女孩,并说服她回到他的旅馆房间,他说,她在那里允许他“除了最主要的事情之外的一切”。她拒绝了后者,说“我不能,我是天主教徒。”“但是,天哪,我也是啊!”可怜的家伙回答道;可怜人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
所有这段时间,自从法国政府回到巴黎后,我的朋友们,特别是亨利·嘉当,并未忘记我的命运。我1939年被解除了大学职位。1944年,我的朋友们让我“复职”("reintegrated"),用行政术语来说,回到了法国大学系统的编制中。正如教育部的一位雇员后来告诉我的那样,法国行政机器尽管有其所有缺点,但至少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像时间机器一样回到过去。从此,在系统眼中,我从未被解雇过。我只是暂时借调 (détaché) 到巴西。正如一位在巴西的同胞兼同事在我们离开文化参赞家时对我说的那样:“你看,韦伊,世界上有两种人:参赞 (attachés) 和借调人员 (détachés)。”
于是,在里约,机器通知了大使我即将抵达。文化参赞礼貌地欢迎了我们,并把我们派往圣保罗,德雷福斯院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于1945年1月抵达圣保罗,正值盛夏和暑假。德雷福斯解释说,我的薪水将从我到达之时起计算,但在法律要求所有巴西政府雇员,即使是临时雇员,进行体检之后才能实际支付。这也包括我,因为圣保罗大学是一所州立大学。由于这项手续可能需要数月时间,德雷福斯会预支他自己的钱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份薪水,加上大使馆以我借调身份支付给我的补助,让我生活得相当舒适,特别是因为巴西宪法的一条规定免除了神父、教授以及我相信还有记者的所得税。这条规定后来被废除了。
自然,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找个住处。我的法国同事们,特别是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格(我的老蒙田中学八年级教授的儿子),在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大忙。与我们在伯利恒阴暗的公寓相比,这是多么大的反差!一栋 modest 但舒适的房子,一个宜人的花园,一棵大含羞草 (mimosa),以及一年四季盛开的玫瑰,常常有蜂鸟(巴西葡萄牙语中称为 beija-flor 或“吻花者”)光顾: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此外,房租低得惊人。我的同事们告诉我原因: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德国人,曾是圣保罗纳粹小组的头目。在巴西,租金受到法律严格管制。虽然很少有房东遵守这些租金管制,但我们的房东认为遵守它们是明智的,以免引起注意。我们和他关系极好。
我相信是三月份课程开始了。我被任命为高等分析的合同教授 (contratado),或临时教授。那时,数学系和图书馆位于一个宜人街区的一栋迷人别墅里。我 либо 步行 либо 乘有轨电车(巴西葡萄牙语中称为 bonde)去上班。雇佣了一个女佣来打扫系里,特别是为每位教授,在课前课后,送上他想要的尽可能多的 cafezinhos(小杯巴西式咖啡)。当我1966年访问巴西时,我观察到这个极好的习俗已经中断了,数学系现在和大学其他系一起安置在一个 sprawling campus 上毫无特色的大楼里。
我的教学职责相当轻松。我的前任阿尔巴内塞 (Albanese),一位颇有声望的几何学家,为系图书馆收集了异常好的藏书,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领域,代数几何方面。这对我的目的来说非常棒。圣保罗市有大量意大利裔人口,许多人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此外,意大利语和巴西语(即比葡萄牙口音更柔和的葡萄牙语)相当接近。阿尔巴内塞可能用意大利语授课;我相信扎里斯基也是这样做的,至少在他逗留的早期是这样。来美国之前,扎里斯基曾在罗马长期居住,并在那里娶了一位意大利妻子。至于我,我开始用法语授课,第二年我换成了巴西语,我很容易就学会了——虽然不如埃夫琳那么容易,她是通过和我们抵达后不久雇佣的女佣(我们早已放弃了这种奢侈)交谈学会的。
巴黎一解放,邮件服务就恢复了。埃夫琳和她的母亲因此得以毫无阻碍地通信,我也恢复了与布尔巴基的通信。解放前,我只收到过一次大会报告:那是1943年9月在离雷恩 (Rennes) 不远的利夫雷 (Liffré) 举行的“小型会议”(mini-conference)⁷,在一个乡村旅馆里,那里仍然能吃到美味且首先是丰盛的食物。这次大会由嘉当、德尔萨特和迪厄多内参加,特别富有成效。如何将结论发送给谢瓦莱和我的问题出现了。一份寄给我们同事兼朋友乔治·德拉姆,并从瑞士转寄给我的副本,从未出现。另一份通过秘密戴高乐派邮袋寄往伦敦的副本,不知怎么到达了纽约,那时它已经丢失了地址。纯属偶然,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佩兰 (Francis Perrin) 看到了它,他认为自己认出了布尔巴基的风格,并立刻寄给了我。巴黎解放后,我在巴西,这样的绕道变得不必要了,我们的讨论像往常一样恢复了。
不久,我的巴黎朋友们做得更好了。他们代表我争取到了一个罕见的优待:一张飞往巴黎的旅行许可证,所有费用报销,这样我就可以重新与布尔巴基和法国取得联系。法国领事馆在六月份通知了我这个机会。连接法国和南美的航班那时已经恢复了。感谢领事馆,我从里约出发时带着一个小包和一公斤咖啡,我相信这在巴黎会非常受欢迎。碰巧我那天没有飞走:我没有被告知需要接种黄热病疫苗——我想是因为在达喀尔 (Dakar) 中途停留。我没有接种疫苗,而巴黎的命令很严格。大使馆设法让我搭乘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就这样,“载着一货物的韦伊和咖啡,” (或多或少引用布尔巴基式的记述),运送我的飞机把我,我相信是在勒布尔歇机场 (Le Bourget),于1945年6月20日放下。一次即兴的布尔巴基大会立刻举行了,在布尔巴基年鉴中记录为“咖啡大会”("coffee congress")。
1945年夏天巴黎的生活远非简单。第一天,我就必须获得必不可少的配给卡 (ration cards):面包卡、肉卡、“油和脂肪”卡,所有这些一直使用到1948年。奥古斯特·孔德街的公寓曾被德国人占领,他们搬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他们甚至试图,但未成功,搬走浴缸。内墙上有附近发生战斗留下的弹痕。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从朋友那里借一个床垫和毯子,并用从邻居那里借来的手推车把它们运到我的住处。出乎所有意料,我发现一对曾是朋友的犹太夫妇安然无恙地住在他们战前住的公寓里。他们在战争年代以假名在萨瓦省 (Savoy) 一个村庄里相当平静地度过。他们俩都是医生,能够获得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食物来源;他们好心地邀请我在逗留期间分享他们的早餐。其余方面,餐馆稀少且相距遥远,但高等师范学校提供了我大部分的营养,大会期间也供给了布尔巴基。
战前布尔巴基就已经开始试用新的参与者——我们称他们为“试验品”("guinea pigs")。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成为了正式成员。这次,师范生萨米埃尔 (Samuel) 被提升为试验品级别,并被任命为咖啡保管员。每天在他的书房里准备好咖啡后,他会把这种稀有珍贵的物质锁起来保管好。我们的会议在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萨米埃尔是官方记录员。他的报告用一首模仿马拉美 (Mallarmé) 的《天鹅》(Cygne) 的十四行诗加以润色,结尾是以下三行诗句:
 布尔巴基在佩尔武-勒波埃 (Pelvoux-le-Poët) 的大会 (1951年)。从右到左:A.W., H. 嘉当, J.-P. 塞尔 (J.-P. Serre), J.-L. 科聚尔 (J.-L. Koszul), J. 迪厄多内等。
布尔巴基在佩尔武-勒波埃 (Pelvoux-le-Poët) 的大会 (1951年)。从右到左:A.W., H. 嘉当, J.-P. 塞尔 (J.-P. Serre), J.-L. 科聚尔 (J.-L. Koszul), J. 迪厄多内等。
Il contemple étonné, comme enivré d'un philtre l'adhérence, un manteau qu'il n'a jamais compris que vêt, sur un compact, immobile, le FILTRE.⁸
我抵达巴黎后拜访的第一位是亨利·嘉当。巧合的是,我到他家时,正好他父亲刚从莫斯科回来。这甚至不是他预定回家的日子。一个法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去了苏联,与他们的苏联同行重新建立联系。埃利·嘉当带去了第一本布尔巴基出版物(俄国数学家当时还未听说过布尔巴基)以及我关于群上积分的书。自从1940年在鲁昂军事法庭出庭那天他为我作证,而我既不能与他说话甚至不能握手以来,我就没有见过他了。1945年他看起来身体健康,尽管他的健康很快就要衰退了。“啊,先生,”我对他说,“我希望能吻您”——我张开双臂拥抱了他。他一定相当吃惊,但以他一贯的仁慈,他优雅地顺从了。
除了为解放而战留下的一些痕迹外,巴黎大部分地区仍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同样奇迹般的是,街道上几乎没有交通。还有机会像那时那样自由地散步吗?街上能看到的唯一汽车是几辆美国军车和一些装有煤气发生器 (gas generators) 的私家车。空气从未像那时那样清新可呼吸。1945年7月,卢浮宫的一个展厅刚刚重新对公众开放。这就是方形沙龙 (Salon Carré),馆长们在那里集中展出了最著名的画作,这些画作在战争期间安全地存放在香波堡 (chateau at Chambord)。据说,由于一名工人的疏忽引发的一场火灾几乎将整个城堡以及藏在地下室的卢浮宫藏品付之一炬;幸运的是,火灾及时得到了控制。进入展厅,我看到一位年迈的绅士,呆立在伦勃朗 (Rembrandt) 的《拔示巴》(Bathsheba) 前,反复惊叹:“拔示巴!我珍贵的拔示巴!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你!” 几天后,当我在去帕尔塞的路上经过沙特尔大教堂时,我几乎想说同样的话,埃夫琳派我去那里给她的母亲送信。去帕尔塞的火车,也就是勒芒线火车,经过沙特尔时可以很好地看到大教堂。埃夫琳和我从未见过它而不深受感动。
我返回巴西的旅程比从圣保罗到巴黎的旅程更困难,尤其是更漫长。那时美国人正将他们的整个军事行动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所有向西飞行的航班都为军事目的保留了,负责送我回巴西的法国教育部无法为我争取到优先权。我不得不乘火车去里斯本,从那里乘坐一艘葡萄牙轮船,极其缓慢地返回里约。8月7日,我们在库拉索 (Curaçao) 停靠,那里是,或者至少曾经是,荷兰殖民地。我上了岸,买了一份报纸。突然我发现自己懂荷兰语了:报纸宣布第一颗原子弹已投在广岛 (Hiroshima)。
让这次爆炸标志着这些回忆录的结束吧。那时我已经到达,或接近,“我生命旅程的中点” (al mezzo del cammin di mia vita)⁹。自从那次回到巴西后,我过着数学家平静的生活,不时被科学发现的喜悦所照亮,但也因我多次旅行(大多与埃夫琳同行)的乐趣以及对世界各地杰作的沉思而增色。我是否应该继续谈论希腊、日本或中国——或者,离家更近的,普瓦图 (Poitou) 或勃艮第 (Burgundy)?让读者的想象力在这些诱人的名字上徘徊吧,我或许可以(像荷马 (Homer) 在他的涅瑞伊得斯 (Nereids) 名录中那样)补充说:“……以及许多其他的。”
但这样的故事难道不需要一个尾声吗?我在巴西的逗留,尽管有许多乐趣,却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所占据的教席迟早要由一位巴西数学家收回。此外,尽管1945年扎里斯基在圣保罗,1946年和1947年迪厄多内在,也不可能不渴望一个更 stimulating 的科学环境。我的巴黎朋友们认为,当勒贝格退休留下一个空缺教席时,有可能安排我被任命到法兰西学院,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幸运的是,我的朋友马歇尔·斯通刚刚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数学系主任,肩负着彻底改造该系的使命。他提供给我一个教席,我接受了。1947年秋天,我和埃夫琳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去了芝加哥,小女儿妮科莱特出生于1946年12月6日圣尼古拉节 (Saint Nicholas' day)。我直到1958年才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76年我从研究院退休。现在,虽然不无一丝忧郁,我终于可以告别所有这些回忆了。
注释:
¹ Joe Bousquet: 法国诗人、作家,因战争受伤长期卧床,与西蒙娜·韦伊有过深入的思想交流。 ² college: 在美国教育体系中,通常指提供四年制本科学位(学士学位)的教育机构,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是综合性大学的一部分。与欧洲通常理解的“学院”有所不同。 ³ Pennsylvania Dutch: 指早期从德国西南部和瑞士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语使用者及其后裔,他们保留了独特的语言(一种德语方言)和文化习俗。Mennonites 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宗教派别(再洗礼派的一支)。 ⁵ Commissariat of the Interior: 指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 (Free French) 运动在伦敦设立的负责内部事务(包括情报、抵抗运动协调等)的机构。 ⁶ 韦伊在其著作《代数几何基础》(Foundations of Algebraic Geometry) 的序言中,曾对当时数学界某些风气有所批评,美国数学会要求他删改了其中略显尖锐的语句。 ⁷ mini-conference: 指规模较小的会议或研讨会。 ⁸ 这三行法文诗句是关于拓扑学中“滤子”(filter) 概念的戏作,大意是:他惊讶地凝视着,仿佛被迷药灌醉/那闭包 (adherence),一件他从未理解的外衣/覆盖在紧集 (compact) 上,静止不动,那滤子。这是布尔巴基成员之间以文学形式进行数学讨论和调侃的例子。 ⁹ al mezzo del cammin di mia vita: 意大利语,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开篇第一句,意为“在我生命旅程的中途”。韦伊引用此句,暗示自己回忆录的时间点大约在他生命的中点。